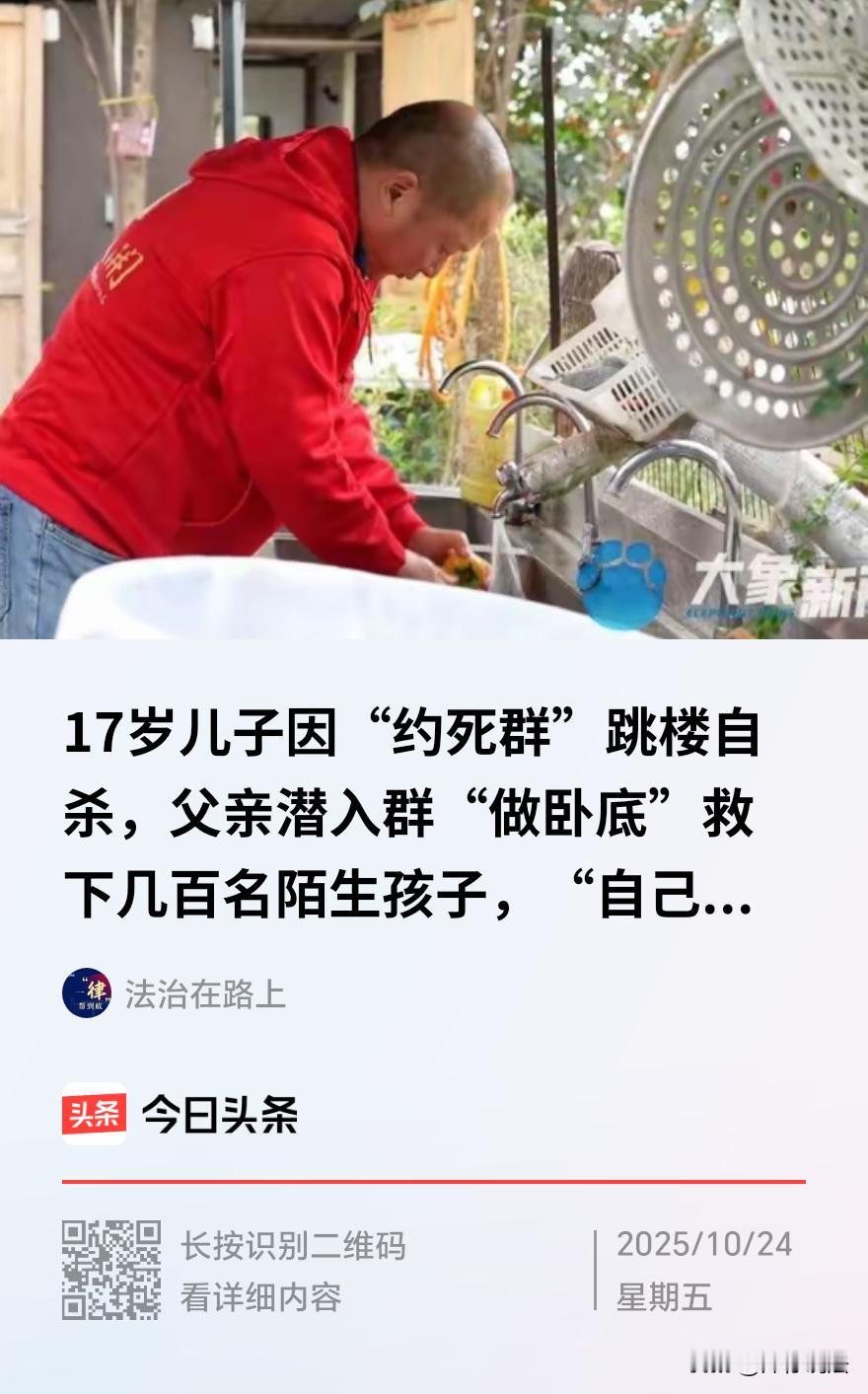河南郑州,一男子有个17岁的儿子,平时非常阳光,却因误入“约 死群”,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儿子突然从楼顶跳下,遗憾离世。男子翻遍儿子遗物,在那些“游戏、动漫群”里找到了答案,群里,孩子们用卡通头像讨论着“跳楼几层最稳”,相约“找个搭子一起走”。他们签名写着“活着没意思”、“再见世界”,言语间满是“父母根本不理解”的绝望。男子决定潜伏其中,从起初笨拙劝说,但迂回劝说,有了一些效果,挽回了一些孩子。三年来,他手机24小时开机,始终坚持,有人成了警察,有人重返校园。 2020年5月12日凌晨,徐世海(化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小区保安神色凝重地问他:“顶楼跳下来一个孩子,是不是你家的?” 徐世海来不及多想,第一时间冲向楼下,发现那个从楼顶一跃而下的少年,正是他17岁的儿子徐浩宇(化名)。 徐浩宇是亲友眼中的“完美孩子”,身高186厘米,成绩中上,擅长绘画,疫情期间还曾为抗疫医生画肖像。 徐浩宇善良开朗,爬山时主动帮同学背包,朋友拮据时悄悄请客吃饭,家中永远把“谢谢爸”挂在嘴边。 悲剧发生前毫无征兆。5月11日傍晚,徐世海刚参与完救援队打捞落水老人的任务回家,徐浩宇不仅给他倒了热茶,还主动洗衣服、拖地。 深夜11点,儿子最后一条消息是:“爸,明天想吃你做的红烧肉。”然而几小时后,这个承诺永远失去了兑现的机会。 儿子离世后,徐世海翻遍日记、相册仍找不到答案,直到点开儿子生前加入的QQ群。 这些名义上的“游戏动漫群”里,充斥着让人脊背发凉的内容,有人详细讨论“跳楼几层最稳”,有人分享割腕不疼的“技巧”,更有人组织“约 死”,在群里寻找轻生“搭子”。 最令徐世海震惊的是群成员状态,大多为十几岁的青少年,头像用卡通图案,签名却写着“活着没意思”“来生再见”。 他们用轻描淡写的语气传递绝望:“父母永远不懂你”“老师只会骂人”“世界不会变,除非重来”…… 徐世海心善,决定潜伏在这些群里,起初他笨拙地劝解:“生命只有一次”“爸妈会伤心”,结果迅速被拉黑。 后来他徐世海摸索出方法,先陪伴后疏导,不发大道理,而是分享路边小花、傍晚云霞,建立信任纽带。 三年间,徐世海的手机24小时开机,只为让孩子们的发声随时有回应。 如今,被徐世海帮助过的孩子中,有人成了经常给他发消息的帽子叔叔,有人复学后朋友圈笑容灿烂,还有人从外卖员成长为拥有6000粉丝的短视频创作者。 不得不说,徐世海是个有爱的人,因为他的坚持,让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各种阴影中走了出来,勇敢面对生活,值得大大点赞。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1、“约 死 群”的组织者和积极教唆者是否构成犯罪?应承担何种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组织、策划、煽动、胁迫、教唆、帮助其成员或者他人实施自杀、自伤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群组组织者与积极教唆者如以“寻找搭子”、“分享经验”、“提供方法”等方式,公开并具体地教唆、鼓励、帮助群内成员实施自 杀行为,其行为性质就可能从“情绪宣泄”转化为“非法侵害他人生命权”的犯罪行为。 对于,教唆、帮助具有认知和控制能力的被害人自 杀,由于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法益,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或共犯。 所以,群组组织者与积极教唆者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不过,一般参与者,对于在群内仅发表悲观言论、诉说自身痛苦但未具体教唆他人的成员,一般难以追究刑事责任。 2、网络平台是否应对徐浩宇的死亡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徐世海若能证明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群组内存在大量诱导、教唆自 杀的非法内容,如群组名称、聊天内容中出现大量“约 死”、“跳 楼”、等敏感关键词,且讨论频率高、参与人数多,从技术层面,平台通过内容审核算法是能够识别和预警的。 如果平台对这些显而易见的违法信息长期处于放任状态,则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 平台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后,负有立即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关闭群组、封禁发布者账号等。如果平台在具备技术能力和管理权限的情况下,未能有效履行上述义务,则构成过错。 基于此,平台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