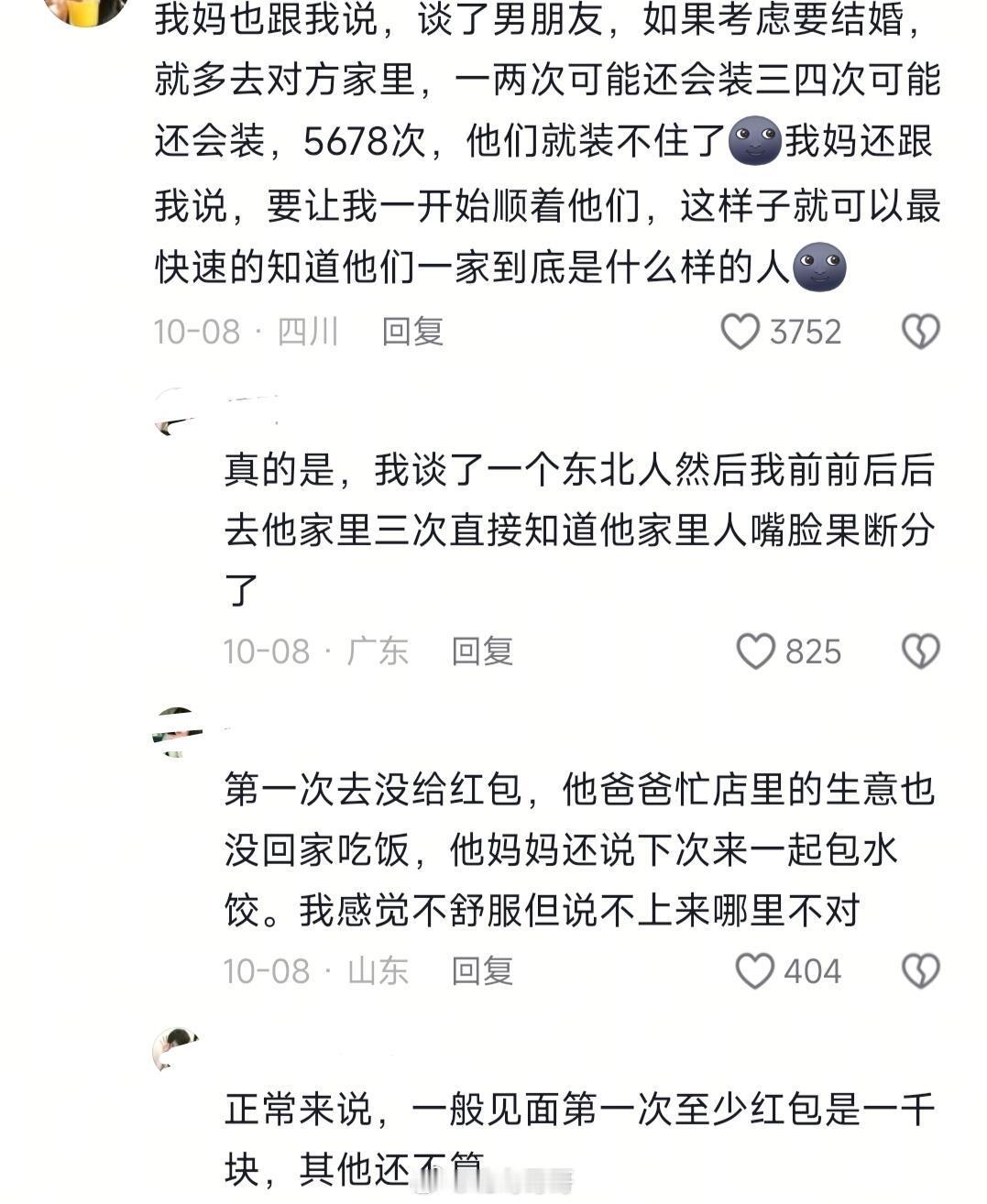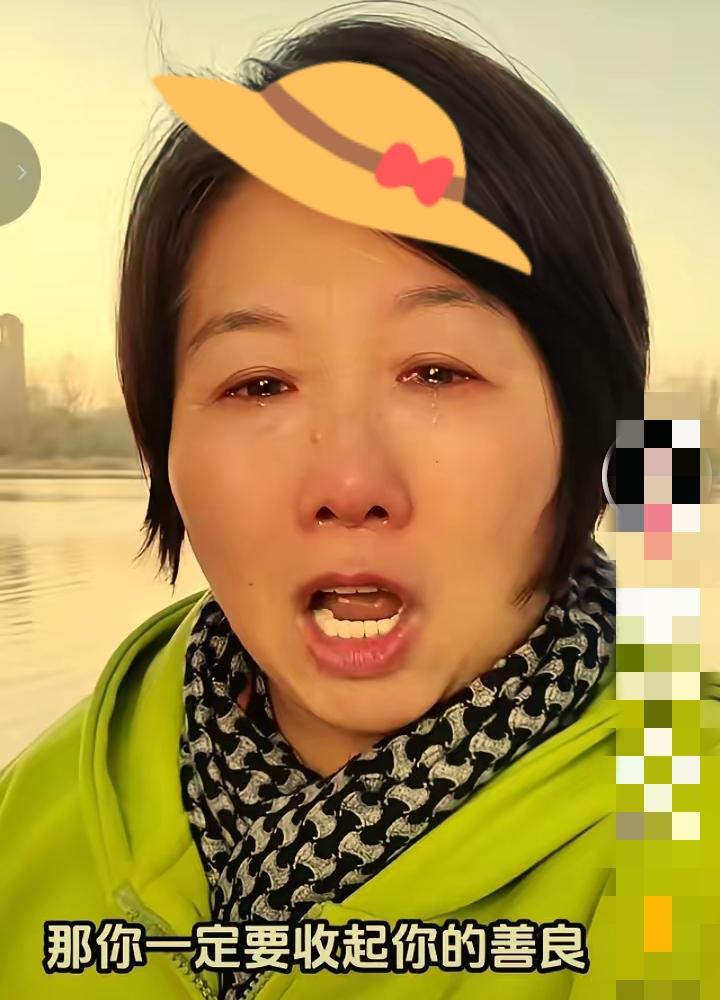我大伯儿子结婚,儿媳却要在房子上加她的名字,大伯拒绝了,那是一套两百万左右的婚房,大伯较真耿直了一辈子,当场就拍了桌子:“这房是我和你伯母砸锅卖铁给儿子准备的,要加名字,得等小两口自己挣!” 我大伯的搪瓷缸子在桌上磕出脆响时,厨房飘来伯母炖的莲藕汤香——那锅汤她熬了一下午,说是给准儿媳小敏补身子的。墙上的日历红笔圈着下月初的婚期,旁边贴着张泛黄的纸条,写着“瓷砖:5800,地板:7200”,是他跑了六家建材市场记下的账。 周五晚饭,小敏帮着端最后一盘青菜,围裙带子还没系好,突然抬头看大伯:“爸,装修师傅问,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 空气顿了顿。伯母的汤勺在砂锅里搅出小漩涡,没说话。小敏绞着围裙角,声音低下去:“我妈说,加个名字,以后我住着也踏实——不是外人。” 大伯没看她,筷子夹起的葱花饼悬在半空。他这辈子最认“实在”二字:年轻时在工地扛水泥,老板少算他五十块工钱,他蹲在工棚门口等到半夜,非要讨个说法;后来开小卖部,街坊多给一毛钱,他追出去半条街塞回去。此刻他喉结动了动,像是把那句“踏实”嚼了三遍。 “踏实?”他把饼拍在碟子里,搪瓷缸子“当”地砸在桌面,茶渍溅到记账纸条上,晕开一小团黑,“这房是我和你伯母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两百万,掏空了我们老两口三十年的积蓄,包括你伯母偷偷卖掉的金镯子,我戒烟三年省下的烟钱,还有你哥大学勤工俭学攒的两万块,全砸进去了!” 小敏眼圈红了,泪珠砸在地板上,碎成一小片湿痕。“爸,我不是图房子……” “那你图啥?”大伯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图个名字挂墙上好看?还是觉得嫁过来就得端走我们老的家底?我告诉你,小敏,这世上最踏实的东西,是自己挣来的!你俩结婚,房子随便住,物业费水电费我和你伯母还能帮衬着;但要加名字?得等你们自己挣出一套来,到时候写谁的都行!” 他拍了桌子,桌上的莲藕汤晃了晃,油星子溅到小敏手背上,她却没躲。我后来才知道,小敏父母早年离婚,她跟着母亲租了半辈子房,搬过八次家,每次房东要收房,母亲都抱着她的旧书包哭:“要是有个写你名字的房子,咱就不用颠沛了。”她要的,或许从来不是那两百万的房产,而是一个“不用再搬”的承诺。 大伯不知道这些。他只记得自己二十岁时,揣着借来的五十块钱进城,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所以认定“自己挣的才稳当”。他抽屉最底层锁着一沓泛黄的纸,是当年给人盖房时的欠条,还有儿子小学得的第一张“劳动小能手”奖状,边角都磨卷了,却被他用塑料膜仔仔细细包着——在他心里,汗水泡过的日子,才配叫日子。 那晚的饭没吃完。小敏默默收拾了碗筷,洗碗池的水声哗啦啦响,盖过了伯母的叹息。大伯坐在桌边,盯着墙上的记账纸条,茶凉透了也没再喝。 婚礼前三天,小敏没来家里吃饭。倒是我哥,偷偷塞给大伯一个存折:“爸,这是我和小敏攒的五万块,她说先把金镯子给妈赎回来——名字的事,我们不急,等以后……等我们自己买了房,您再给我们题字。” 大伯捏着存折,指腹摩挲着封皮,突然想起小敏第一次上门,给他端洗脚水,手被烫得缩了一下,却笑着说“爸,水热乎,解乏”。他眼眶有点酸,把存折塞回儿子手里,转身进了里屋——衣柜顶上,那个红布包着的金镯子,其实他早就赎回来了。 现在那镯子戴在伯母手上,小敏说“妈戴着好看”。而那套没加名字的婚房里,阳台晾着小两口的工作服,一件印着“装修公司”,一件别着超市工牌,在风里轻轻晃。 有时候我会想,大伯拍桌子的那一刻,是不是也在害怕?怕自己护了一辈子的“实在”,会变成扎在孩子婚姻里的刺。但后来看着小敏和我哥周末跑建材市场,为省五十块砍价半小时,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比房产证上的名字更结实——是两个人一起弯腰捡硬币的默契,是你懂我的“安全感”,我也懂你的“不容易”。 就像大伯的搪瓷缸子,茶渍结了一层又一层,可每次小敏来,还是会抢着拿去洗,说“爸,我给您泡新茶”。那茶冒着热气,暖了杯子,也暖了人心。
“结婚前请多去几次男方家”
【2评论】【8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