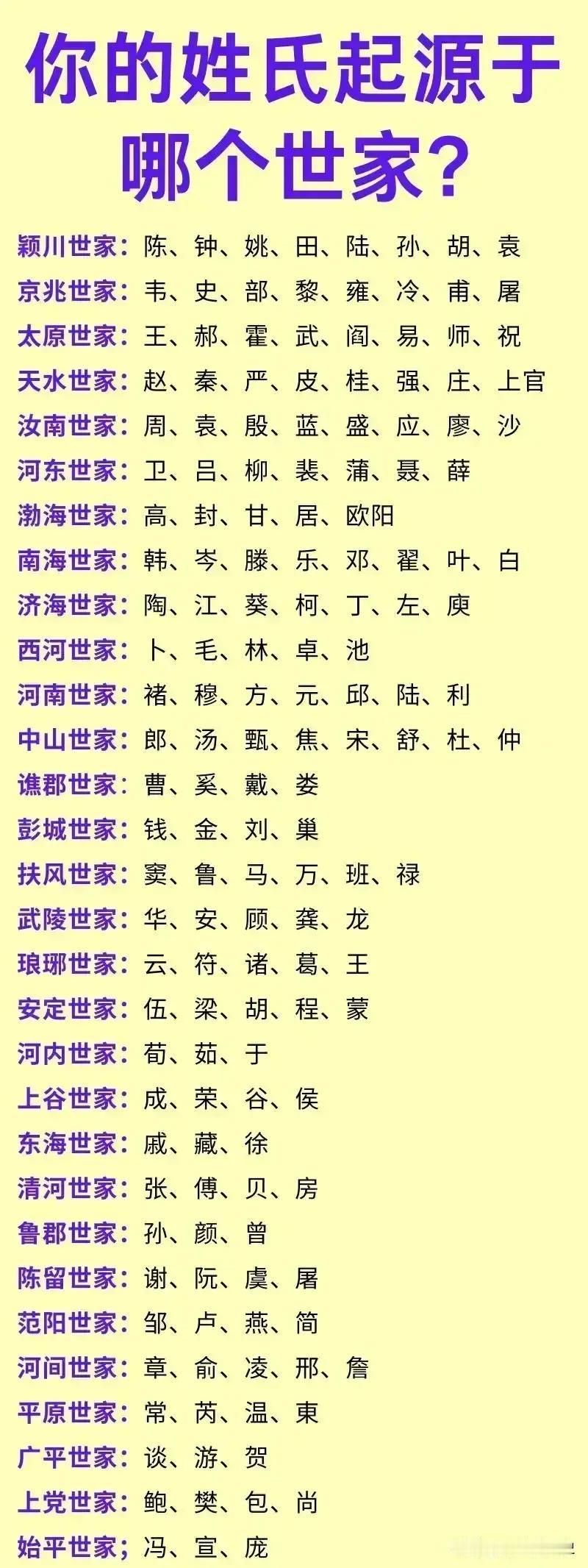"古代,一位记性不好的衙役,需要押送重罪和尚,半路上和尚偷着跑了,没想到衙役却没有着急,而且还非常高兴。 有一位衙役,看起来傻傻的,没有什么能耐,再加上年龄大了,记性也不好,常常丢三落四,唯一的优点就是办事比较认真,但仍然经常把上头交代的事情搞得一团糟。 那是个县衙人手捉襟见肘的年头,案头堆叠的卷宗边角泛黄,墨痕在日光下洇出浅灰;老爷捏着胡须叹气,终究把解送重犯的差事推给了这个总把算盘珠子拨错的衙役。 他攥着那张盖了朱印的文书,指节因用力泛白,仿佛那纸公文能替他记住些什么。 上路第三日,衙役忽然蹲在田埂上拍大腿——他把随身物编成了顺口溜,每走三步就念一遍:“雨伞遮头,包裹压肩,和尚在旁,我走中间。” 声音在空旷的官道上飘远,惊飞了路边啄食的麻雀。 夜宿驿站时,和尚摸出碎银拍在桌上:“店家,切二斤肉,温一壶酒。” 衙役喉头滚动,眼睛黏在油汪汪的肉皮上,嘴上却嘟囔“公务在身,不可贪杯”——筷子却先一步伸了过去。 翌日正午,衙役在头痛中醒来,左手摸到冰凉的伞柄,右手触到沉甸甸的包裹,猛地坐起——身侧空空如也。 冷汗瞬间浸透粗布短褂,他想起老爷的话:“跑了和尚,你就得去蹲大牢。” 慌乱中,他的手碰到脖颈上的铁枷——那本是锁和尚的器物,此刻正硌着自己的锁骨。 再一摸头,昨夜还扎着的发髻没了,头皮光溜溜的,像刚剥壳的鸡蛋。 “和尚还在!”他咧开嘴笑,在屋里转圈,木屐踩在地板上哒哒响。 转着转着,脚步忽然停了:“和尚在,那我去哪儿了?” 并非所有糊涂都是天生——有些看似愚笨的人,反而能在特定规则里活得安稳;可这个衙役,偏偏把自己绕进了认知的死胡同。 县衙当初派他去,本是无奈之举:老衙役告老,新捕快未到,名册上能走动的,只剩这个“办事认真却总出错”的家伙。 这或许暗示着那个年代基层治理的某种粗放——用人只看“可用”,不问“适配”,使得本可避免的疏漏,像田埂上的草,春风一吹就冒头。 这场荒诞剧的结局没人记载,或许衙役最终发现了真相,或许他顶着光头回了县衙,被老爷哭笑不得地打了三十大板。 但千百年后,人们仍在说这个故事,因为它戳中了每个人心底的那层雾——我们总以为看清了周围,却常常看不清自己。 心理学上管这叫“苏东坡效应”,就像诗里写的“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你以为自己是谨慎的,却可能在关键时刻冲动;你觉得自己洒脱,却或许在某个深夜为一件小事辗转难眠——认知里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有时隔着一条河。 如何渡这条河?或许可以学学老木匠刨木头:先直面纹理的疏密(自我审视),再用墨斗弹出基准线(收集反馈),最后在刨花飞舞中,一点点露出木头本来的模样(在成败里校准)。 当年那个对着枷锁傻笑的衙役,与此刻对着镜子自问“我是谁”的我们,隔着时空共享同一场认知困境。 只是,他困在古代的驿站,我们困在现代的日常——何时才能拨开迷雾,看清镜中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