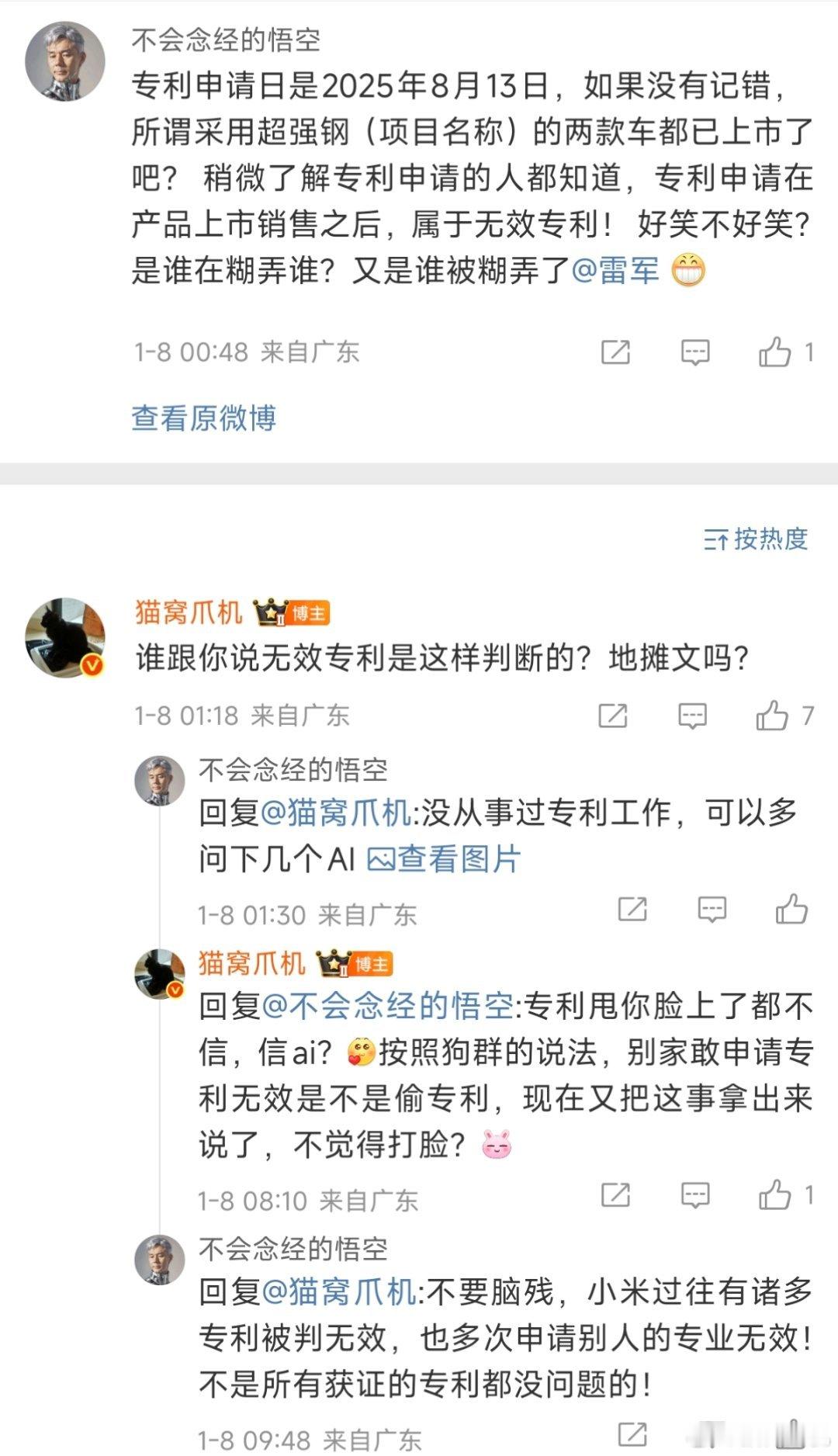正在修改我的长篇,接到一个电话。 是文友打来的,说最近要去参加省里的会议,让我早做准备。 我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睛还盯着屏幕上那段卡了三天的对话——男主该不该在这时候跟女主坦白呢?坦白了吧,显得太急;不坦白吧,后面误会越滚越大。光标一闪一闪的,像在催我。 挂了电话,屋里一下子静了,就剩空调外机在窗外嗡嗡地响,像个老人在叹气。我往后一靠,椅子吱呀一声。去年这时候,我也为这个会折腾过一回。特地去染了头发,三年没动过的白头发,硬是染成了黑漆漆的,照镜子都觉得里头那个人有点陌生。还买了那件深灰色的毛衣,厚实,宽大,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觉得有安全感。结果会没开成,毛衣也就去年冬天套过一回,后来一直挂在衣柜最里头。 昨天回老家吃喜酒,不知怎么的又把它翻出来了。穿上身,站在堂哥家那面有点水银斑的旧镜子前一看,是还行,就是觉得哪不对。哦,是太大了,袖子长得能藏住半只手。去年明明喜欢这种被包裹起来的感觉,今年却忽然觉得它累赘,拖拖拉拉的。宴席上吵得很,小孩到处跑,鞭炮一阵一阵的,我隔着热腾腾的饭菜雾气看着那件毛衣,心想,回来就把它收起来吧,该买两件衬衫,利落点。 手机又震了一下,大概是文友发的会议日程。我没看,手指在删除键上停了半天,还是没按下去。这段情节是得改,不改后面全是窟窿。可这一改,从第十八章到三十五章,人物的动机全得顺一遍,想着都头皮发麻。 这两部长篇,像两个养了太久、枝杈横生的老树,修剪起来,一剪刀下去,不知道会掉下多少叶子。有时候改着改着,会突然忘了最初为啥要安排这个配角出场。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来,远处楼的轮廓模糊了,先亮起几盏零星的灯,接着成片成片地亮起来。我起来开了灯,回头看见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忽然有点恍惚:这五年,一天天的,就在这键盘声里过去了?一千万个字,听起来吓人,摊到每一天,也就是坐在电脑前头的这几个钟头。 五十八了。脑子里冒出这个数的时候,自己都顿了一下。楼下传来谁家炒菜的刺啦声,带着股葱蒜的焦香。我还能坐在这里,为了一段对话、一件毛衣去不去开会这种事儿琢磨半天,好像……也不算太坏。 去开会,无非是见些人,说些话,握几下手,吃几顿差不多的饭。回来,稿子还得自己改,一个字也不会少。文友说这是个机会,可我寻思,我的机会好像不在那头,就在这屏幕的光里,在我这双还能敲字的手上。 我重新坐直,把手机屏幕扣在桌上。那个会,要不就……算了吧。 手指放回键盘,找到刚才那段对话,想了想,把男主那句绕了三个弯的台词全删了,就给他留了最直白的一句。改完,顺手把文档里“宽松毛衣”的描写也找出来,全换成了“熨帖的衬衫”。 窗外彻底黑了,我屋里的灯,还亮着。
正在修改我的长篇,接到一个电话。 是文友打来的,说最近要去参加省里的会议,让我
勇敢的风铃说史
2026-01-08 12:23:22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