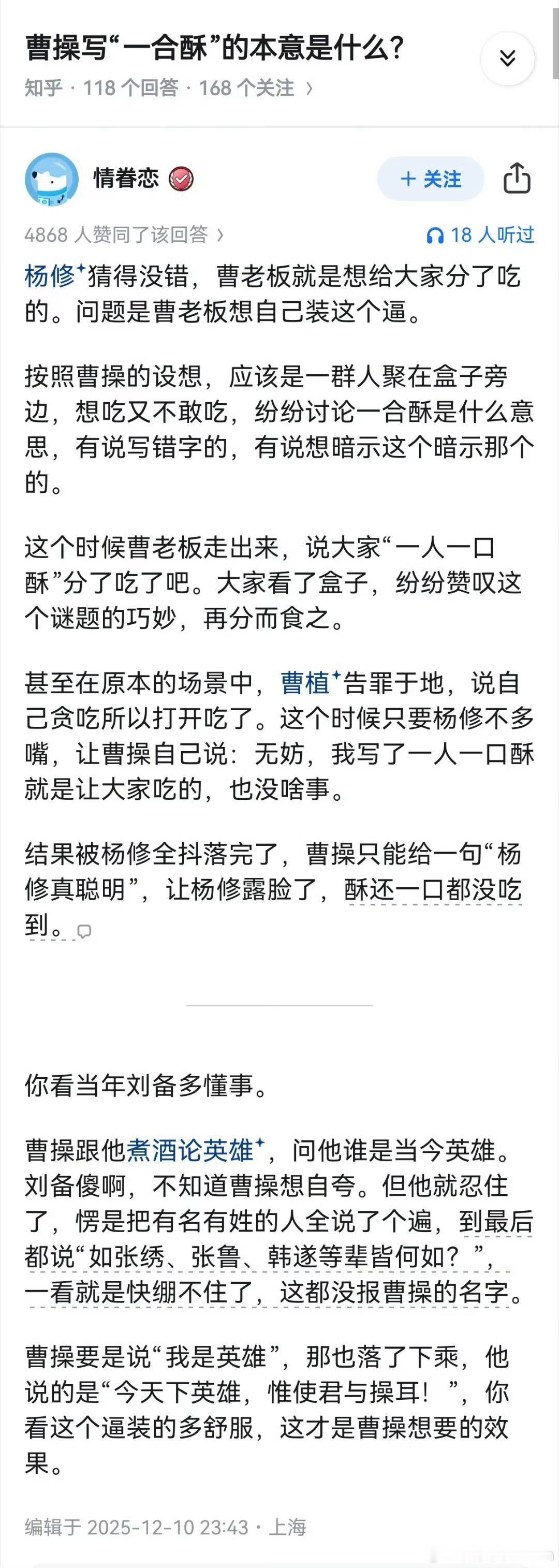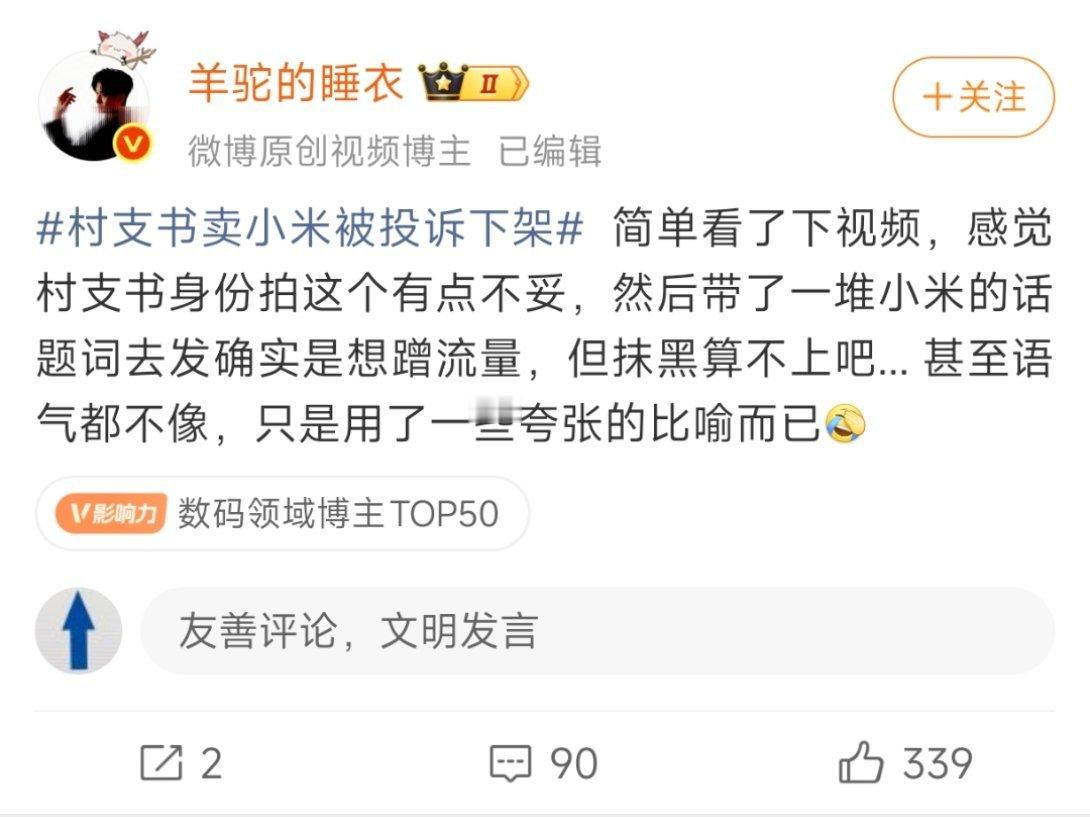架空:魏延惨死马岱刀下,人人都笑他脑后有反骨。姜维却在很多年后才懂:文长非死不可,他若不死,丞相的北伐大计必将毁于一旦。 建兴二十七年秋夜,汉中定军山的蜀汉大营里,姜维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案头的雍凉地图,图上长安的位置被朱砂点了个刺眼的圈。帐外的风裹着寒意钻进来,案头青铜灯豆的火苗猛地一蹿,映得他鬓角的白发格外清晰。 “大将军!”偏将廖化掀帘而入,甲叶上的霜花簌簌落在毡毯上,“末将有一计——子午谷出奇兵,五千精兵直捣长安,汉室复兴指日可待!” 姜维抬眼,这后生眼里的光烫得他心口一缩。多像啊,像极了当年那个拍着地图喊“长安唾手可得”的魏延,连眉峰挑起的弧度都如出一辙。可当年谁都当丞相是嫌这计太险,直到自己接过北伐的印绶,直到今夜廖化的话像锥子扎破了十几年的脓疮,姜维才惊觉——丞相不是怕奇谋不成,是怕它成了。 建安十三年五丈原,丞相榻前最后那夜,杨仪、费祎和他跪在帐内听遗令。“杨仪统军,姜维断后,”丞相咳着血说,“魏延若不服,不必管他。”众人退去时,丞相却攥着他的手腕塞来个牛皮包,骨节硌得他生疼:“伯约,看着就好,记着就好。” 那会儿他只当是弥留之际的胡话。没几日,魏延果然烧了栈道,堵了大军归路,在南谷口勒马大喊“杨仪矫诏”。乱军里,杨仪掏出“丞相遗令”,字字都是“魏延脑后有反骨”;马岱提刀冲上去,魏延回头的瞬间,姜维分明看见他眼里不是谋反的狠戾,是全然的错愕。 “谁敢杀我?”那声喊像根刺,扎在姜维心里十几年。军中都传是杨仪与魏延争权,连他自己也偷偷信过——毕竟杨仪掌权后没少排挤武将。可今夜廖化的话,让他鬼使神差地摸向了箱底那个夹层。 牛皮包上的油布早就脆了,里面是卷泛黄的竹简,丞相的字迹力透竹背:“文长之勇,可破长安;长安之固,蜀难久守。”后面跟着几行小字,像用尽了最后的力气:“魏兵十路合围,我军粮草只够三月。文长若据功自守,蜀地空矣;若战死,长安归魏,北伐更难。” 原来丞相算的不是魏延能不能赢,是赢了之后怎么办。蜀汉那点兵力,守着汉中都捉襟见肘,哪有余力分兵守长安?魏延凭这奇功,朝堂上谁压得住?到时候要么粮草耗尽战死,要么兵败降魏——无论哪种,蜀汉都是砧板上的肉。 姜维忽然想起马岱。那员武将平日里闷不吭声,偏偏在魏延喊出“谁敢杀我”时应声而出,刀快得像早就演练过百遍。原来那把刀,从一开始就是丞相递过去的。 “廖化,”他把地图卷起来,木轴撞在案上咚地响,“蜀汉的家底,就像这灯油,看着亮,烧不了几个时辰。赌不起。” 廖化张了张嘴,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最后低头叩首,铠甲碰撞的声音在帐内格外沉。姜维看着他,忽然想起魏延死时那双没闭上的眼睛——那里面哪有反骨,分明是“我为汉室死,为何说我反”的不甘。 后来邓艾偷渡阴平,刘禅开城投降的消息传到剑阁,姜维正对着地图上的“沓中”二字发呆。他拔剑砍向石壁,剑锋断成两截,像极了蜀汉那撑了三十年的命数。 丞相用魏延的命续的这口气,终究还是漏了。他自己守着那个牛皮包,守着那个秘密,拼了二十年北伐,也不过是在漏船上多钉了几块木板。 魏延的反骨是编的,子午谷奇谋是真的,可蜀汉的气数,早在丞相写下那卷竹简时就定了。后来的人只笑魏延活该,只叹诸葛看错人,谁会知道定军山的秋夜里,一个将军对着半卷残简,把牙咬得生疼。 历史这纸,从来只记结果,不记苦衷。就像那盏灯最后灭了,没人知道它曾照着一个关于忠诚与牺牲的秘密,照着一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把命填进了兴复汉室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