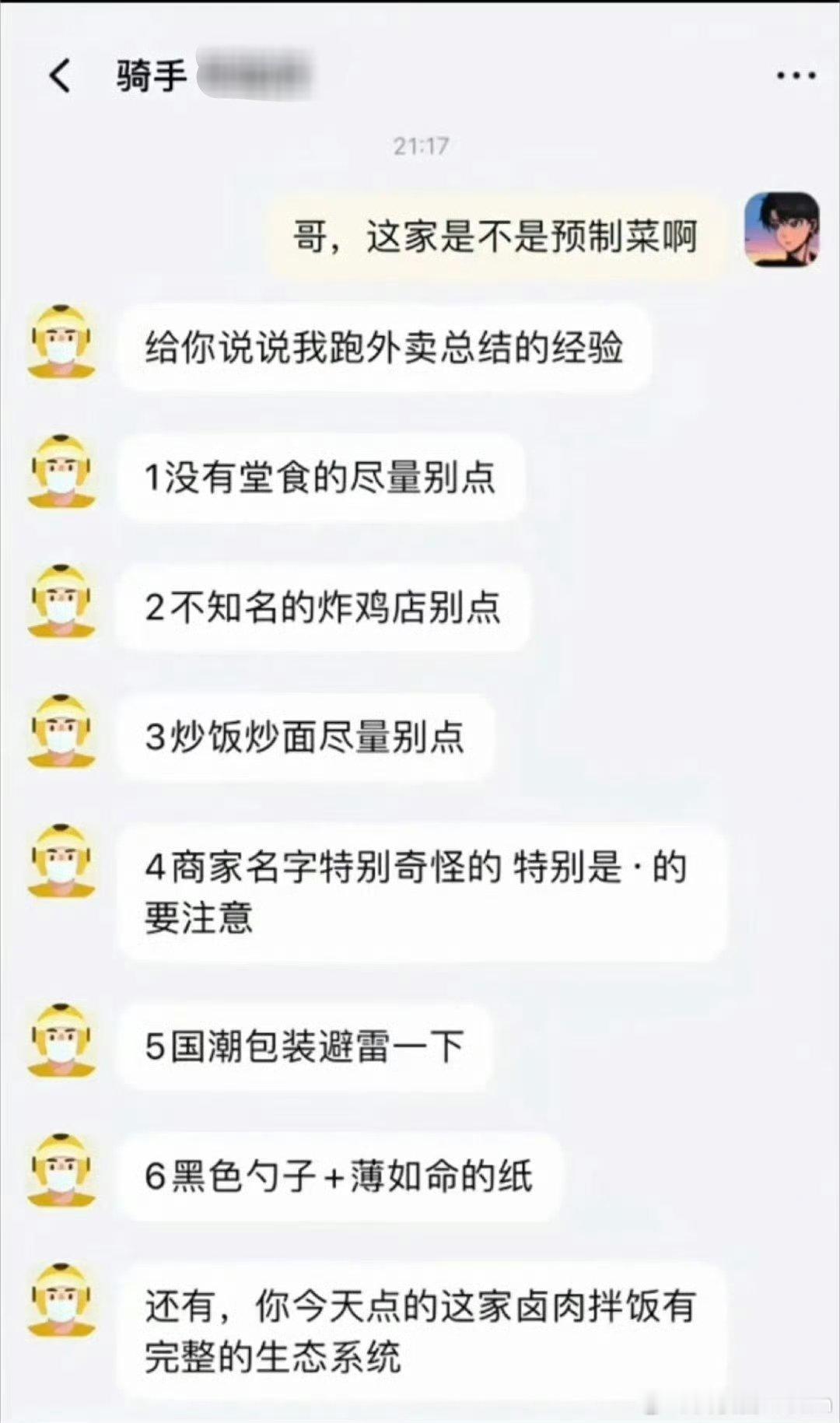六岁时,生产队队长组织本队社员去离家几里地割草,中午大家一起吃大锅饭,热闹场景如若眼前。听母亲说过,以前麦收时节,村里组织村民去割麦子。六岁时,生产队队长组织本队社员去离家几里地割草,中午大家一起吃大锅饭,热闹场景如若眼前。 六岁那年的夏天,日头刚爬到竹梢,队长就扛着铜锣在村口喊:“割草去喽——带好筐子镰刀!”我攥着母亲塞来的小镰刀,木柄磨得发亮,带着她刚纳完鞋底的汗味——那是我对“劳动”最早的嗅觉记忆。 社员们挎着柳条筐,筐沿挂着搪瓷缸子,叮叮当当地走在土路上,惊飞了路边槐树上的麻雀,也惊得我心里的小兔子蹦蹦跳跳。几里地的路,我跟着队伍跑前跑后,看二婶把辫子盘成髻,看三叔用草绳系着裤脚,听他们说谁家的麦子快熟了,谁家的娃昨天摔了泥坑。 到了草地,队长用镰刀在地上划个圈:“这片归咱们!”社员们“呼啦啦”散开,镰刀割过草叶的“沙沙”声里,混着笑闹。我蹲在田埂边,假装割草,其实在追蚂蚱——绿翅膀的,褐身子的,蹦到谁的筐边,谁就笑着把它拨给我。 日头正毒时,炊烟从远处的土灶升起。那口黑铁锅支在石头上,柴火噼啪响,煮着米汤,蒸着玉米面窝头,混着野葱炒鸡蛋的香味飘过来,勾得人直咽口水。队长舀水洗手时喊:“开饭喽!”大家围坐成圈,搪瓷缸子碰着粗瓷碗,有人讲笑话,有人给娃喂饭,我挤在母亲腿边,捧着比脸还大的碗,米汤烫得直缩脖子,却舍不得放。 那时候怎么会觉得割草是好玩的事呢?明明镰刀比我的胳膊还沉,草叶割得手背上一道道红印,可看着筐里的草堆得像小山,听着大人夸“这娃能帮衬了”,心里就甜滋滋的。母亲后来总说,麦收时节比这累多了,割麦子要弯一整天腰,腰都直不起来,可中午的大锅饭最香,新麦磨的面蒸的馒头,就着咸菜都能吃三个。 前几天路过老街,看见几个老人蹲在墙根晒太阳,说谁家孩子结婚请了全村人吃饭,摆了二十桌。我忽然想起那口黑铁锅,锅里的米汤永远冒着白汽,馒头掰开能看见细密的气孔,就像那时的日子——看着苦,嚼着却有麦香。原来所谓热闹,不是人多,是每个人眼里都有光,知道身边的人会把馒头分你一半,会帮你把沉筐子抬上肩。 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沉,梦里全是青草味和柴火烟味。后来长大,吃过山珍海味,却再没尝到过那么香的米汤。不是味道变了,是再也没有那样的场景:一群人顶着日头干活,围着一口锅吃饭,汗珠子掉在地上,都能长出笑声来。 现在我常给孩子讲起那口大锅,他问:“妈妈,你们那时候没有外卖吗?”我摸摸他的头,没说苦,只说:“那时候的饭,要大家一起做,一起吃,才叫饭。”就像现在,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周末喊邻居来家里包饺子,听他们说笑着拌馅、擀皮,蒸汽模糊了眼镜片,恍惚间,又看见六岁那年的土灶边,母亲正笑着往我碗里舀米汤,碗沿上还沾着一粒没擦净的玉米面。
哎哟,听我说个事儿——真是心里堵得慌。邻居一女儿转了五百块给她妈妈,说今年想
【2评论】【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