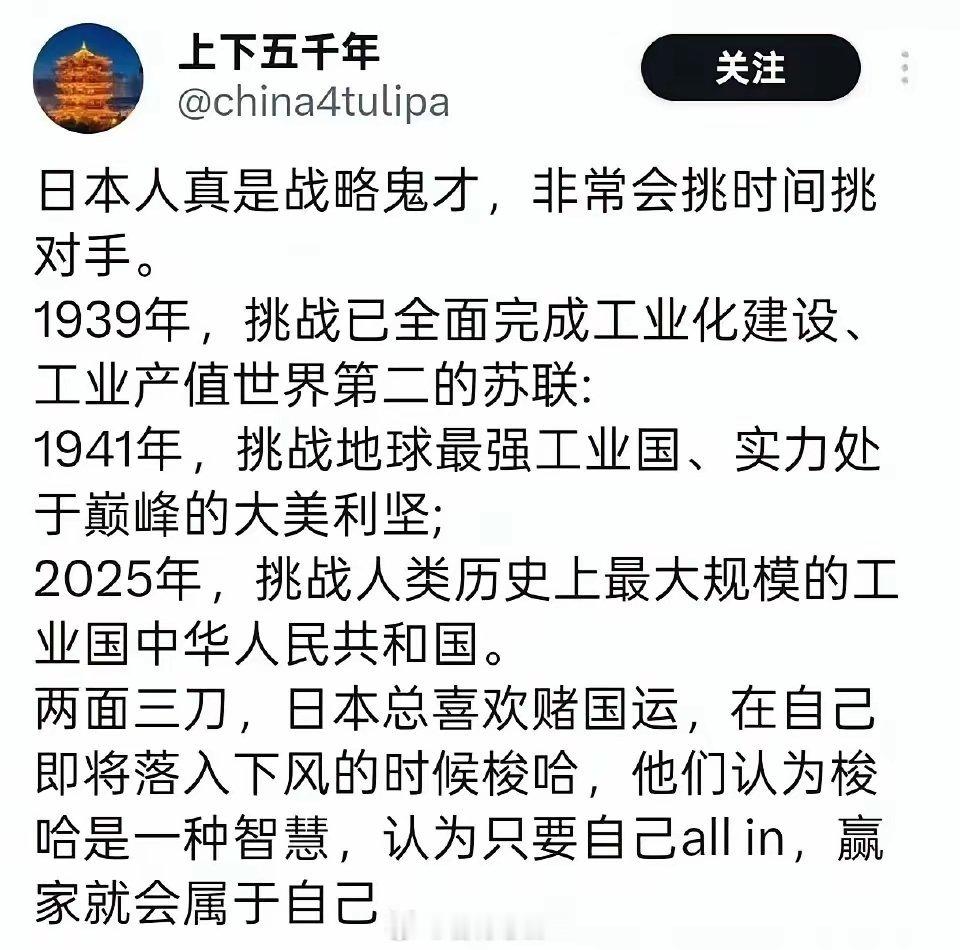莫言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诗人。他宁愿把生他养他的家乡形容成滑溜的肛门和无臭的大便。却要用最美好的诗句,呈现给北海道和北海道生活的人们 这种说法其实是对莫言创作的严重误读。莫言笔下的家乡,是山东高密东北乡——那个他从小摸爬滚打、浸满汗水和泥土气的地方,他写的不是贬低,是剥掉滤镜的真实乡土。 他出生在1955年的高密农村,童年赶上饥荒,跟着母亲去地里挖野菜,亲眼见过饿殍,听过村里老人讲土匪、鬼子的故事,这些刻在骨子里的记忆,让他没法用轻飘飘的美好词汇去粉饰家乡。《檀香刑》里的猫腔戏班、《红高粱家族》里的酒坊和高粱地,还有那些带着“粗粝感”的细节描写,都是他对故土最坦诚的告白——爱一个地方,不是只说它的好,而是连它的伤疤、它的不完美一起接纳。 他写家乡的“不堪”,是因为这片土地养了他,也让他见识了人性的复杂。小时候他跟着爷爷去赶集,见过小贩为了几分钱争执,见过妇女为了孩子偷拿摊位上的糖块,这些琐碎又真实的片段,后来都变成了他笔下的人物。 他在《生死疲劳》里写驴、牛、猪的轮回,用动物的眼睛看高密几十年的变迁,里面有荒诞,有苦难,可字里行间藏着的,是对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敬意。他从不用“优美”“诗意”这类词去包装家乡,因为真正的乡土,从来不是文人笔下的田园牧歌,是带着烟火气、甚至带着“脏”与“痛”的活着。 再看他写北海道的文字,那是完全不同的创作语境。他第一次去北海道是2001年,受日本文学界邀请参加交流活动,走在札幌的街头,看当地渔民出海,听老人讲北海道的开拓史,他写的是异国土地上的人间百态,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是不同文化里共通的对生活的热爱。 他写北海道的雪,写温泉边的对话,写小酒馆里的清酒,这些描写带着新鲜感,却没有刻意美化——就像他写家乡的真实一样,他写北海道,也是写他看到的真实,只是这份真实里,少了他对家乡那份“痛彻心扉”的牵绊,多了几分旁观者的温柔。 把“写家乡的粗粝”和“写北海道的美好”对立起来,本质是没读懂文学创作的内核。莫言的“国际主义”,不是偏爱异国,而是他能从任何一片土地上,看到人类共通的情感——高密的农民和北海道的渔民,都在为了日子奔波,都有对家人的牵挂,都在苦难里找活着的滋味。 他写家乡的“不美好”,是因为他把自己当成了高密的一部分,他有资格剖开故土的肌理;他写北海道的“美好”,是因为他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尊重并欣赏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两者从来不是“厚此薄彼”,而是同一个作家对“人”的关注的不同体现。 那些拿片段文字指责莫言的人,多半没读过他的完整作品。他在《晚熟的人》里写过,“文学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它要揭示人性的复杂”。 高密是他的根,他对根的书写,带着恨铁不成钢的疼,也带着融进血脉的爱;北海道是他看到的世界,他对世界的书写,带着好奇与尊重,也带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这才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诗人”的底色——扎根乡土,却不囿于乡土,眼里装得下家乡的泥土,也容得下世界的山海。 文学的价值,在于直面真实,不管是家乡的真实还是异国的真实。莫言从来没有贬低过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只是不肯用谎言去美化苦难;他写异国的美好,也不是否定家乡,而是展现了人类情感的共通性。真正的国际主义,是懂得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种生活都值得被尊重,这也是莫言作品能走向世界的根本原因。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