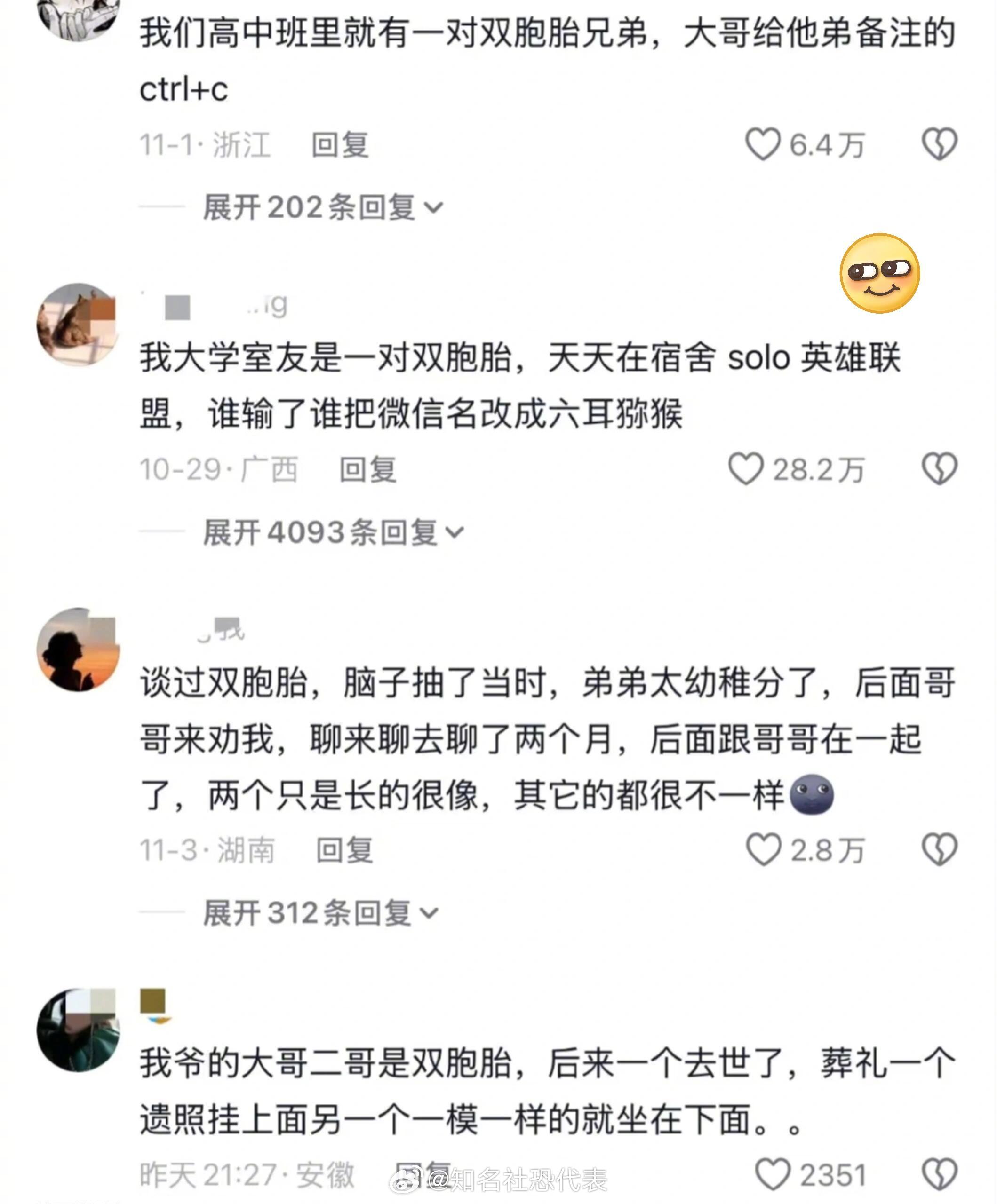1944年,10岁的双胞胎姐妹被送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每周三次她们会被脱光衣服送到一个房间里与一个医生见面,每次时间长达8小时。 约瑟夫·门格勒,这个拥有双重博士学位的纳粹首席医生,并不是在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而是在验证一种狂热的种族幻想,他痴迷于在这些东欧犹太双胞胎身上寻找遗传学的秘密,试图论证所谓雅利安人的优越性。 为此,他从欧洲各地搜罗了约1500对双胞胎,在那个生死由命的火车站台上,那关键的一瞥和轻轻一拉,让这对姐妹避开了直通毒气室的厄运,却把她们推向了更为漫长的炼狱。 父母和姐姐们的背影在混乱的人流中消失,成为了永远的最后一眼,而她们被扔进了为了制造数据而存在的集中营。 作为“对比样本”,双胞胎的生命被死死捆绑在一起,一旦其中一个死去,另一个就没有了活着的价值,必须立刻被杀死进行解剖对比。 这个残酷的潜规则,竟然成了伊娃拼死求生的动力,当那五次不明液体的注射让高烧和四肢肿胀吞噬她的意识时,门格勒只是冷漠地看了一眼体温表,就判了她死刑:“只有两周时间了。” 在那两周里,躺在病床上的伊娃依靠着唯一的信念在与死神博弈:为了不让妹妹被杀,自己绝对不能死。 高烧让她神智不清,她却一次次凭借本能从地板爬向水源,喝水,昏迷,醒来再爬,这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意志力对抗——十岁的孩子在与纳粹的毁灭机制赛跑。 当热度终于退去,门格勒甚至对此感到惊讶,但他并未停止手中的笔,新的折磨随即而来:不打麻药的手术、抽取大量血液、向眼睛里滴入化学试剂试图改变虹膜颜色。 更有甚者,为了观察连体反应,有些孩子被人为地缝合在一起,在伤口化脓的痛苦哀嚎中死去。 1945年1月,苏联军队踏碎了集中营的铁丝网,曾经拥挤着3000名双胞胎的营地,最终只走出了200多个形销骨立的孩子,伊娃和米里亚姆就在其中。 然而,解放并不意味着自由,那个身穿白大褂的幽灵始终在她们的血管里游荡,因为纳粹为了掩盖罪行销毁了绝大多数实验记录,甚至没人知道当年被打进身体里的液体到底是什么成分。 这种由于档案缺失造成的“信息真空”,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虐待,几十年后,哪怕各自有了家庭,噩梦依然在延续。 1963年,身在以色列并怀有身孕的米里亚姆突发严重肾脏感染,医生的诊断揭开了那个被掩盖的恐怖事实:她的肾脏一直停留在了十岁的大小。 1984年,她创立了名为CANDLES的组织,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海捞针,通过一个个电话、一封封信件和报纸广告,她奇迹般地联系上了分布在十个国家的122名双胞胎幸存者。 这是一场与遗忘的对抗,虽然门格勒早已逃亡南美并最终于1979年在巴西溺亡,但他制造的痛苦还在折磨着活着的人,米里亚姆最终因膀胱癌在1993年去世,那永远长不大的肾脏带走了她。 面对这无法愈合的伤口,伊娃在奥斯维辛解放五十周年之际做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决定,她公开宣布原谅纳粹,原谅门格勒。 这一举动激怒了不少同遭磨难的幸存者,但在伊娃看来,这并非是为罪人开脱,因为那些实验档案永远消失了,生理上的伤害无法逆转,如果不放下仇恨的包袱,她就永远被困在了那个10岁时的实验室里,永远是那个等待被测量的受害者。 参考信息: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理想国译丛)》·得到APP书评·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