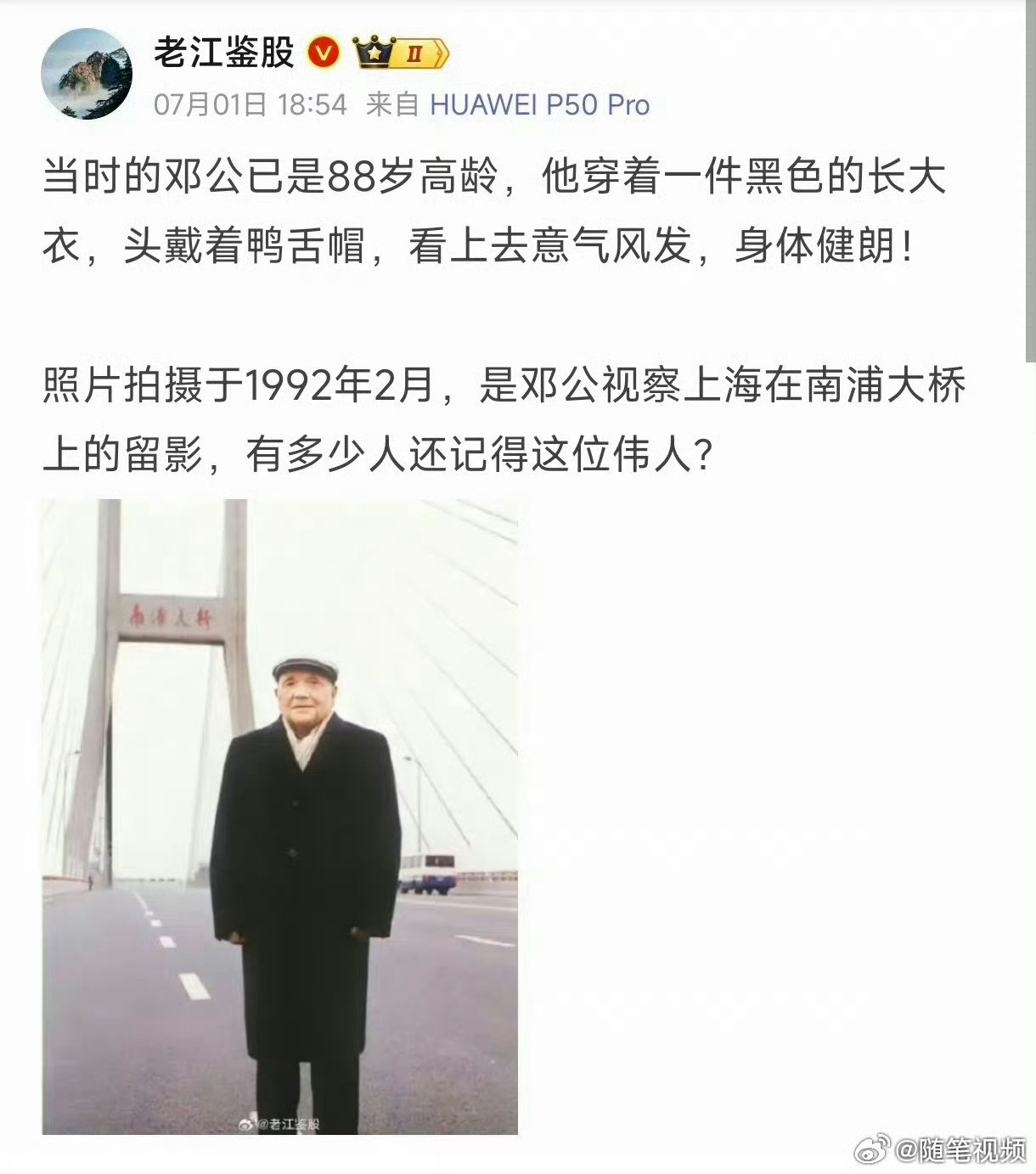1912年,林语堂与厦门巨富的千金陈锦端相恋,不料,陈锦端的父亲却坚决不同意,棒打鸳鸯后,转而将林语堂介绍给了自己的邻居——鼓浪屿首富的二女儿廖翠凤。 1919年,在开往美国的轮船上,林语堂就当着新婚妻子廖翠凤的面,他把那张红纸化为灰烬,笑着说这东西只有离婚才用得着,咱俩这辈子用不上。 林语堂最初的心尖人,是厦门巨富陈天恩的女儿陈锦端,那真是郎才女貌,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草”才子,一个是圣玛利亚女校的绝色佳人。 两人情投意合,美得像画,但这也就是个“像”而已,陈老爷子是实业家,看人毒得很,欣赏林语堂的才华是一回事,嫁女儿是另一回事,一句“门不当户不对”,就把这穷牧师的儿子拒之门外。 更绝的是这位陈老爷子的操作——他一边棒打鸳鸯,一边转身充当起了红娘,把隔壁鼓浪屿首富廖家的二小姐廖翠凤介绍给了林语堂,我不嫁女儿给你,但我邻居合适你。 面对父权的重压,被林语堂视为“白月光”的陈锦端躲在楼上不敢下楼,自始至终沉默以对,而邻居家的二小姐廖翠凤,长相虽不如陈锦端惊艳,性格却泼辣通透。 当廖母嫌弃林语堂家里穷,抛出那句著名的厦门俗语“哪有吃白米饭的大户人家,嫁给吃稀饭的穷人家”时,廖翠凤没有退缩。 她那个年代的大家闺秀,能为了一个穷小子硬刚自己的亲妈,只回了一句:“穷有什么关系?人家是大学生,将来会有出息的。”就这六个字,把林语堂那颗被陈家碾碎的自尊心,一点点拼了起来。 这婚是结了,但廖翠凤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林语堂带着“情话”烧了婚书,转头就把日子过成了真正的“稀饭”模式。 两人到哈佛求学,后来又去德国,奖学金断了,生活费没了,这位昔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首富千金,没发一句牢骚,默默把带来的嫁妆、首饰一件件当掉换米面,甚至出去打工贴补家用。 她在变卖首饰支撑这个家的时候,林语堂心里其实还住着那个“白月光”,这才是这段婚姻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廖翠凤对此心知肚明,但她玩出了一种让人高山仰止的境界。 林语堂晚年爱画画,笔下的仕女永远梳着一样的发型,留着长发,别着个宽夹子,女儿不解,林语堂竟毫不避讳地说:“锦端的头发就是这么梳的。”换个心眼小的妻子,这画架子早被砸了。 廖翠凤倒好,她不仅允许丈夫心里的这块“自留地”,甚至在回到上海定居后,还大方地邀请陈锦端来家里吃饭。 当孩子们看到父亲听说陈锦端要来时那种坐立难安的紧张劲,感到困惑不解时,廖翠凤却能坦然地笑着解释:“没办法,你爸爸以前爱过锦端阿姨。”她甚至跟女儿说了句极有分量的话:爸爸爱的是锦端,但最后留下来陪他熬日子的,是不嫌他穷的廖翠凤。 这不是无奈,这是王者的底气,她太清楚了,所谓的“爱情”可能是一道精致的点心,让人回味;但“婚姻”是一碗扛饿的白米饭。 陈锦端成了林语堂画里的影子,美好但虚幻;而廖翠凤把自己变成了林语堂离不开的血肉。 陈锦端后来的人生充满了遗憾的底色,她拒绝了父亲安排的婚事,只身去美国留学,直到32岁才嫁人,终身未育,当年的退缩,让她成了林语堂心中永远的痛,也成了自己一生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