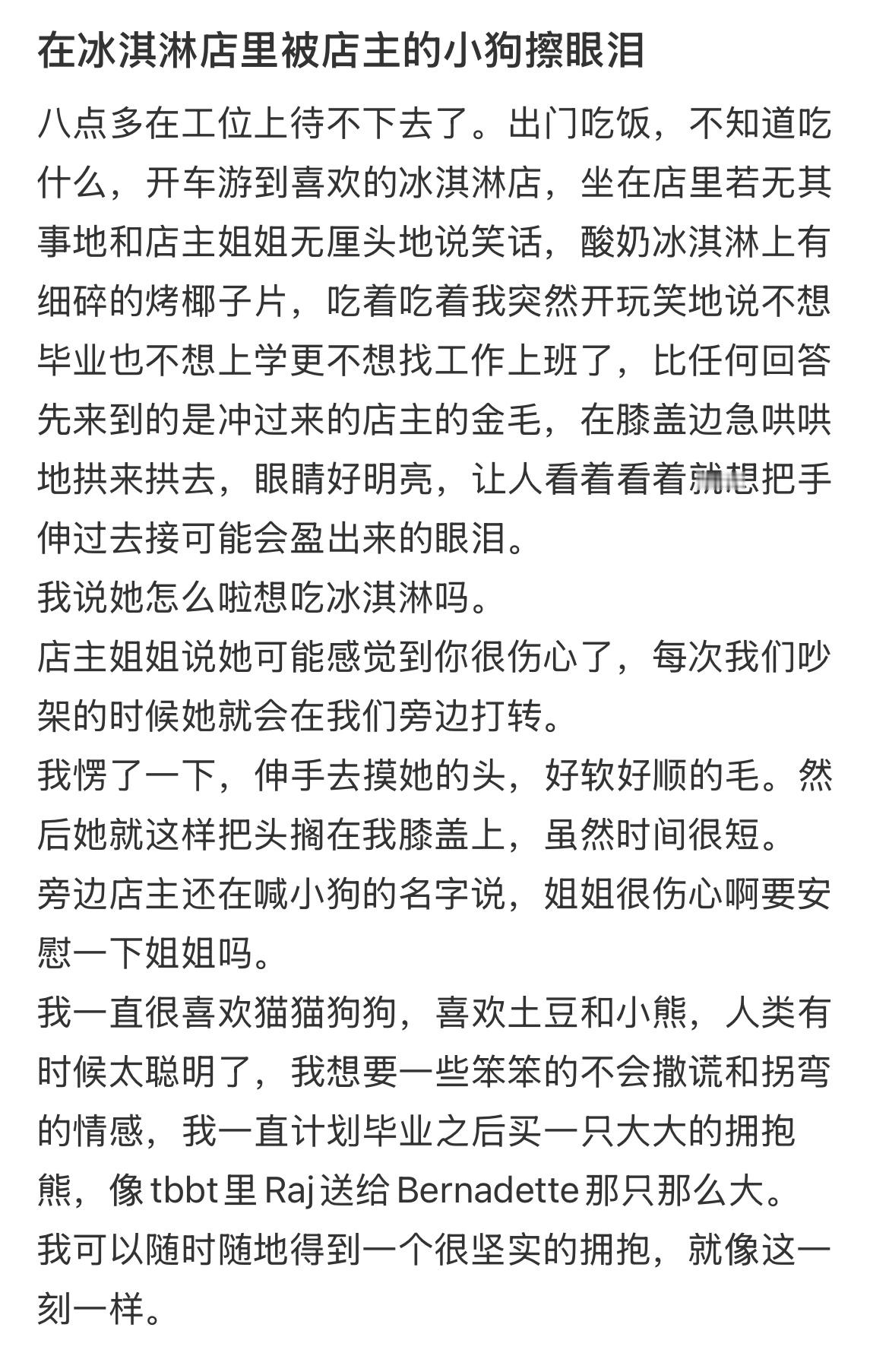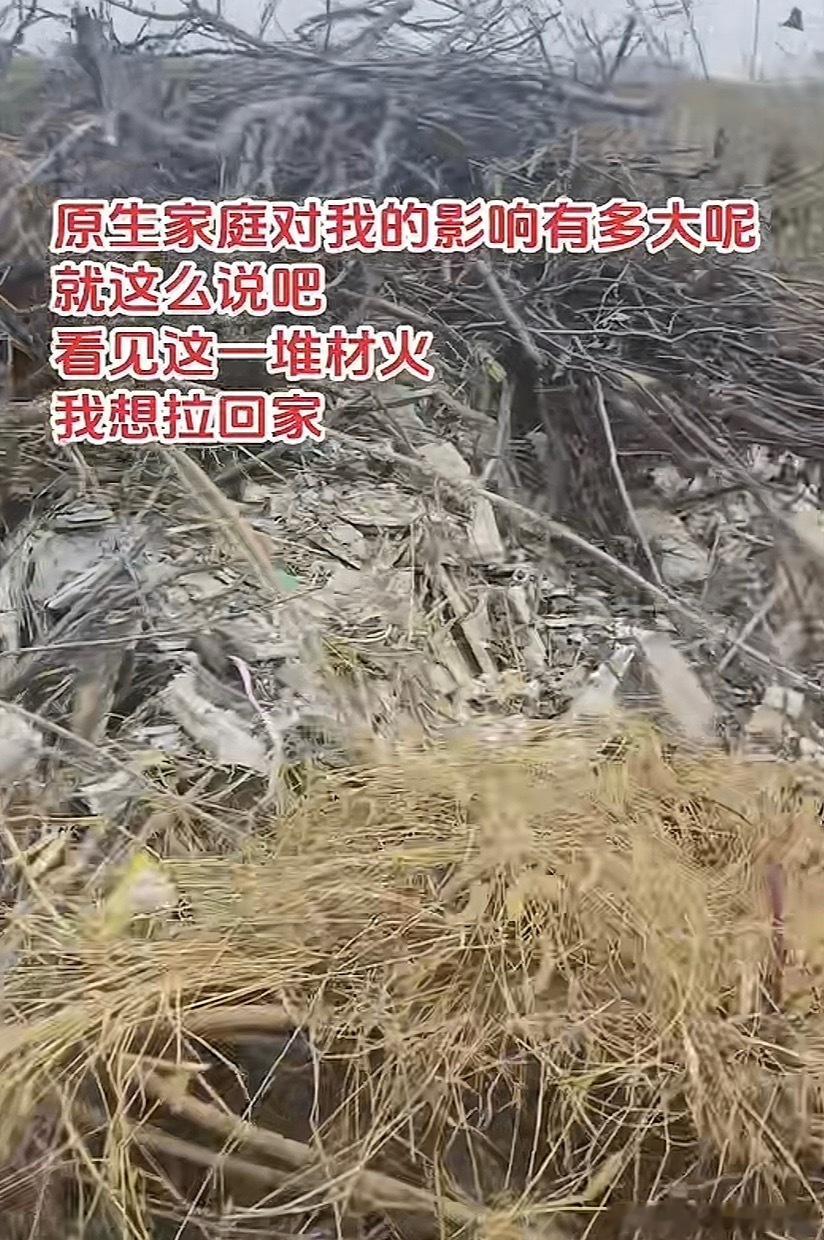我和我老公都是普通的打工人,每个月挣得不算多,可能是因为我俩原生家庭条件都一般,从小就看惯了父母精打细算的日子,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养成了特别节约的习惯,一分钱总想掰成两半花。 现在这物价,说句实在的,不省真扛不住。早上赶去菜市场,摊主喊“青菜三块五一斤”,我俩得蹲下来翻一翻,挑那种带点小黄叶但还新鲜的,再跟摊主磨两句:“凑个整,三斤十块行不?”不是抠,是知道这一块钱省下来,晚上能多买个鸡蛋给孩子煮着吃。 厨房吊柜里那个掉了瓷的搪瓷盆,是结婚时婆婆给的。 沿儿上磕出的豁口,正好能卡住塑料袋提手——这是我俩“省”出来的默契,从恋爱时挤在出租屋煮泡面就开始了。 早上六点半的菜市场,露水还挂在青菜叶子上。 老公牵着我的手往最里面走,那里的摊主熟,砍价时不会翻白眼。 “青菜三块五一斤”,穿蓝布围裙的阿姨扯着嗓子喊,手里的水瓢往菜堆上一泼,水珠溅到我鞋面上。 蹲下来翻青菜时,手指会先捏捏菜帮。 硬邦邦的不买,得是那种捏上去有点软,但叶子还支棱着的——这种带点小黄叶的,水分没跑,回家摘吧摘吧照样新鲜。 老公蹲在另一边,把挑好的青菜摆成小堆,数了数,正好三斤。 “张阿姨,”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比平时低半个调,“三斤凑个整,十块钱行不?” 阿姨拿水瓢敲了敲菜筐沿,“你们小年轻,比我还会算。” 但手还是麻利地把菜装进袋里,又抓了把香菜塞进来,“下次早点来,头茬的嫩。” 提着菜往家走,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红。 老公突然说:“刚才看见隔壁摊位的鸡蛋打折,晚上给孩子煮茶叶蛋吧?” 我没应声,只是把他的手往自己这边拽了拽——他袖口磨出的毛边,在晨光里晃得人眼睛发酸。 小时候放学回家,总能看见爸爸坐在小马扎上,对着台灯算账,铅笔尖在纸上戳出小洞,嘴里念叨着“这个月电费省五块,下个月就能给你买本新字典”,那时候不懂,只觉得爸爸的眉头像打了死结的绳子,现在自己握着菜市场的塑料袋,才知道那绳子的另一头,拴着一个家的温度。 偶尔会有年轻摊主笑我们“老人家才这样挑”。 老公总是挠挠头不说话,但我知道他口袋里揣着孩子幼儿园的缴费单,边角都被手汗浸得起了毛边。 有次孩子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买东西要讲价呀?”我蹲下来捏捏他的脸,“因为妈妈想把省下来的钱,都变成你书包里的新文具,和晚上碗里的荷包蛋呀。” 今天省的一块钱,晚上孩子碗里多了个流心的荷包蛋。 他举着勺子歪头看我,蛋黄液滴在桌子上,像朵小黄花。 这种日子过久了,孩子会举着半块馒头说“妈妈,这个掰给你,我们明天再买”,会把喝完的牛奶盒踩扁了塞进回收袋——原来“省”不是教他抠门,是教他看见每样东西里藏着的心意。 现在那个搪瓷盆里,偶尔会躺着孩子画的画。 歪歪扭扭写着“爸爸妈妈辛苦了”,旁边画了两个小人,手牵着手,手里都提着菜篮子。 你说,这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算不算另一种富裕? 至少在我心里,比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更踏实——因为每一分省下来的钱,都带着菜市场的烟火气,和我们仨的心跳声。
我和我老公都是普通的打工人,每个月挣得不算多,可能是因为我俩原生家庭条件都一般,
好小鱼
2025-11-28 17:47:46
0
阅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