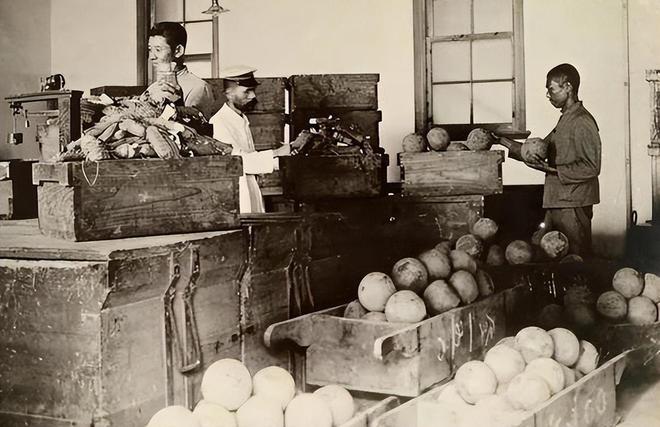1946年,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奉命开赴东北剿匪,在围剿牡丹江土匪时,杨子荣站出来说:“你们等着,我进村子去说降土匪!” 杨子荣这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江湖”。 他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在山东牟平。那时候山东穷啊,活不下去了,1929年,才12岁的他就跟着爹妈去闯关东。到了安东没多久,父亲累死了,母亲带着妹妹回了山东,就把他一个人扔在了东北这片黑土地上。 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在那个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年代,孤身一人怎么活? 为了讨口饭吃,他去丝厂当童工,去鸭绿江上当船工,甚至还下过阴暗潮湿的煤矿。这14年的底层摸爬滚打,没把他压垮,反倒把他炼成了一块“铜豌豆”。他熟悉了东北的三教九流,学会了各行各业的“切口”,甚至连土匪那一套行帮礼节都门儿清。 1945年,抗战胜利了,29岁的杨子荣在老家牟平参军。你说巧不巧,他最开始是个炊事员。但他这个炊事员不安分,送饭的时候看着战友打仗心痒痒,经常撂下饭勺就拿起枪。 部队首长很快发现了这个“宝藏老兵”。1946年3月,那场著名的杏树底村战斗打响了。 当时的情况非常棘手。土匪头子李开江纠集了400多号人,占据了杏树底村。这帮土匪把村子围得像铁桶一样,还有高墙和工事。咱部队虽然有炮,但村里全是老百姓,这炮一响,土匪是死了,老百姓也得遭殃。 僵持不下的时候,杨子荣站了出来。他跟营长说:“别打了,我去说说看。”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对面是400多条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杨子荣拿了一条白毛巾挥舞着,一个人就这么翻出了战壕,向村里走去。 这就是胆色。他进村后,并没有像愣头青一样硬劝,而是玩起了心理战。他发现土匪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头目是外地流窜来的,像许大虎、王洪宾,这帮人最凶,叫嚣着死磕;但还有两个头目郭春富、康祥斌是本村人。 杨子荣抓住这一点,直接攻心:“你们看看,外面大军压境,大炮都架好了。你们要是真打,这村里的老少爷们儿,还有你们自己的爹娘老婆,全得跟着陪葬!” 这话像锥子一样扎进了本村土匪的心窝子。两拨土匪当场就吵了起来,最后本村土匪占了上风,哗啦啦就把枪扔了。那两个外地悍匪一看大势已去,也只能垂头丧气地投降。 这一仗,杨子荣不费一枪一弹,单枪匹马劝降了400多个土匪。他也因此被评为战斗模范,升任了侦察排排长。 但这还不是他最传奇的一战。真正让他封神的,是收拾那个老奸巨猾的“座山雕”。 “座山雕”本名张乐山,这老家伙可不简单。他历经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朝代,当了50多年的土匪,是个真正的“山大王”。他在深山老林里极其狡猾,连当年的日本人都拿他没辙。 1947年1月,部队得到线索,“座山雕”就躲在海林北部的密林里。大部队进山肯定不行,惊动了这只老狐狸,他往林海雪原深处一钻,神仙也找不着。 团里决定,让杨子荣带5名侦察员,扮成土匪进山。 这一趟,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们在大雪封山的老林子里转了好几天,才在蛤蟆塘找到个工棚。杨子荣一进屋,先不说话,用土匪手势和黑话试探。这一套流程下来,真就把里面的眼线给蒙住了。 有个叫孟工头的,答应给他们引路。但这帮土匪太谨慎了,把杨子荣他们晾在一个空棚子里,饿了三四天,只给吃苞米面。这就是在熬鹰,看你露不露马脚。 杨子荣沉得住气。等到孟工头带着“座山雕”的副官来盘道时,杨子荣对答如流,把那个想投奔山头的落魄土匪演得活灵活现。对方彻底信了,还要带他们上山入伙,过元宵节。 这一路上,“座山雕”设了三道哨卡。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就趁机把哨兵给绑了,一直摸到了“座山雕”的老巢,一个叫“马架房子”的木棚。 杨子荣带着两个战士冲进棚子,枪口直接对准了里面那七个土匪。坐在中间那个白头发、鹰钩鼻、留着山羊胡的小老头,正是“座山雕”。 这老匪首还没反应过来,手刚要去摸枪,杨子荣一个箭步冲上去,大脚一踩,枪就被缴了。杨子荣随后还得演戏,骂骂咧咧地说:“三爷,你不讲究啊,让我们兄弟在山下差点冻死饿死,我们是想去吉林投国军,路过宝地想借个道,你这是待客之道吗?” “座山雕”一听这满口的黑话和抱怨,还真以为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刚想解释,就被五花大绑了。 这一仗,又是兵不血刃,活捉了包括“座山雕”在内的13名悍匪。东北军区直接授予杨子荣“特级侦察英雄”称号。那一年,报纸上全是他的名字。 就在活捉“座山雕”仅仅十几天后,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在追剿另一股土匪李德林、郑三炮时,悲剧发生了。 那天凌晨,在闹枝沟,杨子荣带头冲向土匪的窝棚。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成了最大的杀手。当他扣动扳机时,枪栓因为太冷被冻住了,没打响。 就在这一瞬间,土匪孟老三的一颗子弹从屋里射出来,正中杨子荣的胸膛。 他倒在了雪地上,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那年,他才30岁。 如今,在海林市的杨子荣烈士陵园里,松柏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