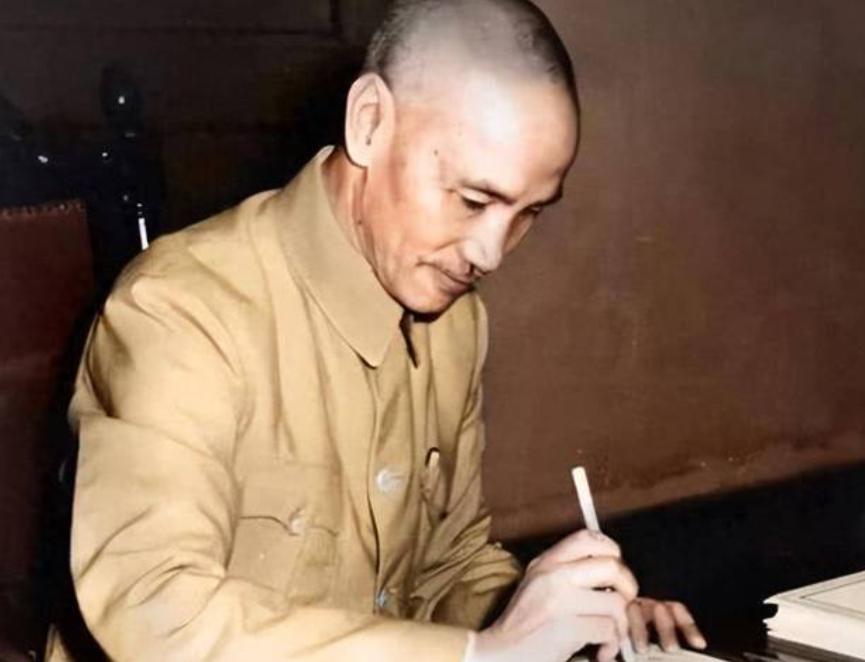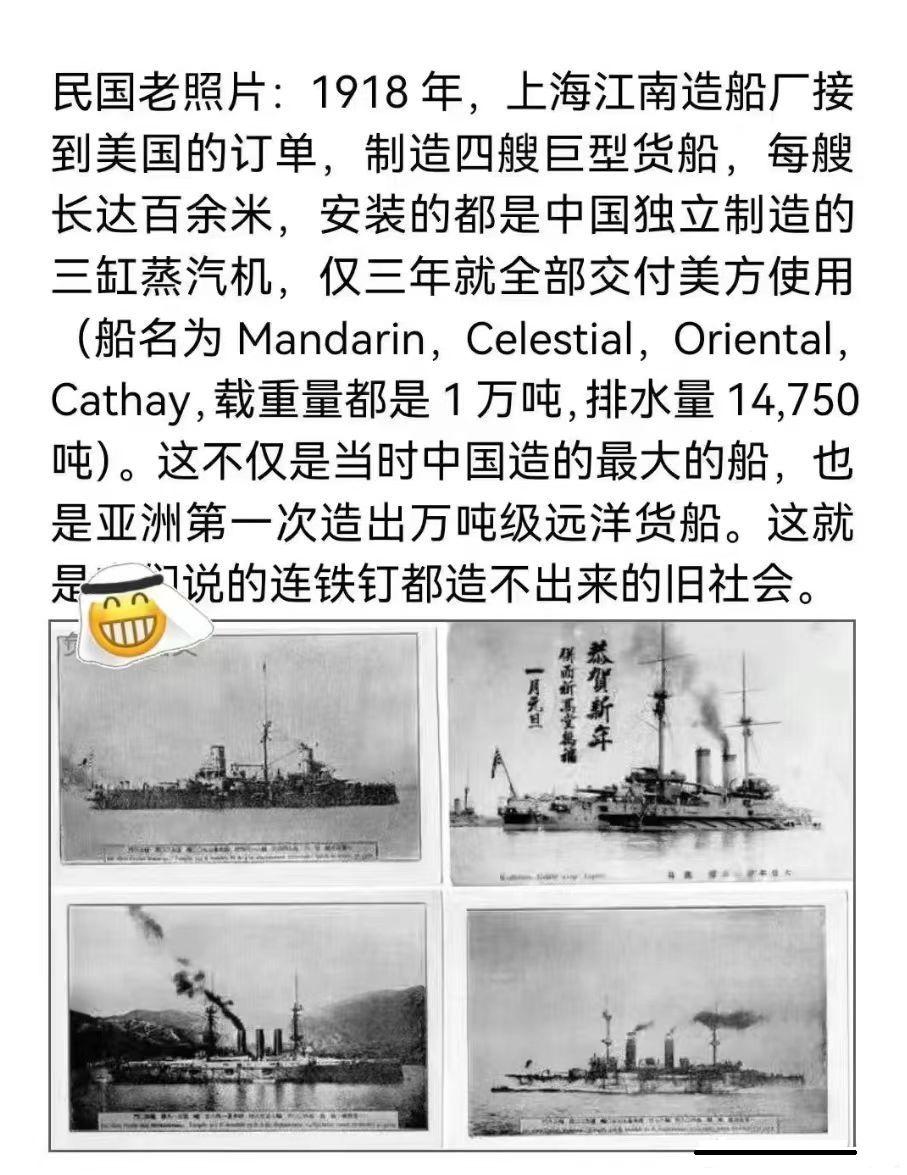1937年夏,上海滩硝烟滚滚,街头尸横遍地。 江阴要塞的布防图刚画上军令纸,日军的军舰却已提前撤离,原定的“瓮中捉鳖”成了一场空。 蒋介石站在作战沙盘前,手握铅笔,久久不动。 他看向角落,那个低头做记录的男人,面无表情,字迹工整。他叫黄浚——行政院的高级机要秘书,也是这场泄密风暴的中心人物。 但此刻,他是“自己人”。 谁都不知道,一天前,在玄武湖边,一名穿长衫的中年男子一边嚼着巧克力,一边将糖纸塞进一棵老槐树的树洞。 不远处,一个拄伞的青年假装在喂鸽子,眼角始终不离那棵树。一小时后,糖纸被取走,三天后,日本70余艘军舰脱离战线,长江防线漏洞百出。 没有人能解释,为何敌人每次都能踩准国军节奏。 冯玉祥在车上刚转弯,敌机便如影随形;宋美龄慰问途中遇袭,爆胎的吉普车冲进水沟;白崇禧刚刚回头转身,先施公司便被炸成平地。 几乎所有“刺杀”都精准得像剧本,每一颗炸弹都仿佛安在地图的“圈重点”上。 “这不是普通间谍能办到的。”蒋介石终于开口。 调查的焦点落在黄浚身上,不只是因为他每次会议都在场,更因为他的生活过于奢靡——南京、上海皆有宅邸,夜夜笙歌,交际广泛。 最要命的是,他的钱从哪里来,没人说得清。他那位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须磨弥吉郎,早已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也正是日本特高课在华的最高指挥。 黄浚的罪,从巧克力纸开始,但远不止巧克力纸。 他训练了一整套谍报系统,换帽子、藏情报、转手交接,一丝不乱。他甚至将儿子安插进外交部,再通过司机、小妾、书童,布下一张看不见的网。 专案组布下反围套,一个假情报从咖啡馆的礼帽中递出:“明晚11点,黄公馆聚会,须磨先生亲自发奖金。” 黄浚果然上钩,邀来间谍网中的十八名骨干。那夜,黄家灯火辉煌,客厅香槟声未落,门铃响了。 不是须磨,是枪口。 宪兵破门而入,十八人被一一按倒在地。黄浚被拷在审讯椅上,脸色苍白。 他交代了所有事——从1931年开始的投敌,到炮台图纸的外泄,再到刺杀计划的精确位置。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却句句刺骨。 一周后,南京雨花台。十八名汉奸站成一排。黄浚穿着旧长衫,眼神木然。身边是他年轻的儿子黄晟,戴着手铐,低头不语。 枪响的一瞬间,那个曾出入高层会议、写诗作赋的“神童”,终于倒下。他的身躯跌在尘土里,和那些因他出卖而死的将士,再无区别。 而战场上,淞沪依旧在燃烧,炮火未歇。国军将士不曾知道,他们原本可以赢得更多的胜利,少流那么多血。 可惜,那场胜仗,被一个糖纸和一顶礼帽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