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一个寒冬的傍晚,南京市郊老干部医院病房的灯光昏黄。 一个瘦削的老人靠在病床上,眼神已渐模糊,他拉住女儿的手,嘴唇微动:“我走以后,别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个也不要。”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没再睁开。 医生记录上写着:“沈志宏,退休后勤科干部,病逝,享年79岁。” 没有头衔,没有战功纪念,甚至连“烈士家属”通知都没人来送。 可谁又能想到,这个“无名老人”,曾在战争最暗的角落,亲手为解放军打开过南京的城门? 沈志宏出生在河北定县一个普通书香门第,家中做些小生意,父母指望他读书成才,将来当个老师、写几本书,养活家人。 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考上了北平的高等师范,主攻哲学。他本该是一个“之乎者也”的教书匠。 可1937年卢沟桥事变那天,他在课堂上听到窗外炮火震天,整栋教学楼都在颤抖。 “读书人若不能护国,读这书又有何用?” 那一夜,他收拾行李,没跟家里打招呼,只留下一封信:“孩去从军,保国护家。” 20岁出头,他南下投奔武汉临时政府,几经辗转进了中央军校第十四期,和一批留学生、文人子弟一起接受训练。 他不是最强壮的那一个,却是最冷静、最沉得住气的人。 抗战期间,沈志宏被编入第91师当情报参谋,战场上的信息收集、敌军动向预判、地图分析都要经过他。 他不爱讲话,却总能精准判断日军的进攻点,被士兵们戏称为“预言家”。 有一次,前线指挥部犹豫是否放弃一个小村落,他用一张徒手画的地形草图说服上级:“这里是通往老河口的咽喉,丢了它,等于拱手让敌人穿胸。” 结果三天后,敌军果然集中兵力猛攻,被早早布防的部队反杀。 这一战后,他被调往后方军政司做信息协调,不再上前线,但他的名字却开始出现在国防部高层的桌面上。 而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面对的,不是敌人的子弹,而是友军的怀疑。 1943年冬,南京郊外执行一次小型任务时,他亲眼看着部队误将三个地下党当作“日伪特务”枪决。 理由仅仅是:三人没带证件、口音不对、神色紧张。 回到驻地,他调查了整整一周,才发现这三人正是中共安插在沿江地区的情报员,他们本想将敌人布雷点的图纸转交给皖东支队,结果路上被拦截,话没说完就被“清理”。 当天晚上,他第一次在军帐中失声痛哭。他问自己:“我们到底在打谁?” 1946年,抗战胜利,沈志宏被调至南京,进入国防部一厅担任中校参谋,主要负责长江以南的防御图纸汇总和敌情上报。 这在旁人看来,是高升,是“熬出来”的成果。 可他却越干越心寒。军政厅每天有人开香槟、赌钱,报纸上却写着“剿匪胜利”“民心归附”。 身边同事多是太太团亲戚、某将军外甥、某议员之子,没人真在乎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每天汇总的情报,根本没人看,他们在意的是哪家饭馆新开张。” 他没辞职。他选择留下,变成一颗“会转的钉子”。 一次偶然的接触,他和一位老战友谈及往事,那战友低声说:“我已经入了组织,他们还需要像你这样的人。” 他没有立刻答应。他沉默了一整个月,直到那天,他看见街头一个乞丐模样的中年人被宪兵暴打,只因为他口袋里掉出一页《新华日报》。 那一夜,他主动联系了那位战友,说:“我愿意帮忙。但我只负责送东西,不写名字。” 1948年冬,南京城内布防加紧,长江防线重新布图,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共军过江,南京危矣。 国防部新设江防图管控室,门禁极严,三层守卫,进出要两人以上同行,每张图纸都有编号登记。 沈志宏就在那批负责“编号”的人里。 他知道,共军想渡江,必须知道布防图的精确位置。每一个铁丝网口、地雷带、碉堡盲区,哪怕出错十米,也可能让上千人丧命。 于是,他和妻子江丽文商量了一整夜。 江丽文,是一位小学教员,温柔、谨慎、目光清澈。可她却比他更果断:“如果你决定了,我陪你。” 他们合谋了整整五天。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在老旧宿舍楼里拆掉地板,藏好工具,准备复制图纸的材料。 偷图那晚,沈志宏以“整理旧档”为由拖延值班同事,趁隙进入密室,用特制微型相机拍下每一页图纸。 拷贝成功后,他把相机藏进了妻子绣花鞋的鞋底。 江丽文第二天背着女儿,去“探亲”,途中将相机交给了接头人。 一周后,南京战役打响。解放军攻城速度之快,连内部人都不敢相信。 “像是对方拿了地图一样……” 没人知道,他们真的“拿了”。 南京解放后,沈志宏没有提过往。他转去后勤,做仓库管理员,一干就是30年。江丽文则成了街道妇联干事,每天跑腿送米送油。 他们没有被授勋、没有进烈士堂,甚至家里连一张证书都没有。 直到1990年代末,党史馆整理地下工作者资料,辗转找到他家门口时,他冷笑了一句:“找错人了。” 1996年冬,他病危,最后一句话,是对女儿说的:“他们有孩子,有家人,有人还活着,不该因为我死了就被人盯上。” 他就这么走了,一生干净,像从没参与过风云激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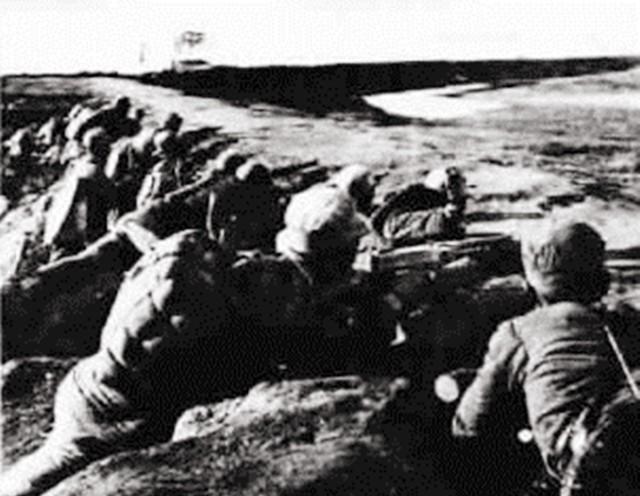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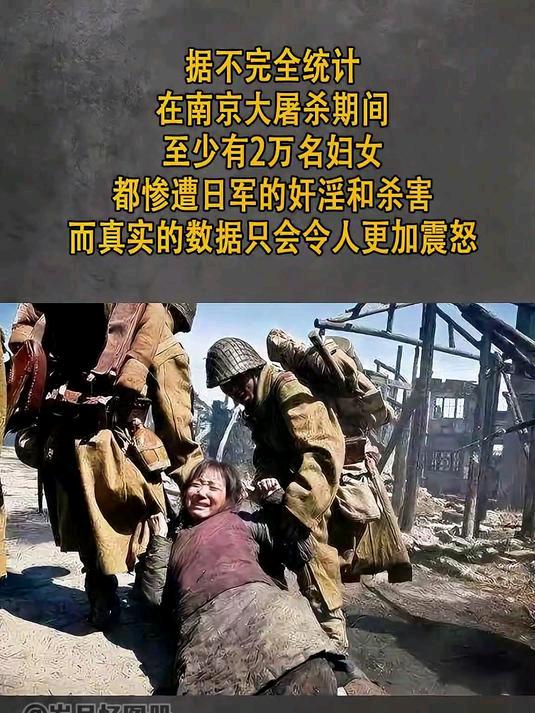

用剑的叮当
他们是谁啊
用户10xxx38
96年还怕啥
江东豪客 回复 12-02 07:18
余则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