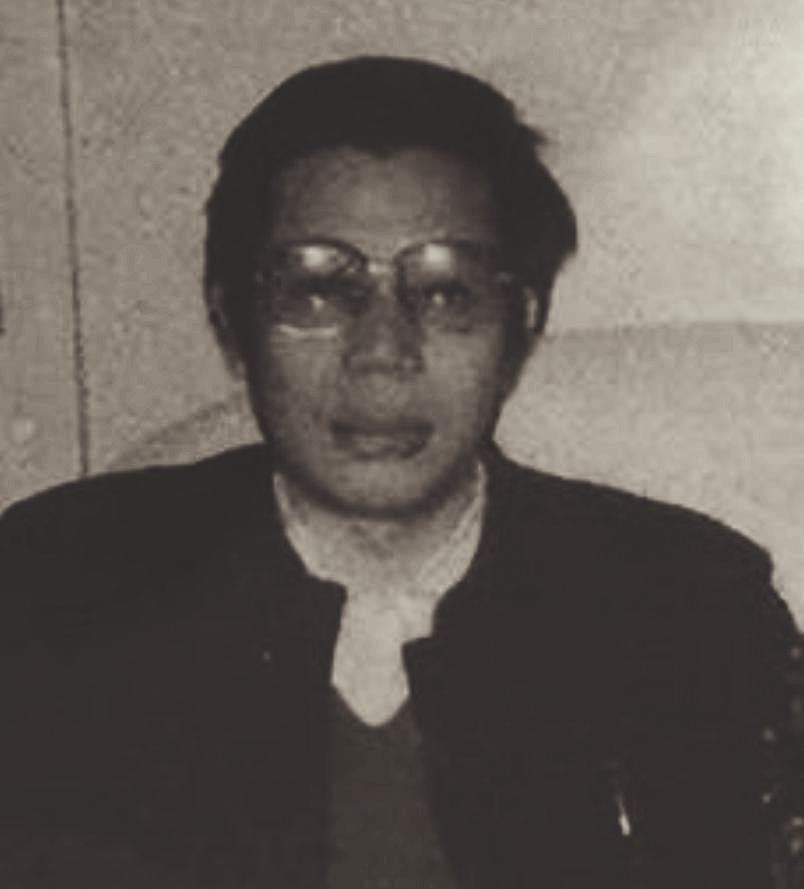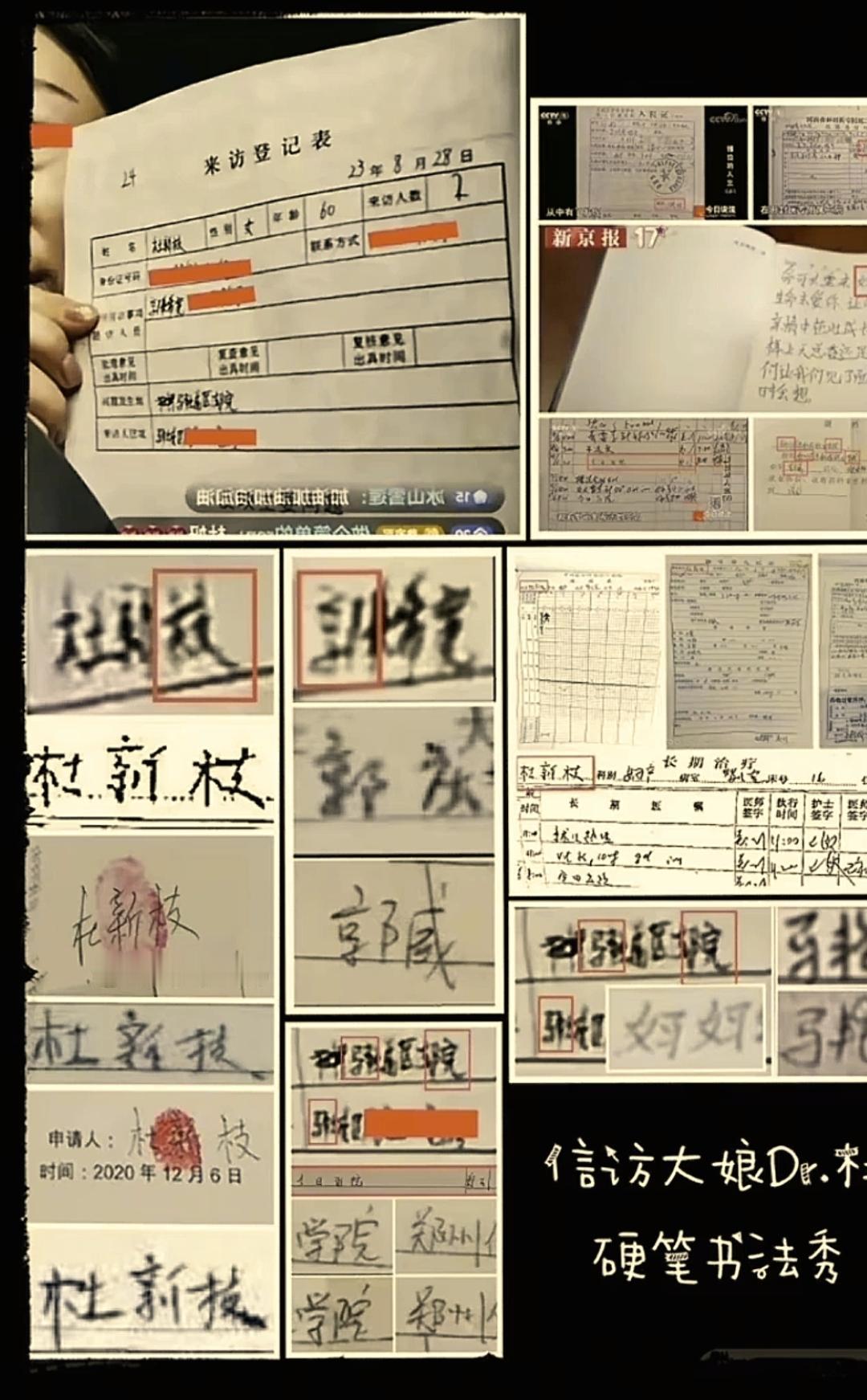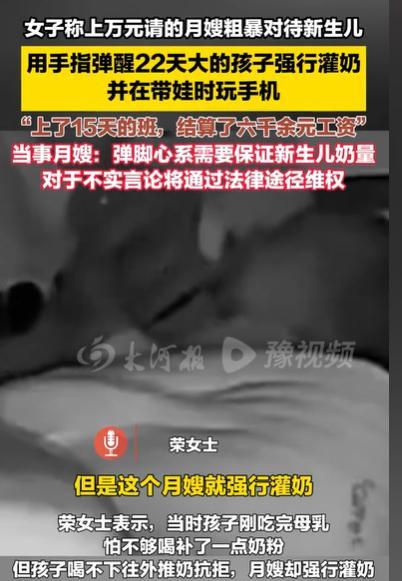1985年5月的一个傍晚,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开完军委会议回到家里,把保姆小刘叫到身边,保姆以为将军要交代家务事,没想到这位七十岁的老将军低声问了一句:“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张铚秀回到昆明军区家中的那个夜晚,风带着山里的凉意,吹得院子里的树叶哗啦啦响,这个刚从北京开完军委会议的将军,推开家门时,屋里安静得只有钟表滴答声,他脱下军帽,放在桌上,转身看见米缸空了,冰箱里只剩几根干瘪的葱。 他是正军级干部,工资每月三百多元,在当时已算高收入,但这笔工资,在他手上从来没有“捂热”过,刚到账,就飞快地“出门”:寄给瘫痪在床的老战友,汇给烈士遗孤的学费,送去老家修桥补路的乡亲手中,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唯独没留多少给自己。 张铚秀出生在江西永新,家里世代是佃农,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母亲靠给人洗衣服拉扯几个孩子,13岁那年,他差点饿死,是村里人东拼西凑给了几口饭,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从那时候起,他就记住一句话:有饭吃,就得想着让别人也吃上。 1933年,他参加红军,第二年,开始长征,腊子口战斗时,子弹擦着他的额头飞过,血糊满脸,他昏倒在雪地里,战友们轮流背着他翻山越岭三天三夜,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醒来后,手里攥着半块青稞饼,没舍得吃完,掰给了另一个伤员,那一刻,他才知道,命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是大家一起拼出来的。 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带兵打仗,最难忘的是皖南事变,那次突围,他身后是一千多战友的遗体,身边只剩下200多人,他带着这些人,在深山老林里挤在一起,一边躲追兵,一边找水喝,有人问他:“还打不打?”他咬着牙说:“活下来,就不能让死去的人白牺牲,”从那以后,他心里就默默立了个账本:谁的牺牲,他都要替他们扛着。 解放后,他当了师长,调进昆明军区,1979年对越作战,他临危受命,指挥云南方向的战事,那时,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被送上前线,有人劝他:“你家都上了,太冒险,”他没说话,但心里有杆秤: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我家的也不能躲,他没告诉任何人,孩子们上战场前,他偷偷在背后看了几眼,转身擦了眼角的湿气。 战事结束后,他升任司令员,有人以为他会开始过上“将军的日子”,但他的生活跟普通战士没两样,家里的沙发用了快30年,弹簧塌了,他拿块三合板垫上接着用,太太丁亚华出身名门,祖上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可她常年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从没一句怨言,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他的钱,都花在更重要的地方了,” 家里常年住着十来口人,有从老家来的侄子,有牺牲战友的孩子,还有下属的家属,饭桌上坐得满满当当,一顿饭下来,米缸见底,有人问他:“这样不累吗?”他只是笑笑,把饭碗端到孩子面前,他觉得,这些人,是命运给他留下的责任。 1985年,中央宣布百万大裁军,当张铚秀听说昆明军区要撤销时,他沉默了很久,这支部队刚打完仗,立了功,墙上还挂着血染的锦旗,他原以为别的军区要并入昆明,结果反了过来,会场上,他掐着文件许久没说话,最后站起来,带头签了字,他说服干部、安抚官兵,干脆利落地制定三条规矩:不伸手、不干扰、不添乱。 有人不服,觉得堂堂一支主力部队,说撤就撤,太憋屈,他却说:“命令就是命令,当年我们冲阵地的时候,没时间讲委屈,”他每天打电话安慰老部下,晚上还要翻看转业安置的名单,生怕谁被漏下,那段时间,他连家里米缸空了都没顾上,还是保姆偷偷告诉别人,才有人送来一袋米。 张铚秀退休后,生活更加节俭,他早上六点起床打太极,中午准时午睡,吃饭从不浪费,剩菜剩饭,他总是热一下再吃,每月的退休金,大部分继续流向老家的困难户、战友的后代、需要帮助的孩子,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破旧的咸菜罐子,是他从老家带来的,他说:“这咸菜是小时候吃的味道,吃着就不会忘,” 有人劝他换个新房,换套家具,他摆摆手:“能用就行,”但听说哪个地方灾了,他立马掏钱;谁家孩子没学上,他立马写信寄款,有一年,老家修桥,他捐了两万块,那是他攒了好几年的全部积蓄,有人想把他的名字刻在桥头,他坚决不同意:“桥是大家修的,不是我一个人的,” 2009年,张铚秀病重住院,他躺在病床上,仍然念叨着那些曾经帮助过的人,他让儿女把床头那本小账本拿出来,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几十年间的支出:哪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他资助了多少;哪个老战友生病他掏了多少钱;哪个五保户过年他寄了米和油,他说:“这本账,没还完,还得接着记,”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开国少将张铚秀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