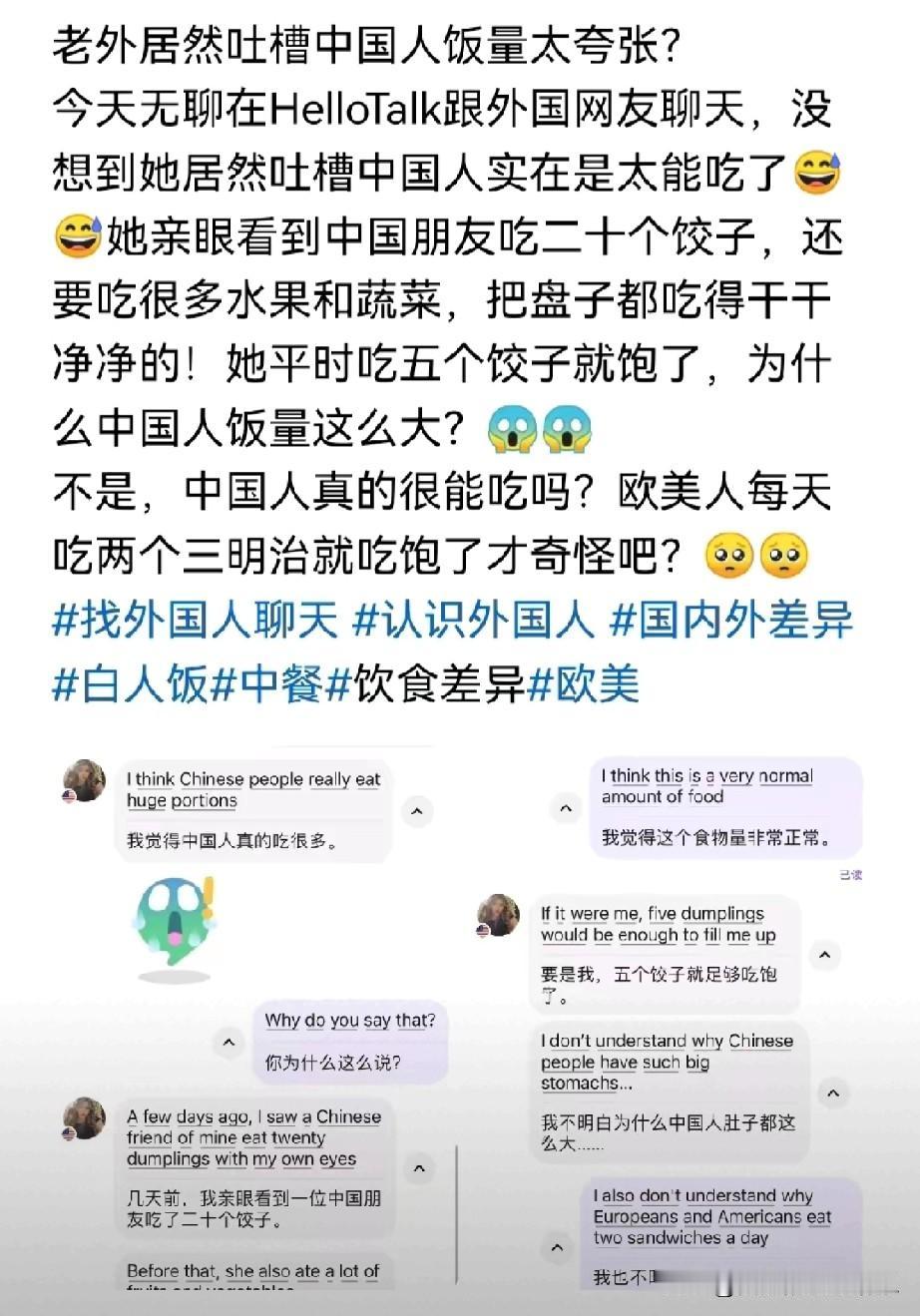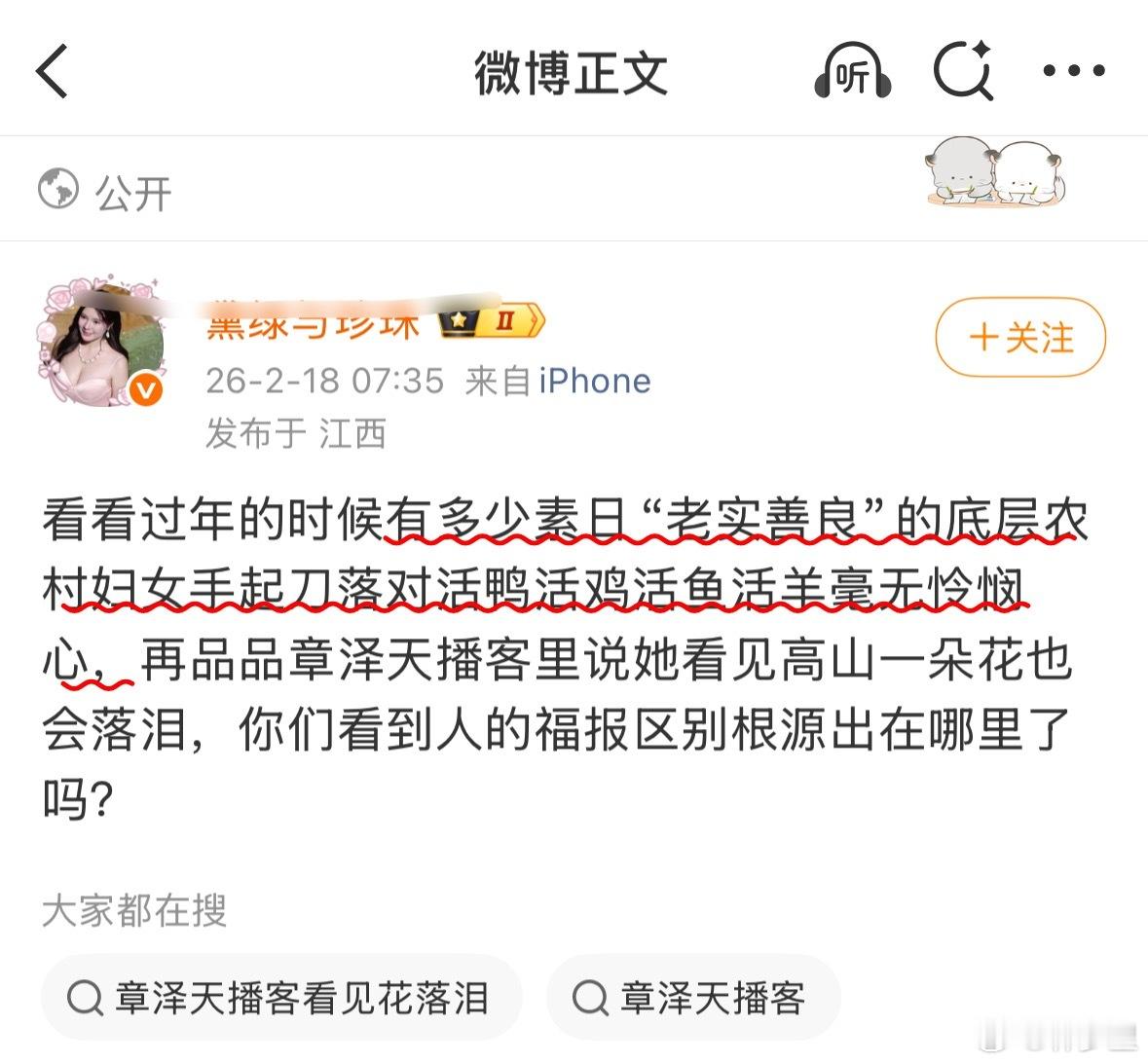1994年,一个英国姑娘坐在成都的小馆子里,对着一碗白米饭发呆。她刚刚吃了一口鱼香茄子,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她想不通,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这碗饭,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这个英国姑娘叫扶霞·邓洛普,当年的她,还是个毕业于剑桥的高材生,出身也十分优越,父亲是银行高管,母亲是策展人,从小过着优渥的生活,出入的都是体面场合,家里吃饭用的是银质刀叉,周末去米其林餐厅更是家常便饭。可偏偏是这样一位见惯了“体面”饮食的英国淑女,被成都街头苍蝇馆子里油腻腻的鱼香茄子击溃了所有的味觉防线。 说起来这事挺有意思的,扶霞当时是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名义跑到四川来的,带着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背景,拿着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一本正经地要做田野调查。结果呢?第一顿饭就被川菜收编了。那些年在伦敦的高级餐厅里,她吃过的所谓“精致中餐”都是些什么玩意儿,酸甜咕咾肉、柠檬鸡,连炒饭都要加青豆和玉米粒,完全是为了迎合西方人那点可怜的味蕾。她以为自己懂中国菜,起码懂个大概,直到那口鱼香茄子滑进食道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过去二十多年全白活了。 要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成都还没现在这么光鲜。小馆子的地板踩上去黏脚,菜单油乎乎地贴在墙上,老板娘用围裙擦完手直接端菜上来。扶霞后来在书里写,她当时盯着那碗米饭看了很久,不是嫌弃,是被震撼到说不出话。她从小到大吃的米饭,要么是煮得稀烂要么是干巴巴的,从来没有一碗米饭能这样颗粒分明、软硬适中,偏偏又能完美地接住鱼香茄子的汤汁。这哪里是主食,分明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引子。 我读扶霞的故事时,总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到底是我们这些从小吃中餐长大的人太麻木了,还是像她这样半路出家的“外人”才能真正看见中国菜的伟大?她后来辞掉了伦敦的工作,搬到成都,进了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跟一群十几岁就出来学厨的小孩一起切萝卜、练刀工。那些小孩可能想不通,这个金发碧眼的老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放着好好的剑桥硕士不当,跑来跟她们抢厨师饭碗。 但扶霞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她说自己是被那口鱼香茄子“开了悟”,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话听着矫情,可仔细想想,一个人花了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那套关于“什么是好吃”的判断体系,被一口菜彻底掀翻,这种冲击确实不比宗教皈依小。更何况她还是个英国人,一个来自全世界公认最难吃国度的英国人,他们的国菜是炸鱼薯条,他们的烹饪哲学是水煮一切。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扶霞成了全世界最懂中餐的西方人,写了《鱼翅与花椒》《川菜》这些书,把中国饮食文化掰开揉碎了讲给老外听。她拿过詹姆斯·比尔德奖,美食界的奥斯卡,被《华尔街日报》称为“最懂中餐的西方人”。可我觉得,这些头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那个下午,在成都某个连名字都记不清的小馆子里,一个异乡人被一碗普通的鱼香茄子击中,从此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连根拔起,栽进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 说起来,鱼香茄子这道菜本身就挺讽刺的。它根本没有鱼,名字里却偏偏带着“鱼香”。这种命名方式大概只有中国人能理解,我们用想象力创造出一种并不存在的味道,然后用最普通的食材去接近它。扶霞后来研究透了川菜的历史才知道,所谓鱼香味,其实是模拟四川乡下做鱼时用的那套泡椒、姜蒜、糖醋的调味组合,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独立的味型。一个外国人要理解这层文化编码,比单纯觉得“好吃”要难得多。 可扶霞偏偏就是被这种复杂的东西迷住了。她后来写过一句话,大意是:中国菜最厉害的地方,不是用了多贵的食材,而是能把最普通的东西做出最不普通的味道。这话说得太对了。你看那碗鱼香茄子,茄子是菜市场最便宜的紫皮茄子,泡椒是自己家里泡的,肉末只要一点点提鲜就行,成本加起来没几块钱。可就是这么一堆廉价的东西,经过油锅的历练,最后呈现出那种咸、甜、酸、辣、鲜交织的复杂层次,比任何米其林餐厅的精致摆盘都来得动人。 这些年我常常想起扶霞的故事,尤其是在那些对中餐充满偏见的声音出现的时候。有人说中餐油烟大、不卫生,有人说中餐太油腻、不健康。我就想笑,这帮人大概从来没真正理解过中餐。他们以为中餐就是外卖盒里那些黏糊糊的橙汁鸡块,殊不知真正的中国味道,藏在像鱼香茄子这种看似平凡实则精妙的家常菜里。它不需要银质刀叉,不需要米其林评级,甚至不需要一个体面的环境。它只需要一个愿意放下所有成见,认认真真吃一口饭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