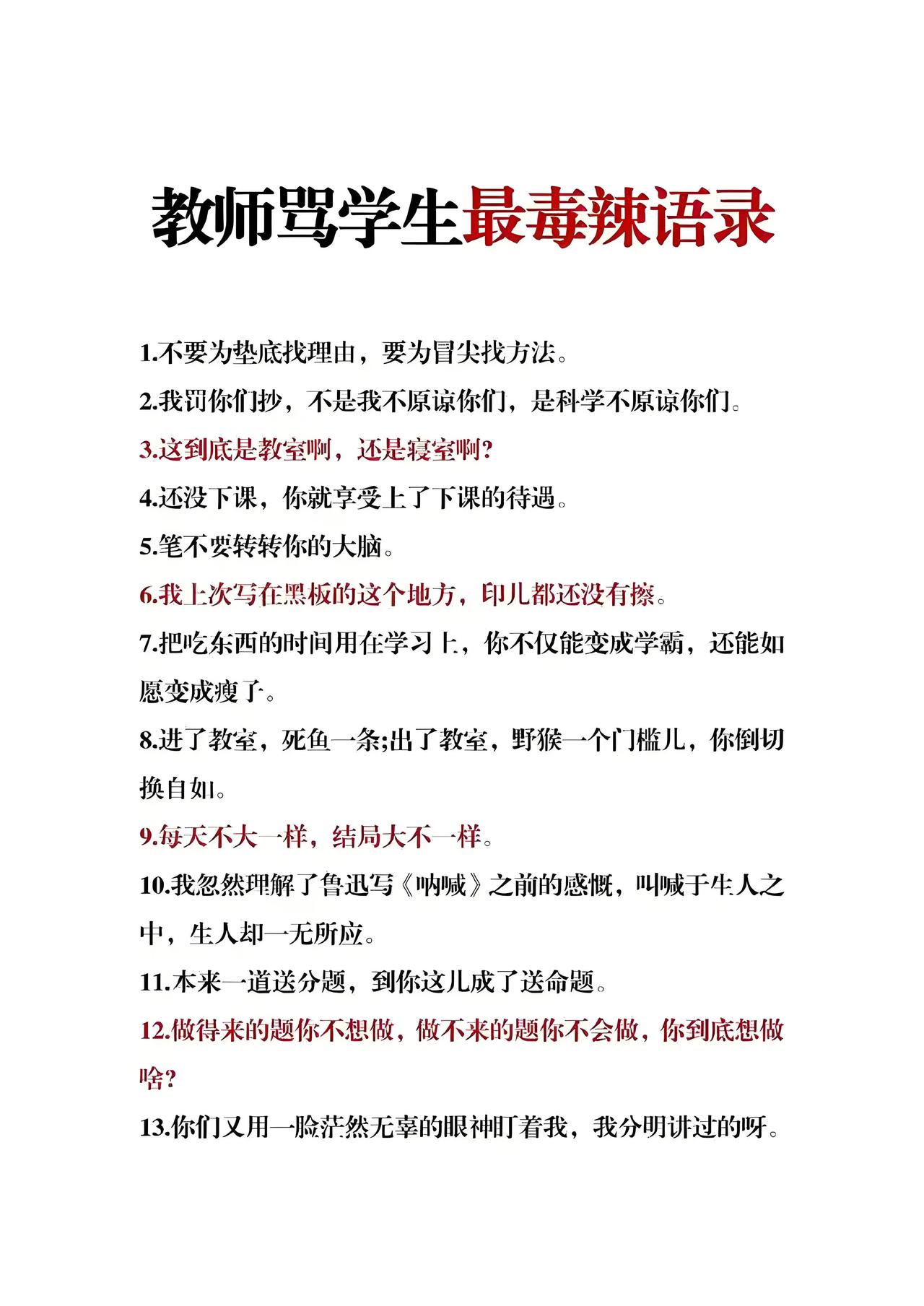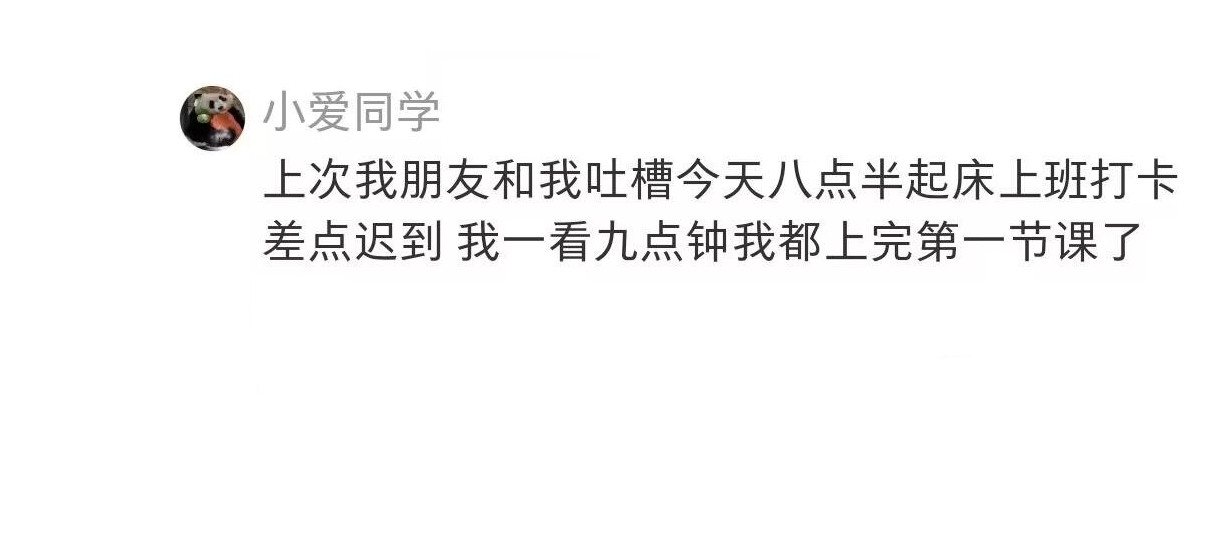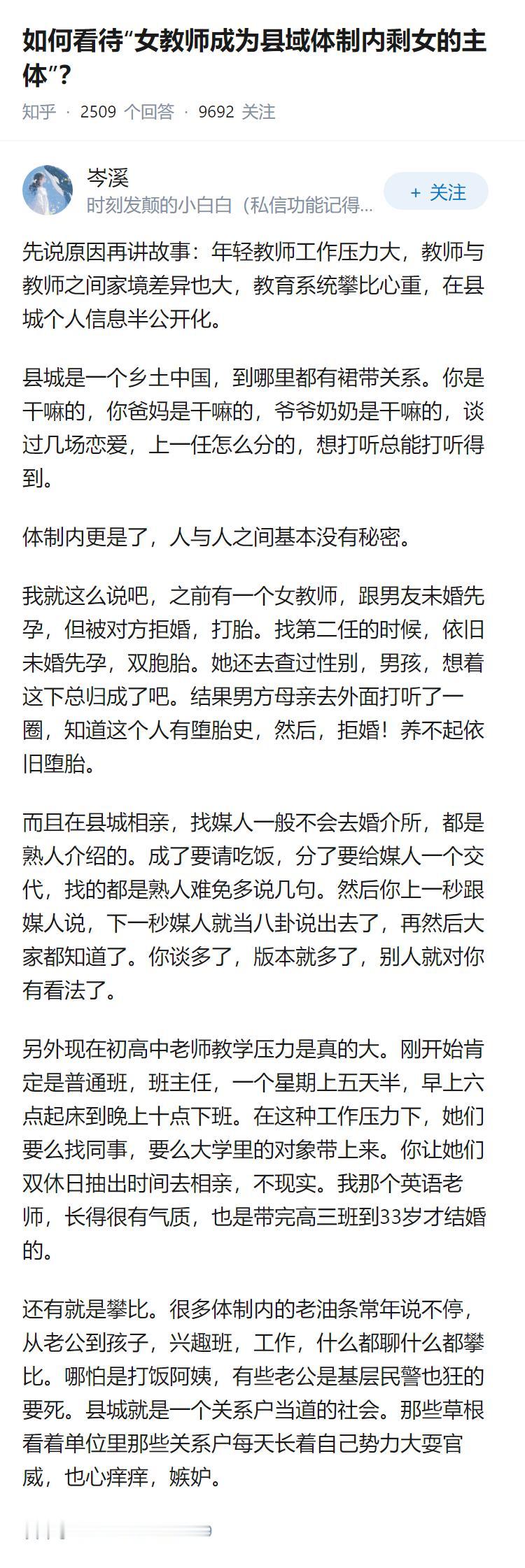1984年我退伍返乡,正赶上公社学校招民办教师,我去考了。去报到那天,在校门口,碰到一个小姑娘,说她弟弟不能来上学了。 小姑娘也就十岁出头,裤脚卷着,露出沾着泥点子的脚踝,手里攥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另一只手攥着半块啃过的窝头。见我穿着新的确良衬衫,她先是往后缩了缩,又咬着唇挪过来,把窝头往我手里塞:“老师,您吃,路上走饿了吧?我弟说今天新老师来,得给您留口吃的。” 我没接,蹲下来问:“你弟咋不来报名?是不舒服吗?” 她眼圈一红,绞着衣角说:“昨天上山割猪草,他踩空崴了腿,肿得像发面馒头。俺爹说,反正将来要种庄稼,认不认字都一样,就不让他来了。” 我跟着她往村东头走,土坯房的院墙倒了半截,院里堆着半干的柴禾。推开门,就看见个瘦小男孩趴在炕沿上,腿上裹着破布,手里攥着根烧过的木炭,在炕席上画歪歪扭扭的“一二三”。见我进来,他赶紧把木炭藏在背后,脸涨得通红。 我摸了摸他的腿,骨头没事,就是崴得厉害。转身去公社卫生院买了瓶跌打药,又跟他爹说:“腿养着就行,耽误不了学习,我每天放学来给他补俩钟头课。” 那之后的一个月,我天天揣着课本去他家。有时候傍晚天擦黑,他家的煤油灯忽明忽暗,堂屋的旧风扇转得吱呀响,我就着灯影儿给小男孩讲算术题。他学得快,讲一遍就懂,还把我教的字工工整整写在裁好的草纸上,攒成厚厚的一摞。 后来小男孩腿好了,背着姐姐缝的布书包天天第一个到校,书包上还绣了个歪歪的五角星。再后来他考上了县卫校,成了村里第一个学西医的人。现在我每次回老家,他都在镇上的诊所里等着,给我免费量血压,说当年要不是我,他现在还在地里刨土。 那小姑娘也嫁了邻村的养蜂人,每次我去,都塞给我两罐刚摇的槐花蜜,玻璃罐子里飘着细碎的蜜沫,甜得人心里发暖。上次回去见她,她正给孙子缝书包,指尖还沾着蜜渍,看见我就笑:“老师,您当年教俺弟认字,现在俺孙子也去您以前上课的学校啦。”
临近退休,40年教龄的老教师,给广大教师朋友提出如下忠告:1、女教师,特别是长
【29评论】【16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