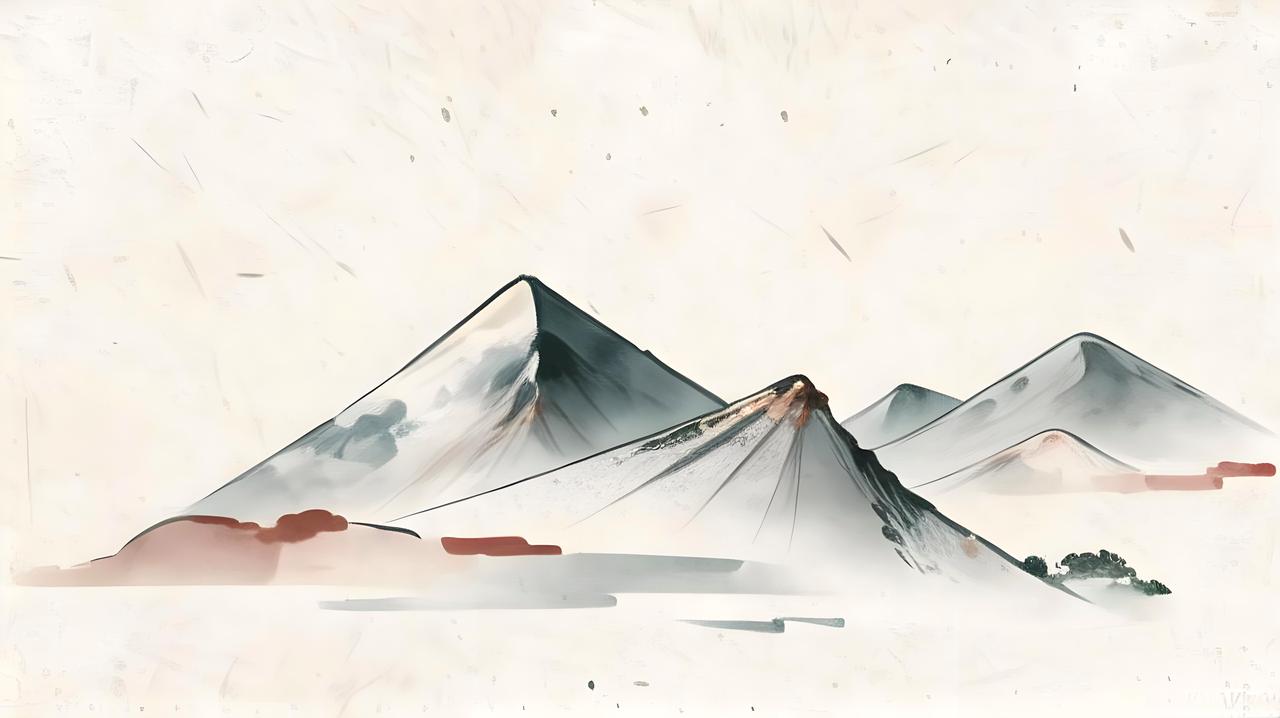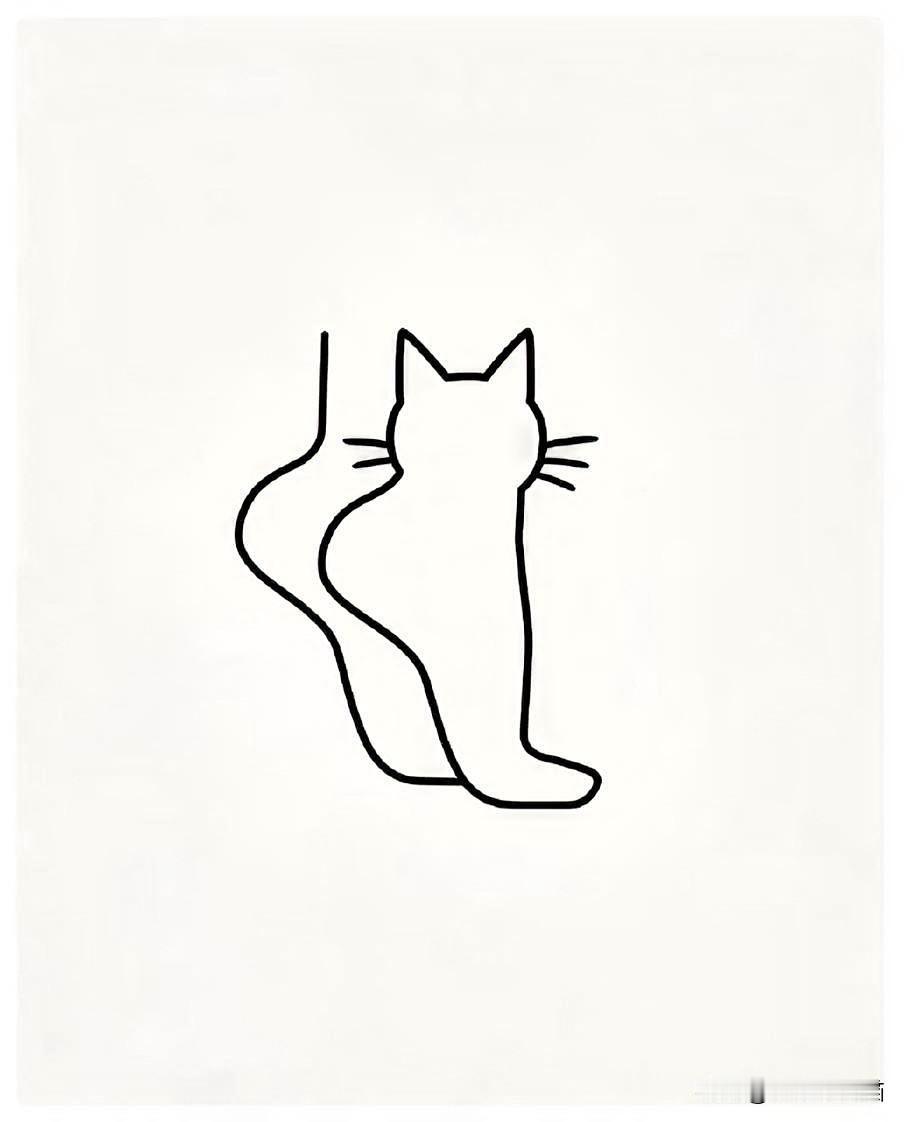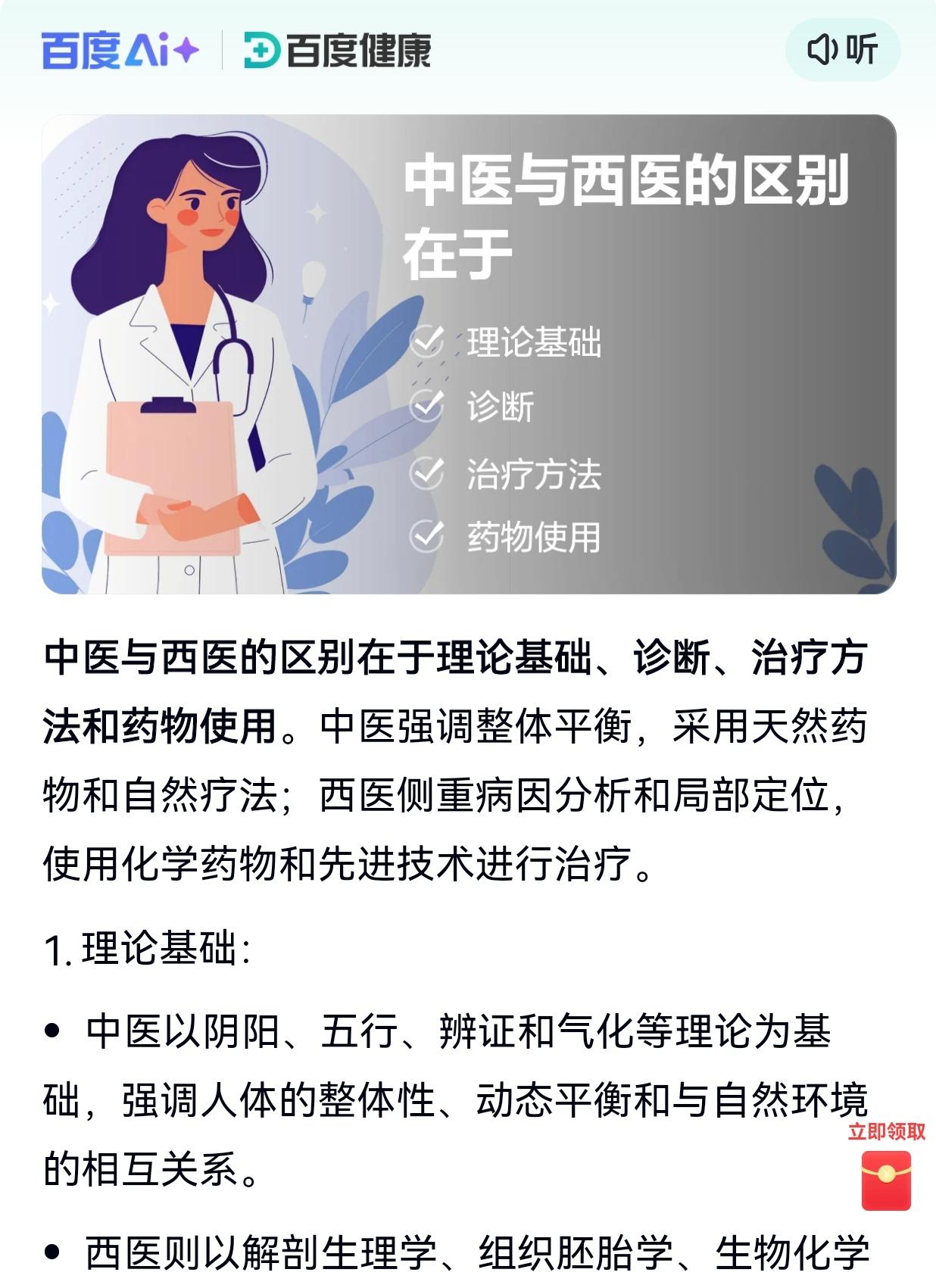药方无言:有些君臣佐使,只能自己配伍 老中医临走前捻着胡须对我说: “一味药再好,也不可逢人便赠;一帖方再灵,未必适合所有人。家传的方子,是祖宗用身子骨试出来的,捂在怀里比晾在外头强。” 那年我二十八岁,刚接过“回春堂”的匾额,只觉得老人家守旧。 直到站在药柜前,看着那张泛黄的“扶正固本汤”方子被印在竞争对手的宣传册上,我才尝到满口黄连的苦。 我和阿诚的缘分,起于十五岁的药材集市。他爹是采药人,背着一篓筐的野生黄芪来铺子里卖。后来我们一起上山认过药,在同一个师父门下抄过方。他开了第一家分店时,我送去一副“诚信赢天下”的牌匾;我研发新药膳包,他第一个放在柜台最显眼处。 这样的情谊,谁都说是杏林佳话。 “回春堂”有了名气后,我们常在后院煎茶论药。他妻儿咳嗽,我亲自配川贝枇杷膏送去;我母亲腿脚寒,他年年冬至前捎来上好的艾绒。两家人吃饭,孩子们抢着叫“伯伯”,夫人们聊着家常,药香里裹着烟火气。 那个让我后怕的秋夜,我记得药炉上的水汽氤氲。店里只剩我俩,对着满屋的药材匣子,喝着我泡的陈皮老白茶。几盏茶下去,话头从药材行情说到了各自难处。 “最近心里头不踏实,”我按着太阳穴,“老家祠堂要修,一笔不小的开支,店里想进一批野山参,定金都让人踌躇。” 阿诚给我续茶:“短钱的话,我那里有。” “那倒不必,”我摇头,“就是愁。祠堂的木梁是老楠木,师傅说非得用陈年的桐油来护,这年头纯正的桐油,比人参还难寻。” 说这话时,我全然没留心他沏茶的手,微微顿了一下。 半月后,管账的师兄掀帘子进来,脸色不对:“诚记那边把说好的那批三七全截走了,说是他们自家急用。” 我怔了怔,拨通阿诚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温厚如常:“老爷子风湿犯了,老方子里三七不能少,实在对不住。” 这理由严丝合缝,正是我前几日同他叹过的苦衷。 但我还是多了个心思,让师兄把另一批贵细药材单独存好。这个举动,后来保住了“回春堂”的根基。 风波起在来年开春。 先是库房里那罐我祖父传下的“九制熟地黄”见底飞快,接着两个跟了我十年的学徒递了辞呈。最伤元气的是,我调理了三年才渐有起色的“健脾八珍糕”,被城东新开的药铺照着样子做了出来,价钱却便宜三成。 线人把话递到我耳边时,我在祖父的牌位前坐了一宿。所有痕迹都绕回阿诚,他盘下了城东的铺面,带走了我的学徒,仿透了我的路数。 我在老茶室等他。他如约而至,身上那股熟悉的药草气里,混了一丝陌生的疏离。 “图什么?”我问他。 他转动着手中的茶盏:“记得你说,老祠堂的楠木梁,非得陈年桐油养。我家祖宅的梁,也快朽了。” “就为这个?” “还有你煮茶时说的那些,”他抬眼,眼里没什么波澜,“你说过,看祠堂凋敝,才懂有些根基不能动。我的根基,是我那一大家子人。” 后来我才晓得,他早就在谋算这些。而我,在一盏接一盏的茶汤里,把家底都摊给了他看。 我告诉他来年想主推哪几味药,他提前囤了货;我嘀咕某个学徒心浮,他许以重利挖了去;我甚至跟他剖析过几位老主顾的体质底子。 最诛心的是,连他截我药材的由头,都出自我家的私事。 “你知道我最痛的是什么?”我看着他的眼睛,“不是方子,是你拿我修祠堂的孝心,做了你生意的垫脚石。” 他沉默了很久,说:“这世道,方子不传外人。” “回春堂”勉强撑着没倒,但口碑损了。我撤了分店,回到最初的小铺面,重新坐堂看诊。 妻子没多话,只是悄悄收起了厨房里他家常送来的那只药膳罐。儿子有天忽然问:“爸,诚伯怎么不来找你下棋了?” 我答不上来。 老中医听闻,拄着杖来看我。他没问缘由,只是叫我拿脉枕。 “师父,我败在何处?”我终于问出口。 他三指搭在我腕上,良久才说:“脉象浮数,是心火泄得太过了。好药如真言,贵在藏,不贵在施。” 如今,我学会了在开口前,先将话在舌下含一含:这方子是否非得给出?这人是否真需这味药?给出去了,是救人,还是惹病? 不是变得吝啬,而是懂了“藏”的深意。 前些天,阿诚托人送来一包顶好的天麻,说是给我治头痛。我原封退了回去。 不是心中还有怨怼,而是终于明白:有些药,一旦给错了人,良方也成毒引;有些话,一旦说过了界,交情便成病灶。 昨夜整理故纸,翻出当年一起在师父处抄的《药性赋》。扉页上,我们曾互相题字。他写的是:“同心同德,岐黄之道。” 如今我懂了,同道能走多远,不看共饮过多少茶,而看彼此守住了多少不该说的“君臣佐使”。 言语如药:下口容易,收回难。 《黄帝内经》有言:“谨守病机,各司其属。” 治病如此,处世亦然,须明辨什么当言,什么当默。 记住:家传如秘方,捂在怀里才能传家;口舌如门户,守住关键才得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