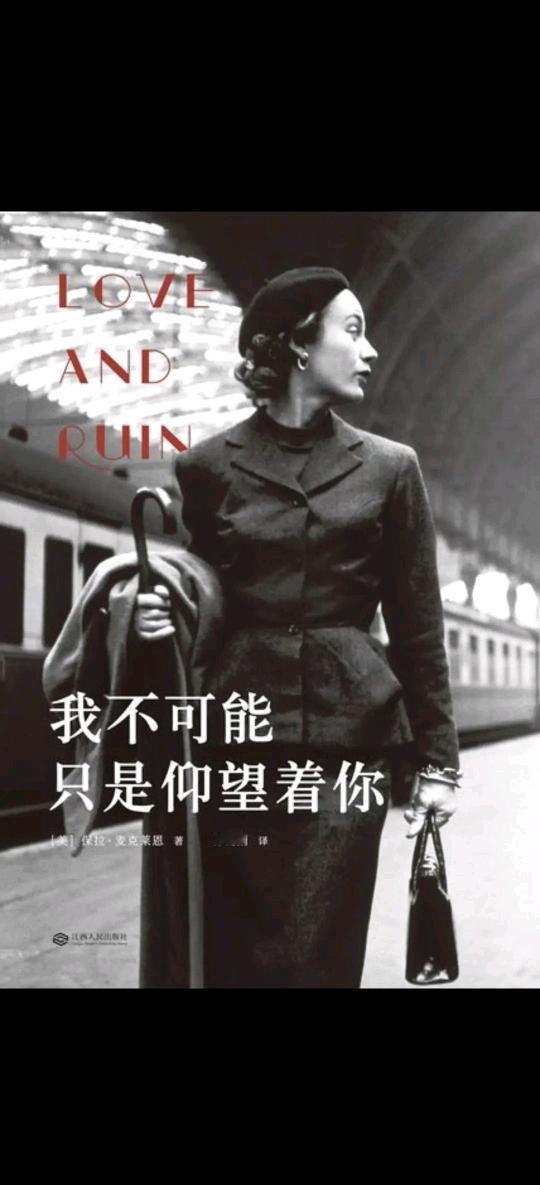她是一名清朝刽子手的老婆,那些被砍下来的脑袋无人问领,就会被刽子手带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些脑袋就会交由他的老婆处理。 这个女人是谁?这些常人避之不及的东西,又能给她带来什么? 照片上的女人名叫邓李氏,是清末刽子手邓海山的妻子,在那个年代,刽子手是个特殊又被人嫌弃的职业,从业者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底层人,邓海山就是其中之一。 光绪二十八年的北京胡同里,邓家的院门总是关得严实,路过的人要么加快脚步,要么干脆绕道——谁都知道,这院子里晾着的不是衣物被褥,是一颗颗惨白的人头骨。邓海山每次从刑场回来,背上的麻袋沉甸甸的,别人买菜归家,他拎着的是无人认领的头颅,进门只说一句“又带了几个”,便把麻袋往厨房一放,转身去擦拭那把沾着血污的鬼头刀。 邓李氏从不问这些头颅的来历,也不打听案子的是非。她只默默地搬来大铁锅,添上井水,架起柴火,待水烧开后将头颅放入锅中。滚烫的沸水咕嘟咕嘟翻滚,她握着长柄刷子,一下下刷净骨头上残留的皮肉,动作娴熟得像在清洗寻常厨具。邻居家的炊烟带着饭菜香,邓家的烟囱里飘出的气味却让街坊们皱眉,背后偷偷骂“晦气”“遭报应”,这些话传到她耳朵里,她也只是低头继续干活,连眼皮都不抬。 处理干净的头颅,会被她摊在屋檐下的木架上晾晒,太阳底下,骨头渐渐泛白,和院子里的柴禾、农具摆在一起,显得格外刺眼。有一次,隔壁王嫂来借针线,瞥见木架上的头骨,吓得手里的针线筐都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地跑回家。邓李氏捡起针线筐,送到邻居门口,只淡淡说了句“不碍事,都刷干净了”,王嫂却躲在屋里不敢应声。 她做这些,从不是为了什么怪癖,而是为了活下去。清末的刽子手虽有官府四元大洋的赏钱,却抵不过世人的排挤,邓海山挣的钱勉强够糊口,而这些无人认领的头颅,是家里重要的“进项”。当时新式学堂兴起,学医、学画的师生需要骨骼做教具,没人愿意沾这种“阴物”,邓李氏处理的头骨干净无异味,恰好填补了缺口。 买主都是趁夜悄悄来,敲三下门,递上银子,接过用油纸包好的头骨,转身就走,全程不说一句话。邓李氏从不问对方身份,也不多要一分钱,她只知道,这几块银子能给孩子买米、扯布做衣裳,能让生病的丈夫抓药。头一回干这活时,她夜里总被噩梦惊醒,感觉有冷风往被窝里钻,可看着孩子们饿得发慌的眼神,她的心渐渐硬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邓海山曾被师父告诫,斩满九十九人就收手,否则会遭报应,可他贪恋赏钱和家属给的“外快”,一生斩了近三百人,双手沾满鲜血。旁人嫌弃邓海山,连带着邓李氏和孩子也被孤立,孩子们上学要走后门,放学路上还会被同伴骂“刽子手的崽子”,回家哭着要转学,邓李氏只能抱着孩子,一遍遍地说“忍忍就好了”。 她的日子,全靠这些“阴物”撑着。有一年冬天,家里快揭不开锅,邓海山又因为醉酒误了差事被官府罚俸,邓李氏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连夜把刚处理好的三颗头骨送到学堂,换回来的银子买了米和面,让全家熬过了最冷的日子。那天晚上,她坐在灶台边,看着跳动的火苗,手上的老茧被热水泡得发白,心里却踏实了——至少,孩子们不用挨饿。 1914年,北京政府规定死刑改用枪决,斩首被废除,邓海山彻底失业。没了头颅可处理,家里的“进项”断了,日子一下子难了起来。邓海山想种地,地主嫌他“晦气”不肯租地;想进善堂混口饭吃,又因“杀人太多”被拒绝,只能整日酗酒,对着墙壁发呆。 邓李氏没抱怨,她捡起针线活,给人缝补衣裳换些零钱,还去街上捡柴禾、挖野菜,硬生生撑起了这个家。院子里的木架再也没晾过头骨,改成了晾晒衣物的地方,只是那木架上的划痕,还留着当年的痕迹。孩子们渐渐长大,外出谋生,从不跟人提起家里的往事,邓李氏也老了,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时,偶尔会盯着那木架发呆,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有人说她心狠,说她为了钱什么都敢做,可没人知道,她只是个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底层女人。那些常人避之不及的头颅,在她眼里不是阴物,是救命稻草;那些旁人唾弃的活计,是她养活家人的本事。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凭着一双粗糙的手、一颗坚韧的心,在世人的歧视和生活的重压下,撑起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家。 邓李氏的故事,是清末底层百姓的缩影。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总有人要干这些没人愿意干的活,总有人要在绝境中挣扎求生。她的“狠”,是被逼出来的坚强;她的“不在乎”,是藏在心底的无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