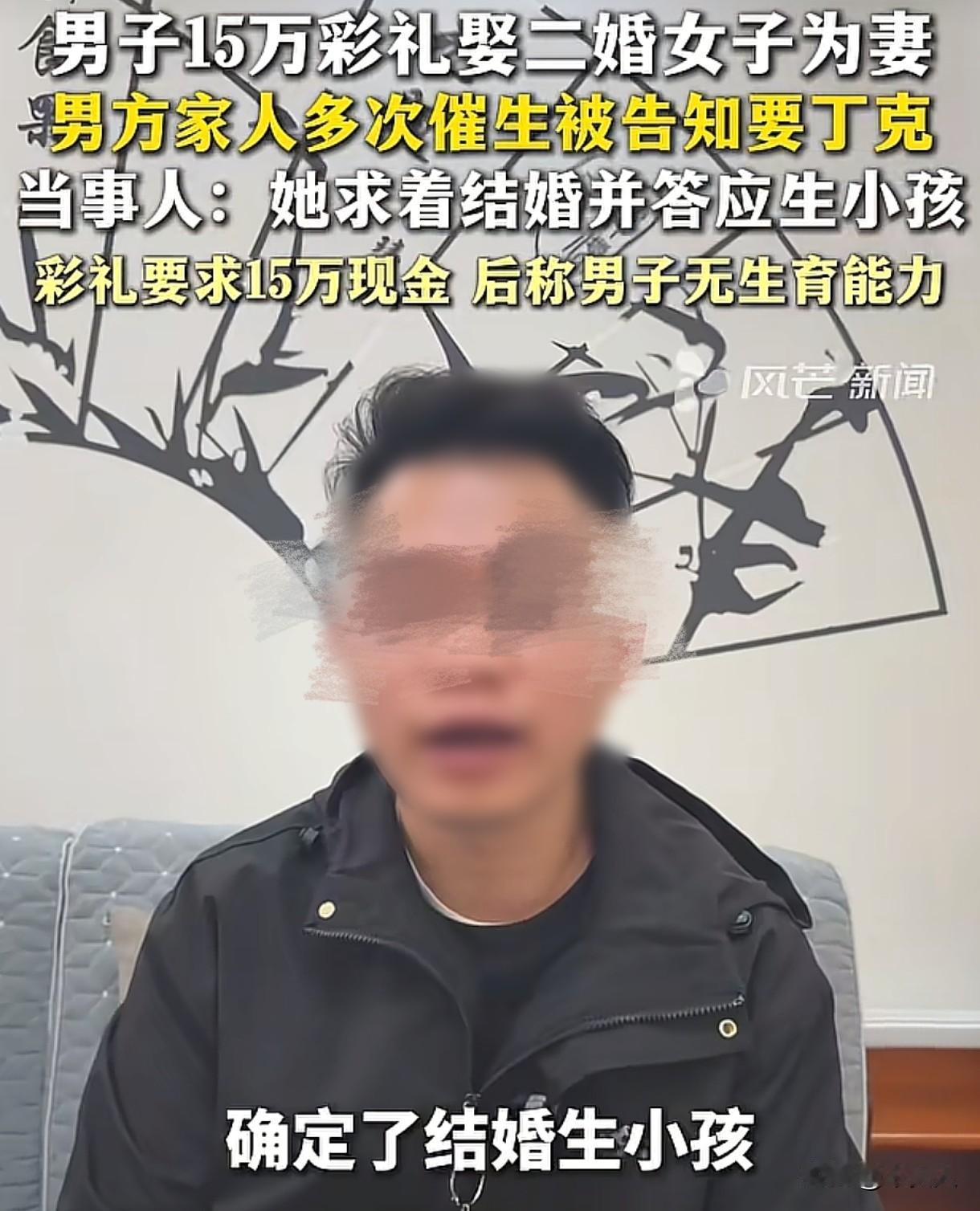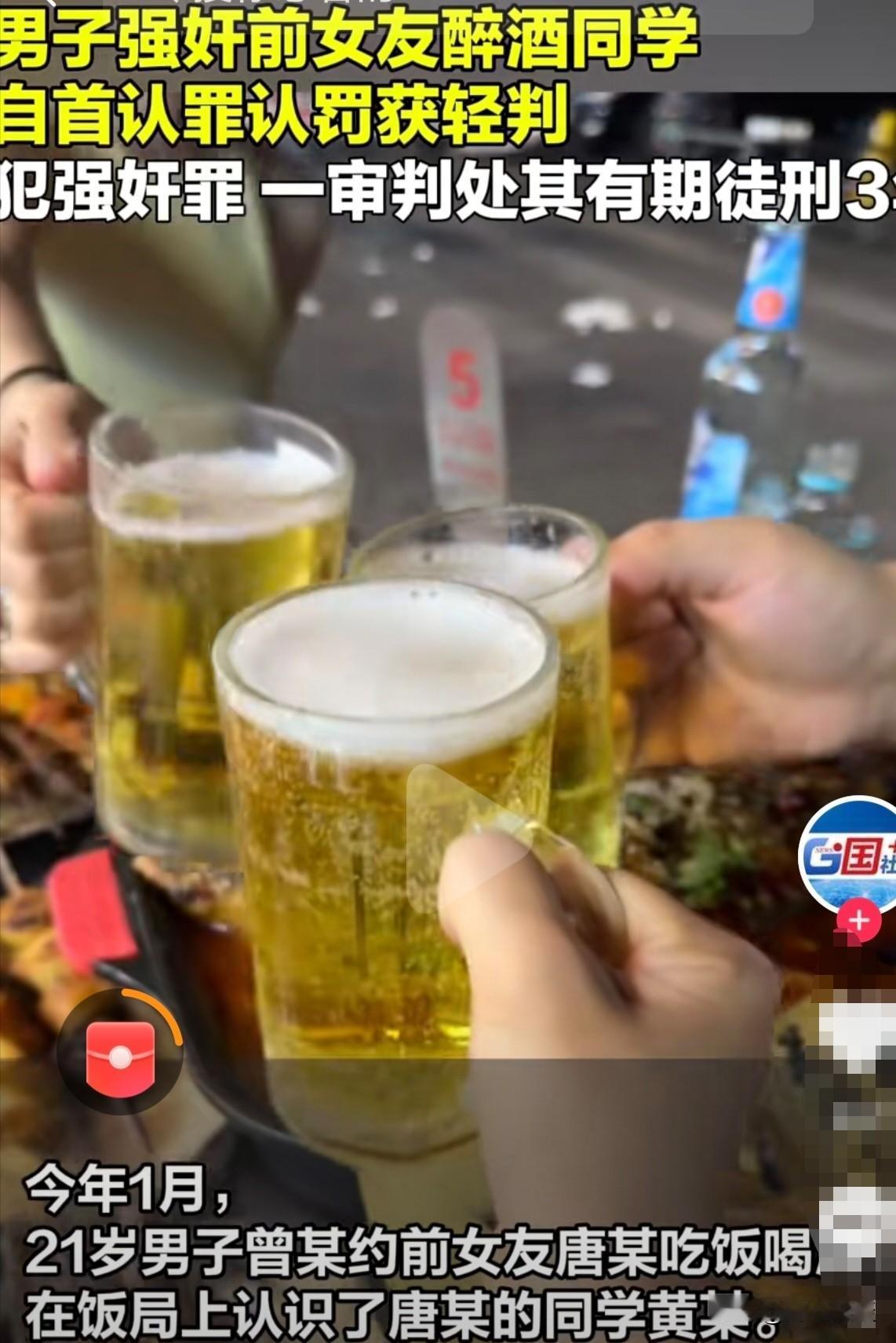2024年3月,河南驻马店,14岁女孩和13岁女同学,和3名成年男子去宾馆,14岁女孩让另外一名女孩去厕所,两名男子先后和她发生了关系。事发后,她先说是自愿,又说不是自愿。警方最初定性为聚众淫乱,后又更改为引诱未成年聚众淫乱。检察院却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捕。 根据驻马店市公安局官方通报的核心内容:2024年3月中旬,14岁的李某与13岁的王某,通过社交软件结识3名成年男子张某、赵某、孙某。 几人相约见面后,一同前往当地某宾馆开房。期间,李某让王某前往卫生间等候,随后与张某、赵某先后发生性关系。 事发后,王某家长发现异常报警,李某最初向警方陈述“是自愿的”,时隔两天后又改口称“被强迫”。 警方最初将案件定性为“聚众淫乱罪”,但随后很快调整为“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然而,驻马店市检察院审查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予批捕决定。 这份结论一出,舆论瞬间分裂:有人觉得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到位,也有人认为司法不能仅凭反复的陈述定罪,必须坚守证据底线。 从法律定义来看,“聚众淫乱罪”针对的是聚集多人进行淫乱活动、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主观上要求参与者均系自愿;而“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则明确将未成年人作为特殊保护对象,只要存在“引诱”行为,即便未成年人表面自愿,也可能构成犯罪。 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认定“引诱”情节,以及未成年人的“自愿”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但检察院为何会作出不予批捕决定?核心问题出在“证据链”上。 根据司法实践要求,认定“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需要同时证明三个关键事实:一是行为人实施了“引诱”行为(比如用金钱、物质、言语诱惑等);二是未成年人因引诱参与了淫乱活动;三是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 从官方通报的信息来看,李某的陈述前后矛盾,没有其他证据(如监控、聊天记录、物证)佐证张某等人存在“引诱”行为,也无法证明性行为发生时存在胁迫、暴力等情节。 在“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下,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本质上是对证据标准的坚守,而非否定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涉性犯罪的条款相对简单,仅对“奸淫幼女”作出明确规定,且门槛较低,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当时突出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 1997年《刑法》修订时,新增了“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将“引诱”作为核心定罪要件,这背后是对“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的考量——既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避免无限扩大打击范围。 最典型的历史参照,是2013年南京某“聚众淫乱案”,该案中,多名未成年人参与淫乱活动,行为人以“未成年人自愿”为辩解理由,但法院最终以“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定罪。 两起案件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南京案中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用金钱、游戏装备等方式引诱未成年人,而驻马店案中缺乏此类关键证据。 从这两起案件的对比中能清晰看出,司法实践中对“引诱”情节的认定越来越严格,证据链的完整性成为定罪的核心前提,这也是我国司法进步的重要体现。 从这起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家庭监护的缺失是关键诱因,14岁和13岁的未成年人,能够随意通过社交软件结识陌生成年男子,还能独自前往宾馆开房,这背后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的行踪监管、交友引导严重不足。 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2020年湖南某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中,受害者也是因家长监管不力,长期与陌生男子网络交往后遭遇侵害。 这些案例反复提醒我们,未成年人的保护,不能仅靠司法兜底,更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普及率仍然偏低,很多孩子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不知道如何辨别不良诱惑,也不知道遭遇侵害后该如何维权。 反观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早在20世纪中期就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明确告知未成年人“性同意”的边界,以及遭遇侵害后的求助渠道。这种前置性的保护措施,远比事后的司法追责更能减少未成年人涉性案件的发生。 还要注意的是,司法对证据标准的坚守,并非对未成年人的“放任”,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打击犯罪。 在驻马店案中,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后,警方并未终止调查,而是继续补充侦查。 这种“审慎办案”的态度,恰恰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负责任表现——如果仅凭不完整的证据定罪,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反而不利于维护司法公信力,最终损害的还是未成年人的长远利益。 河南驻马店这起事件,表面是司法定性的争议,实则是法律逻辑、社会认知与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的碰撞。 它告诉我们: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需要法律的刚性支撑,但这种支撑必须建立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法治原则之上。 同时,未成年人的保护也不能仅靠司法兜底,更需要家庭履行监护责任、学校开展有效性教育、社会构建全方位的保护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