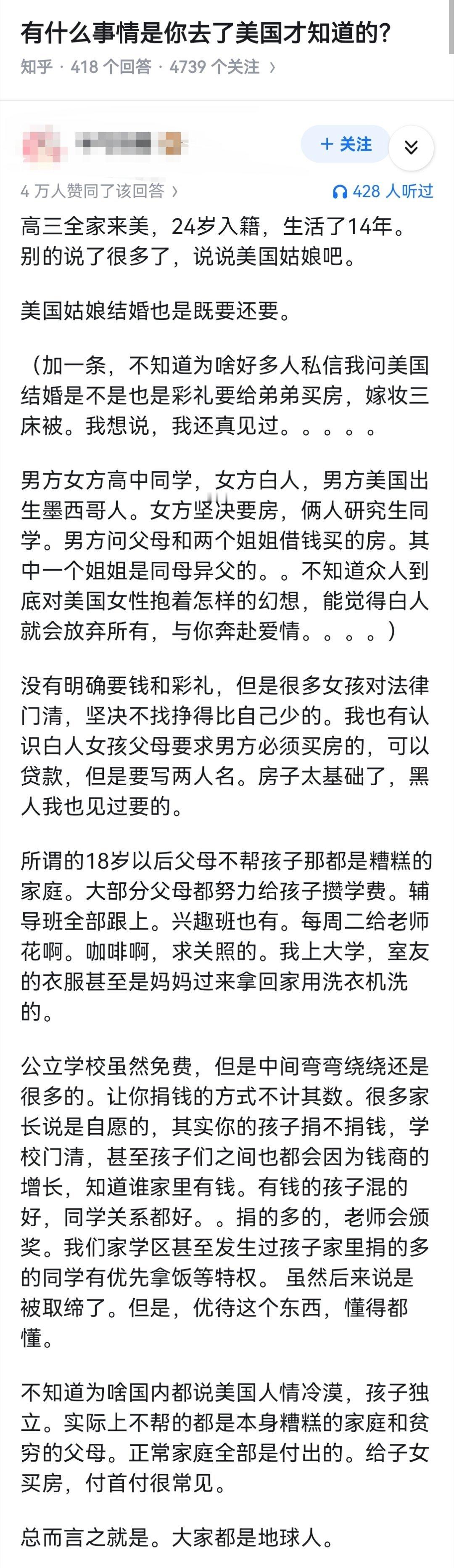1923年,美国,一名1岁多的黑人小男孩,被两名医生固定在椅子上。男医生按着他的头,女护士开始启动一台机器。此时,小男孩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这场面,给人第一感觉好像是一种刑罚。其实不是,两名医生正在给这名小孩治疗疾病,女护士操作是一台X光机。 咱们把时间轴拉回1900年,那时候美国黑人医生占比是1.3%。那会儿黑人占总人口多少?11.6%。好,咱们再看2018年,黑人医生占比涨到了5.4%。 是不是觉得有进步?别急,你得看这中间跨度是多久——整整120年!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根线就像心电图停跳了一样,几乎就是趴在地上没动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丹利副教授都说了,这情况“80年来都没有改善”。 这就像什么?就像你跑马拉松,别人都跑完全程了,你还在起跑线那儿系鞋带,系了一百年。 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其实都摆在明面上。 早在19世纪,黑人想学医,那就是在做梦。咱们得提个人,詹姆斯麦丘恩史密斯。这哥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拿到医学学位的黑人。厉害吧?但他这学位不是在美国拿的。因为美国的医学院压根就不收他,因为他肤色不对。没办法,他只能漂洋过海去了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在1837年才圆了医生梦。 在那个年代,想救人还得先出国,这是多大的讽刺。 更有意思的数据来了。根据杜克大学的资料,1868年到1904年这段时间,全美其实有7所专门给黑人学生开的医学院。看着还行是吧?但到了标题里提到的1923年,这7所学校就剩下了2所。 这就是所谓的“优胜劣汰”?我看未必。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排挤。教育资源这东西,就像水流,一旦上游被截断了,下游的田地只能干死。 美国医学院校协会那个主任迈克尔迪尔说得很直白:这是“制度性和系统性种族主义”。 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就是:从根儿上就不想带你玩。 在这种环境下,黑人社区的孩子要想当医生,难如登天。你想啊,谁小时候还没个当科学家的梦?但要想成才,你得有资源,有导师,有榜样。可在黑人社区,这些都是奢侈品。 更扎心的是,好不容易挤进医学院的那些黑人苗子,日子也不好过。《美国医学会内科杂志》的数据显示,黑人学生的退学率是5.7%,白人是2.3%。这多出来的两倍多,不是因为他们笨,是因为在这个圈子里,他们是异类,是被边缘化的那一小撮人。 你可能会问,医生是黑人还是白人,有那么重要吗?只要能治病不就行了? 这还真不一样。这关乎人命。 在美国,黑人新生儿的死亡率是白人新生儿的3倍。 这是一个让人看了想砸桌子的数据。但是,如果这些黑人宝宝是由黑人医生来照顾,他们的存活率就会显著提高。 为啥?不是白人医生医术不行,而是这里面有个“信任”和“理解”的问题。 咱们都有去医院的经历,如果对面坐的大夫能懂你的生活习惯,能听懂你的土话,甚至只要看着面善,你是不是心里就踏实多了? 对于美国黑人来说,这种“踏实”是保命的。 咱们再看个数据,美国黑人死于艾滋病毒的可能性是白人的6到14.5倍。这差距大得吓人。除了治疗机会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信任”。 历史上,美国医学界对黑人干过不少缺德事,导致很多黑人压根不信白人医生。哪怕病得难受,也不愿意去医院,或者去了也不听医嘱。 但如果有黑人医生在,这道心墙就能拆得掉。研究都说了,如果黑人男性看病遇到黑人医生,他们更愿意去做预防性检查。 这就好比咱们见了老乡,话匣子容易打开,心防容易放下。 哈佛医学院的丹巴若许教授说得特别到位:医生的多样性,是为了重建信任。 可惜啊,现在的局面是,信任还没建立起来,人先没了。 这不仅仅是个就业问题,这是个公共卫生危机。就像专家警告的那样,黑人医生的短缺,直接导致了传染病、慢性病在有色人种社区里肆虐。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被排斥,所以医生少;因为医生少,所以病人死得多;因为死得多,社区更贫困,更出不了医生。 回到1923年那张照片。那时候,那个黑人小男孩面对X光机时的恐惧,或许只是对未知机器的害怕。但今天,无数黑人患者面对医院时的恐惧,却是对整个医疗体系的不信任。 这一百年的时光,科技从X光机进化到了核磁共振、AI诊断,但在“人心”这台机器上,有些零件似乎生锈了,卡在那儿整整一个世纪没动窝。 要是连看病救人这事儿都要分个三六九等,都要被肤色卡脖子,那这所谓的现代文明,多少有点虚伪。 咱们常说医者仁心,但这“仁心”如果照不到所有人身上,那它就是残缺的。美国想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喊口号没用,得真把那些堵了一百年的路,给挖通了才行。 这事儿给咱们的启示也很深:公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得有人去争、去抢、去打破旧规矩才能换来的。 希望下一个一百年,不再需要用这种冰冷的数据来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