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3年,知青刘朝旭被推荐上大学,临走时去找队长告别。没想到,在他家窗前,听到里面队长说:“朝旭要走了,去给他借点路费吧!”队长媳妇说:“你上次卖了羊皮袄才凑够给知青买锅的钱,现在让我上哪儿借!” 这番话把刘朝旭的思绪瞬间拽回了四年前,那时候他和一群北京来的学生娃刚到这黄土高原,入眼尽是铺天盖地的黄,连点儿绿颜色都难找。 就在那一个个依坡而建的土窑洞前,面对这种从没见过的荒凉,大伙儿心里正打鼓,是郭叔那张黑红的脸凑了上来。 这汉子实诚,那一脸憨笑把大伙心里的慌乱给压下去了,那时候村里的日子苦,可郭叔从自家炕上的小桌上抓起凑来的大枣和饼子,就往他们手里塞,大娘大婶们端来刚烧开的大碗水,那种“成了一家人”的热乎气,是这片贫瘠土地上最先给他们的馈赠。 然而,“那口锅”的故事,却成了这四年里最沉的一笔良心债。 知青点的日子过得粗糙,轮到刘朝旭做饭那天出了岔子,早起他把蒸帘放好,馍馍搁上,刚低头要去添把火,却发现灶膛里的火苗早就灭了个干净,扒开湿漉漉的柴火一看,好家伙,那口用了许久的大铁锅,底儿上不知何时破了个洞,正滴滴答答往下漏水。 这可是关乎大伙吃饭的大事,刘朝旭慌了神,火急火燎地跑到大队部找会计,预支了十五块钱,那些一元、两元、五元的毛票被他仔细叠好塞进裤兜,接着就去堵郭叔家的门,借了驴车要进镇买锅。 郭叔那时正在喝粥,一听这事,嘴一抹就跳上了车,连那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事都不分,只说赶紧走。 那是初夏的日头,到了半路日头毒了起来,心急火燎赶车的郭叔热得受不住,就把那是冬天御寒保命的羊皮袄脱了,随手卷成一团搁在车板上,连带着刘朝旭递给他的那卷买锅钱,也一并揣进了外褂兜里。 悲剧就在那一眨眼的功夫发生了,两人在供销社挑好了那口锃光瓦亮的新锅,回头再去拿车上的衣裳付钱时,车板上只剩下一捆干巴巴的麻绳,那件羊皮袄连带着里面的公款,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 两个人在来回的土路上来回找了两遍,连个影儿都没有,郭叔当时的脸色很难看,但他那股子犟脾气上来了,只是说:“娃,俺丢的钱俺负责,先回去。” 哪怕后来刘朝旭拿着大伙儿重新凑的一把钱硬要塞给郭叔,甚至偷偷把钱扔进郭家屋里,都被那汉子黑着脸追出来给塞了回来,嘴里还数落他不听话。 直到今天站在窗根底下,刘朝旭才算是彻底明白,当年郭叔那是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填补那个丢钱的窟窿,不让知青们饿肚子,那件老羊皮袄是真的再也没赎回来,那是山里汉子过冬的命根子,就这么替他们挡了灾。 听到屋里那句“卖了羊皮袄”,窗外的刘朝旭眼眶子通红,没敢推门惊动那两口子,转身悄没声地走了。 回到知青点,他红着眼把这事儿跟大伙一说,平日里不管是咋咋呼呼的还是沉默寡言的,这时候全都不约而同地把手伸进了口袋,那个年代谁都不富裕,但这笔钱凑得格外快,大伙儿只有一个念头:得把郭叔的羊皮袄给“穿”回去。 几天后的清晨,那个箱子被悄悄留在了知青点,刘朝旭把赎回来的羊皮袄整整齐齐叠在里头,拜托没走的知青回头转交给郭叔,自己则扛着行李,在那件皮袄的温度里默默踏上了返乡的路。 直到人走了,郭叔才赶来送行,看着那件失而复得的旧皮袄,这个在黄土地上刨食了大半辈子的硬汉子,两只粗糙的大手在羊皮上摩挲个不停,嗓子眼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这娃,咋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呢。”后来为了给刘朝旭寄点自家种的红枣,他逮着知青就问地址,可大伙儿为了怕他又破费,谁都咬死了说不知道。 这段没有道别的缘分,终究没能等到再见的那一天。 就在刘朝旭上大学的第二年,一封来自知青点的信,把他的一颗心砸得粉碎,信纸上有泪痕,字迹却清晰得刺眼:村里山体塌方,郭叔为了救人,被埋在了那口窑洞里。 那个总是嘿嘿笑着、把热乎饼子塞给他们的黑脸汉子,那个大冬天没了羊皮袄硬扛过来的倔老头,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片黄土之下。 那一刻,大学校园里的刘朝旭泪流满面,毕业后,刘朝旭成了一名人民教师,虽然工作在外地,但他每个月领了工资,雷打不动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出一部分寄给那位远在山西农村的郭婶,钱不算多,但他知道,这是他替那个没机会再穿羊皮袄的汉子,去守的一份家。 岁月更迭,当年的那些苦涩与欢笑都已被风沙掩埋,唯独那件羊皮袄的故事,像一枚生锈却滚烫的钉子,死死地钉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那些并不富裕却依然倾尽所有的善良,如同这黄土高原一样厚重,成了刘朝旭这一生都还不完的恩情。 信源: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知青史·大潮》 《山西知青下乡史料汇编》 知网收录的“知青下乡与乡村互助”相关学术论文 环球网 《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笔谈:青春的梦想与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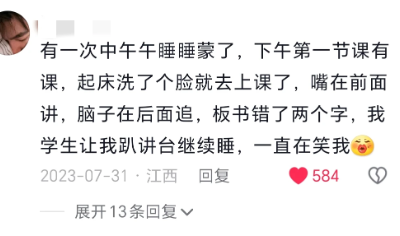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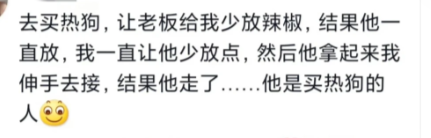

![[红脸笑]终于能把心放肚子里了,莎莎这脚踝伤总算有了准信儿!](http://image.uczzd.cn/657157319006603484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