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事之后,立即送进博物馆。 1917年10月15日清晨,巴黎郊外的刑场飘着冷雨,行刑队队长对着士兵低声下令时,没人敢多看几步外那个穿红裙的女人。 她叫玛塔·哈丽,荷兰裔舞女,此刻却被标着“叛国者”的标签,而她的头颅,将在几小时后装进玻璃罐,送进巴黎阿纳托密博物馆。 13岁那年,玛嘉蕾莎·吉尔特鲁伊达·泽利(她的原名)在荷兰鹿特丹的贫民窟里第一次体会到一无所有。 父亲的贸易公司破产后消失,母亲染病去世,孤儿院的铁门在她身后关上时,她攥着母亲留下的唯一一条旧丝巾,指节攥得发白。 后来她在报纸上看到征婚启事,嫁给荷兰军官鲁道夫·麦克劳德,以为能逃离贫困,却只换来酗酒的拳头和殖民地军营的孤独。 1903年她抱着女儿离开时,连船票都是变卖首饰凑的。 巴黎的女神游乐厅舞台,成了她的重生之地。 1905年她给自己取了“玛塔·哈丽”这个名字,马来语里是“黎明之眼”。 她披着从殖民地淘来的纱丽,把爪哇舞蹈的扭胯动作和欧洲现代舞糅在一起,上台时故意踩掉一只鞋,赤脚在灯光下旋转。 《费加罗报》说她“像从东方神话里走出来的”,可没人知道,那些所谓的“神秘图腾”,不过是她在孤儿院墙上见过的涂鸦改的。 香奈儿后来设计的流苏裙,悄悄抄了她舞裙下摆的弧度。 1914年柏林的演出后台,德国情报官递给她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是2万法郎和一枚微型相机。 “法军参谋部的晚宴,你该去看看。”他说。 那时战争刚爆发,她的演出合同被撕毁,银行账户冻结。 她点头时,手指无意识摩挲着盒子边缘和当年攥着母亲丝巾的感觉有点像。 后来法国情报机构也找上她,给她更丰厚的报酬。 她开始在两个阵营间游走,用柠檬汁写密信,把情报藏在舞鞋夹层,我觉得这种在刀尖上找平衡的本事,或许是她从童年就学会的生存技能毕竟那时她连下一顿饭在哪都不知道。 1917年1月的西班牙马德里,她收到德国电报,催她立刻回法国传递“重要情报”。 那时她刚和法军情人路易·加斯顿上校告别,对方塞给她一枚刻着家族纹章的戒指。 她不知道,这封电报早被英国破译团队盯上协约国早就摸清了德国密码的漏洞,故意让她带着假情报回来。 2月13日她刚到巴黎公寓,门就被撞开,士兵搜出那枚戒指时,说这是“通敌证据”。 军事法庭上,法官把一叠照片摔在桌上,都是她和不同军官的合影。 “这些男人给你的情报,害死了多少法国士兵?”她想解释那些只是社交场合的逢场作戏,可没人听。 后来才知道,法军在凡尔登战役输得太惨,正需要个“红颜祸水”来转移民众视线。 7月24日判决下来那天,她在牢房墙上画了朵郁金香,那是荷兰的国花。 刑场上她拒绝戴眼罩,说“我要用眼睛看着自由”。 枪声响起时,她脖子上的珍珠耳环掉在泥里,滚进一个弹坑里。 士兵按命令把遗体运到医学院,解剖时特意切下头颅,泡进福尔马林,标签写着“叛国者H-21”(她的德国间谍代号)。 那时没人想到,这个被嫌弃“伤风败俗”的女人,头颅会在博物馆里待上37年。 1954年巴黎阿纳托密博物馆清点标本,那个编号347的玻璃罐空了。 管理员翻遍1940年代的档案,只找到一句模糊记录:“1951年标本维护时发现变质”。 有人说被她的粉丝偷走了,有人说纳粹占领期间弄丢了,还有老馆员偷偷说,是1950年代初博物馆扩建时,被当成“无主垃圾”扔掉了。 就像她的一生,真相总被传说盖过,连最后这点遗存,都没能落得个清楚。 如今博物馆的那个展柜还空着,阳光斜照时,能看到玻璃上淡淡的水渍,像当年福尔马林蒸发后留下的痕迹。 1906年女神游乐厅的海报复印件挂在隔壁展厅,上面的玛塔·哈丽正扬起纱丽,笑容亮得晃眼。 她终其一生都在抓住点什么从童年的温饱,到舞台的光环,再到两个阵营间的安全感,可到头来,连一颗头颅都留不住。 或许这就是那个年代最残酷的地方:一个女人想靠自己活下去,却总要被贴上各种标签,直到连骨头都不剩完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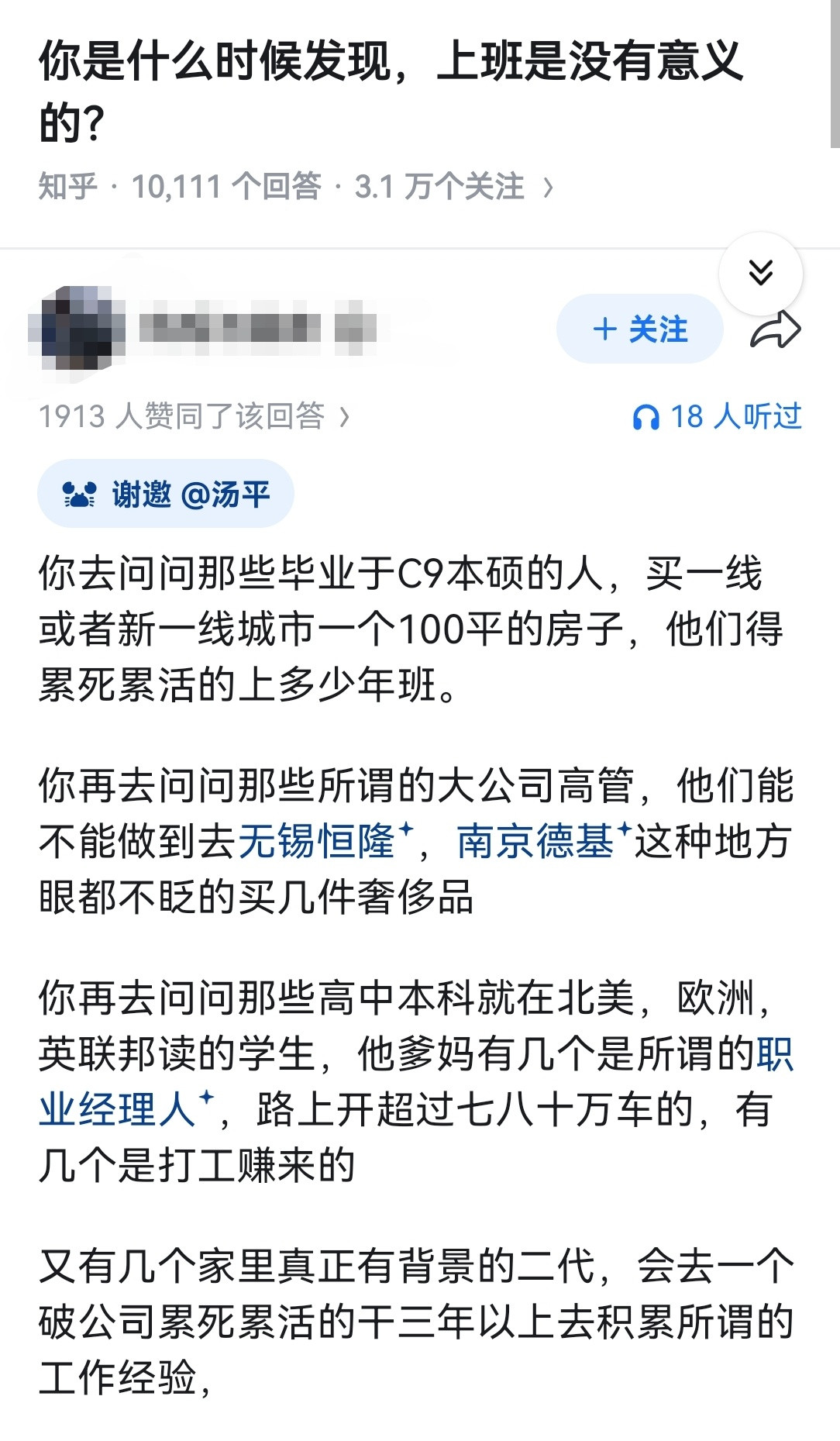
![15岁[???]](http://image.uczzd.cn/2198274213048303461.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