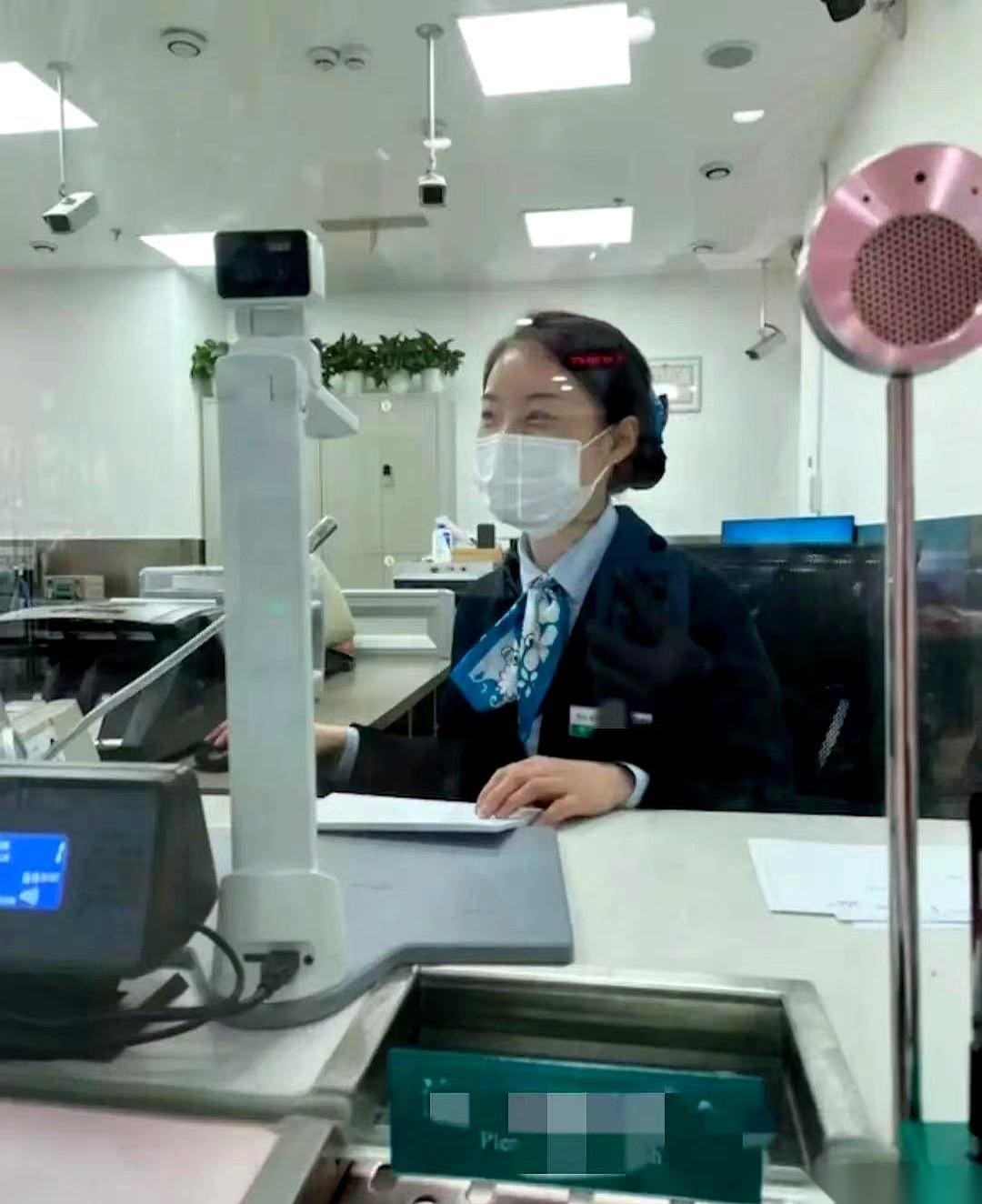老婆在银行上班,闲聊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每个银行都有好多账户几十年没人交易,从几块钱到几千块不等,行里叫“睡眠账户”。她最近整理老档案,翻到个1987年的存折,户名是“周桂兰”,余额栏写着“38.6元”,最后一笔交易是存了两斤粮票兑换的现金,之后就再也没动过。 老婆今晚回来时,制服领口还别着工牌,银灰色的丝巾松松搭在肩上,一进门就把自己摔进沙发里——银行月底结账,她整理老档案整到头晕。 “你知道吗,”她捏着眉心笑,“行里好多账户睡了几十年,几块到几千块,像被人忘在抽屉角落的旧糖纸。” 我给她递水,她却从包里摸出张复印件,边角都卷了:“今天翻1987年的档案柜,碰到个硬壳本,蓝布封面边角磨白,翻开第一页,户名‘周桂兰’三个字是钢笔写的,笔尖顿了顿,‘桂’字的竖弯钩拖得有点长。” “余额38块6,”她指尖点着复印件上的数字,“最后一笔交易备注‘粮票兑换’,旁边铅笔小字标了‘2斤’——1987年,粮票刚退出流通没几年,好多人还习惯把剩下的票证换成现金存着。” 我凑近看,数字被印泥盖得有点模糊,像蒙着层细灰。“她当时是急着用钱,还是只是想把粮票换成现金存起来?” “谁知道呢,”老婆把复印件平铺在茶几上,“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几十块,38块6能买半袋面粉,或者给孩子扯块花布做件新衬衫。周桂兰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的确良衬衫,去银行时手里攥着粮票,指节因为用力有点发白。” 我们俩对着那张纸发呆。窗外的路灯刚好照进来,在“周桂兰”三个字上投下细长的影子,像她站在那里,没走。 “同事说,这种睡眠账户最后大多充公,”老婆突然轻声说,“但这个不一样,你看这存折,内页夹着片干了的槐树叶,压得平平整整——她当时存这笔钱,是不是心里有个盼头?” 我想起我妈总说,1980年代末,谁家要是有几十块活期存款,出门都腰杆直些。“也许她后来搬家了,存折弄丢了?” “或者生病了?”老婆的声音更低了,“我查了系统,开户地址是老城区的巷子,现在早拆了,变成写字楼了。” “也可能,”我突然想到,“这笔钱是给哪个孩子攒的,结果孩子没等到花这笔钱的时候?” 空气静了会儿,只有冰箱制冷的嗡鸣。老婆把复印件叠成小方块,塞进钱包夹层:“明天我跟领导说说,先别标‘睡眠账户’,再放放吧。” “放着等谁呢?” “等周桂兰啊,”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或者等她的孩子,她的孙子——万一有人记得,1987年的春天,奶奶去银行存过两斤粮票换的钱呢?” 我想起前几天收拾老家,在衣柜最底层找到我爸1992年的存折,余额52块3,最后一笔是取了10块买化肥。当时只觉得旧,现在突然明白,那些数字不是钱,是他们攥在手里的日子。 今晚睡觉前,老婆把钱包放在床头柜上,月光从窗帘缝钻进来,刚好照在夹层的复印件上。我仿佛看见1987年的周桂兰,站在银行柜台前,把两斤粮票轻轻放在玻璃上,柜台里的人问她存多久,她想了想,说“活期”——大概是觉得,说不定哪天就需要这笔钱,说不定哪天日子就松快了。 可日子松快了,她却忘了来取。 也许不是忘了,是后来的日子里,有比38块6更重要的事:孩子上学,老人看病,或者只是某天路过银行,想起存折在家里,想着“明天再来”,然后明天复明天,就过了几十年。 老婆翻了个身,迷迷糊糊说:“明天我再查查周桂兰的开户信息,说不定能找到她的后人。” 我没说话,只是摸了摸她的头发。其实找不找得到又怎样呢?38块6现在买不了半袋面粉,甚至买不了一杯奶茶,但1987年那个把粮票换成现金的女人,一定在存款单上写下“周桂兰”三个字时,心里有过一个闪着光的瞬间——就像我们现在,把工资存进卡里时,想着下个月要给孩子买的玩具,要带父母去的医院,要和爱人过的周末。 那些被时间盖住的数字,原来都是没说出口的盼头。 天亮时,老婆已经走了,我在茶几上看到张便签,是她的字迹:“周桂兰的存折原件我锁档案室铁柜了,钥匙贴在柜门内侧——等她来。” 我没说话,只是把便签夹进了我的笔记本。夹在1987年的那一页。
老婆在银行上班,闲聊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每个银行都有好多账户几十年没人交易,从几块
若南光明
2025-12-16 21:33:31
0
阅读: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