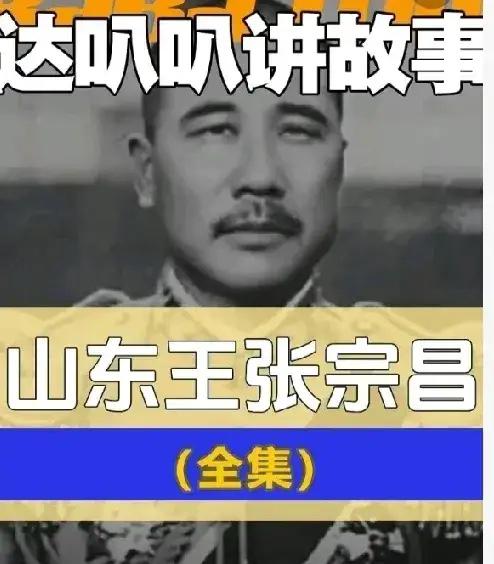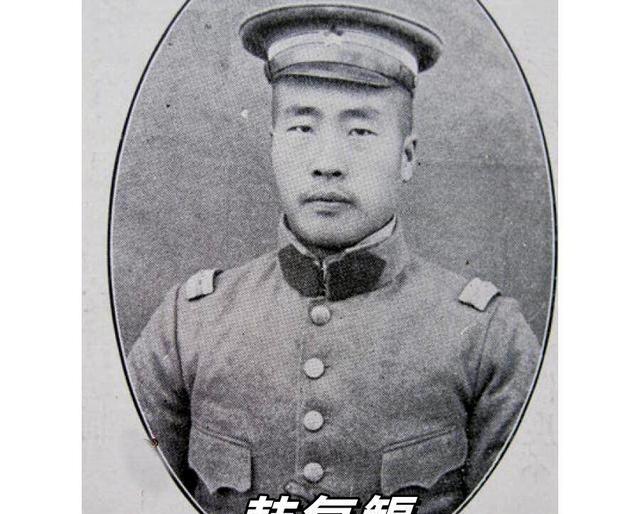张宗昌准备处决一个逃兵,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200军棍,可棍字也不知道怎么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底细,便说道:“这兵胆大包天,敢临阵脱逃,不能轻饶。” 搁在民国军阀里,张宗昌的“没文化”早就不是秘密,可当着一屋子参谋副官的面,总不能承认自己连俩常用字都不会写。他盯着案头的白纸,笔尖在纸上戳得咚咚响,脸涨得通红——刚才还拍着桌子骂逃兵“丢尽了奉军的脸”,转头要写处置手令,却卡在了最关键的字上。 这逃兵是刚补入部队的新兵,跟着大部队开赴前线时,趁着夜色偷偷溜了,没走多远就被巡逻兵抓了回来。张宗昌本来就因为战局不顺一肚子火,当即拍板要“就地正法”,杀一儆百。可真要落笔写“毙”字,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只剩个“死”字,可觉得不够威风,想换“枪决”又不会写,干脆打算改成打军棍,至少能显露出“网开一面”的样子,可“棍”字的偏旁到底是“木”还是“扌”,他琢磨了半天也没头绪。 旁边的副官早就看出了端倪。这位“三不知将军”——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姨太太有多少,平时签字画押全靠画圈,遇到正经文书,要么让秘书代笔,要么找个借口把人打发了。今天偏偏赶上他心血来潮,要亲自写手令,结果闹了这么个窘境。副官想上前提醒,可又怕扫了张宗昌的面子,毕竟这位军阀的脾气出了名的暴躁,前几天还有个参谋因为说错一句话,被他罚去喂马。 张宗昌猛地把毛笔一摔,宣纸被墨汁溅得星星点点。他梗着脖子,眼神扫过底下低头不语的众人,语气比刚才更凶:“这兵既然敢逃,就说明心里没把军纪当回事!打200军棍太便宜他了,传我命令,拉到操场上去,让全体官兵都看着,重责400军棍,要是还能站起来,就给我拉去挖战壕,累死算完!” 他故意把处罚加重,就是想转移注意力,让没人敢深究他为啥突然改了主意。 士兵被拖下去的时候,腿都软了,嘴里不停喊着“饶命”,可张宗昌坐在堂上,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心里暗自庆幸,还好反应快,没让这帮手下看出自己的底细。可没过多久,就有参谋偷偷跟副官咬耳朵:“将军今天咋回事?明明说要毙了,怎么又改成军棍了?” 副官赶紧捂住他的嘴,压低声音说:“少多嘴,将军自有分寸,咱们照着办就是了。” 其实副官心里跟明镜似的,将军哪是有分寸,分明是写不出字,又拉不下脸。 张宗昌的没文化,在军中早就闹出不少笑话。他当年主政山东时,想附庸风雅办诗社,写的诗被人传得沸沸扬扬,“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至今都是民国笑谈。可笑话归笑话,没人敢当面戳破,毕竟他手里握着兵权,脾气上来了,人命比草芥还轻。就像这次的逃兵,400军棍下去,人早就没了半条命,拉去挖战壕没几天就没了气息,说到底,还是没逃过一死。 有人说,张宗昌这是“草菅人命”,可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人命本就不值钱。他没读过几天书,靠着投机倒把和一股子蛮劲当上军阀,治军全靠暴力威慑,根本不懂什么叫“恩威并施”。不会写“毙”和“棍”字,只是他愚昧无知的一个缩影,更可怕的是,这种愚昧还伴随着生杀大权,让无数底层士兵成了他权势的牺牲品。 后来这事渐渐在军中传开,没人敢明着说,只能暗地里当作笑料。有一次,张宗昌又要处置人,秘书主动上前说:“将军,您口述,我来写。” 张宗昌瞪了他一眼,可还是点了点头——他心里清楚,自己那点文化底子,再闹几次笑话,怕是连手下都要不服了。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没想着学认字,依旧我行我素,直到后来兵败下野,还带着一身的荒诞与残暴。 张宗昌的故事,看似是个荒诞的笑话,实则藏着旧时代的悲哀。一个没文化、没底线的军阀,靠着枪杆子就能主宰他人的生死,而那些像逃兵一样的底层士兵,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不会写两个字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力让愚昧变得肆无忌惮,让生命变得毫无尊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