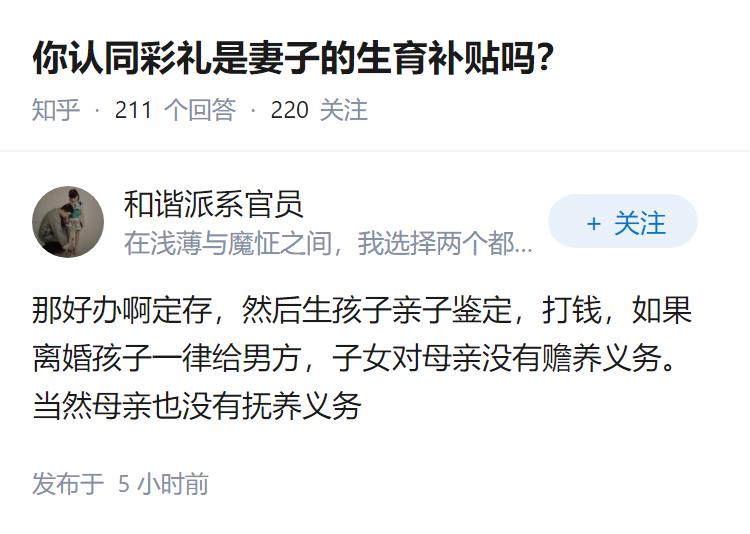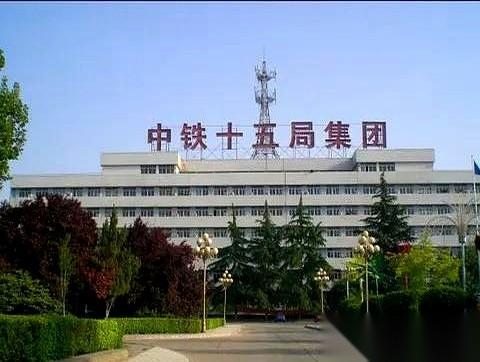黑龙江漠河惊现“雪线碑!林场伐木炸山,冻土裂开一道冰窟,内立一具身披兽皮的枯尸,双臂环抱一株未燃尽的松明火把,怀中皮囊封存三十七张手绘地图。 揭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寒冬,一位鄂伦春猎人妻子为救被暴风雪围困的边防军驿马队,孤身穿越“鬼哭岭”三百里无人冻原,以命引路、血染雪道的泣血传奇 2024 年漠河边防军巡逻道上。 新兵小张裹紧防寒服,接过老兵递来的半截松明火把。 “这火把,得照着雪母当年的路子举。” 老兵的声音裹着寒风。 雪没过脚踝,老兵指着远处的树:“看见树疤没?那是她辨路的记号。” 小张望着跳动的火苗,听老兵说起 1900 年的那场风雪。 1900 年腊月雪母家的木屋外。 巴罕刚打猎回来,看见妻子在整理兽皮行囊。 “你真要去?鬼哭岭的雪能吞人。” 他攥住妻子的手。 雪母摇头,把孩子的小棉袄塞进怀里:“他们等着活命。” 她弯腰捡起地上的驯鹿粪,塞进皮囊 —— 这是鄂伦春人的引火物。 2024 年漠河民俗馆的库房里。 研究员小林正修复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刻着模糊的 “雪” 字。 这是 2015 年冰窟旁发现的,专家推测是驿马队立的纪念牌。 木牌边缘有刀削的痕迹,像是仓促间刻成的。 小林轻轻擦拭木牌,想象着百年前士兵们刻字时的心情。 1900 年雪母跋涉的第五天清晨。 她蹲在雪地里,用冻裂的手指扒开积雪。 找到几株深埋的石蕊地衣,塞进嘴里 —— 这是能抗饿的野菜。 远处的太阳刚露边,她按鄂伦春古法,用影子判断方位。 皮囊里的地图被体温焐着,背后的士兵名字已被汗水浸软。 2024 年漠河小学的课堂上。 老师李娜展开一张复刻的兽皮地图,孩子们凑过来看。 “雪母用鹿血混炭灰画路线,雪再大也不会晕开。” 她指着地图上的红点:“这是她割手做的标记,怕队伍走散。” 后排的鄂伦春族男孩举起手:“我爷爷说,这是咱们的护路符。” 1900 年驿马队被困的第七天。 士兵王二柱冻得缩成一团,怀里揣着给家人的遗书。 李照国突然直起身:“你们听!有哨声!” 狼嚎声中,隐约传来狼牙哨的调子,是鄂伦春人唤鹿的信号。 士兵们挣扎着站起来,朝着哨声的方向望去。 2024 年漠河的雪祭活动上。 鄂伦春族老人葛大爷点燃松明火把,递给身边的年轻人。 “每年这时候,都要沿着雪母的路走一段,不能忘了她。 ” 火把队伍蜿蜒在雪地里,像一条跳动的火龙。 葛大爷边走边唱鄂伦春古歌,歌词里唱着 “血痕映雪,路通家国”。 1900 年雪母倒下的那一刻。 她手里的火把还在燃烧,落在雪地上烫出一个小坑。 李照国把她抱起来时,发现她怀里的地图还紧紧贴着胸口。 “咱们走!跟着血痕走!” 他举起火把,声音沙哑却坚定。 士兵们轮流举着火把,踩着雪母留下的血印往回走。 1900 年驿马队脱险后的第三天。 李照国带着几个士兵回到雪母倒下的地方。 他们用刺刀挖开冻土,立起一块木牌,刻上 “雪母引路处”。 有人把仅剩的干粮撒在木牌旁,有人对着木牌敬礼。 “等开春,咱们得回来给她立块真碑。” 李照国对着木牌说。 如今,漠河的冬天依旧寒风刺骨。 边防军巡逻时,还会带着松明火把,沿着雪母的路线走。 民俗馆里,复刻的兽皮地图成了镇馆之宝,每天都有游客来看。 鄂伦春族的老人还在给孩子讲雪母的故事,教他们认路的技巧。 雪母没留下名字,却让漠河的雪地里,永远亮着一盏引路的灯。 信源:探访大兴安岭腹地鄂伦春族“最后的猎人” 2023-03-25 18:51·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