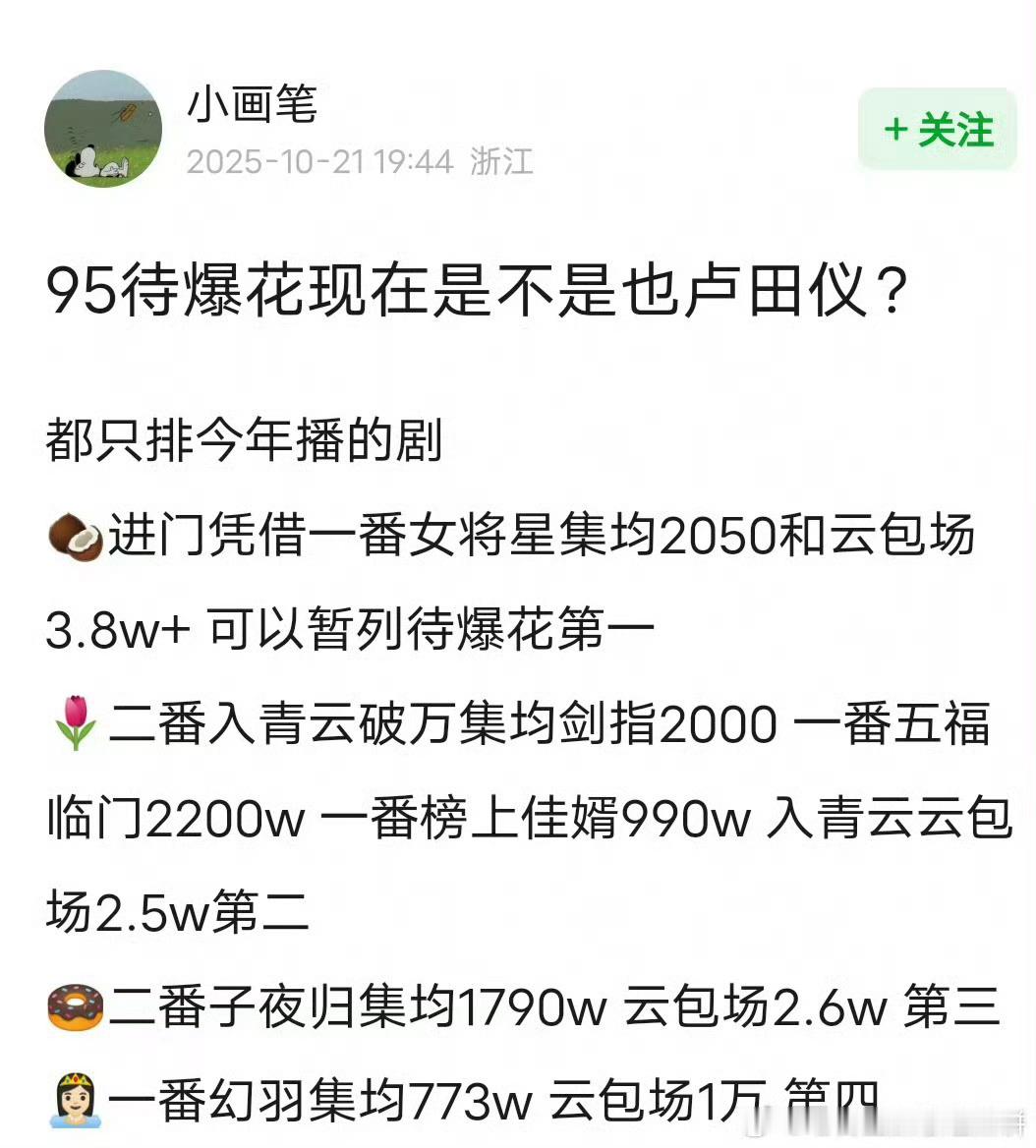昨晚有男的发消息说喜欢我,我睡不着跟他聊,还发了照片,他问 “这是谁呀”,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居然没认出来。 我叫秀莲,嫁给当家的李根五年了。李根是个实在人,天天扛着锄头去地里刨食,力气大,话却少,晚上回来倒头就睡,跟我说话不超过三句,不是 “饭好了没” 就是 “水在哪”。家里的活儿我全包,洗衣做饭、喂猪种菜,忙得脚不沾地,日子过得像口老井,静得没一点波澜。 发消息那男的,是我娘家村的二柱,比我小两岁,以前总跟在我屁股后面“秀莲姐”“秀莲姐”地叫。后来他去南方打工,听说混得还行,好几年没联系了,咋突然冒出来说这话?我盯着手机屏幕,手指头在“你连我都不认得了?”那行字上悬了半天,到底没发出去。删了又打,打了又删,最后只回了个“哦”。 他秒回:“不好意思啊秀莲姐,刚没细看,你这照片……看着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我心里更堵了。不一样?哪不一样?我摸了摸脸,镜子在堂屋柜子上,我懒得去看。反正天天早上起来就喂猪,猪食桶比我还高,溅一身泥点子是常事;然后去菜园子薅草,日头晒得眼睛都睁不开;回来做饭洗衣,晚上倒头就睡,哪有功夫拾掇自己?结婚前我娘还给我买过雪花膏,现在那玩意儿早过期扔了,脸干得起皮也顾不上抹。 正愣神呢,里屋传来李根的呼噜声,跟打雷似的。我把手机塞枕头底下,翻了个身对着墙。二柱又发来一条:“我记得你以前扎俩麻花辫,穿红格子衬衫,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可好看了。” 红格子衬衫……我想起来了,那是我十八岁生日,我娘扯的布给我做的,就穿过一次,去镇上赶集,二柱还跟我搭话,问我是不是去相看对象。那时候我脸都红透了,骂他小屁孩懂啥。现在呢?红格子衬衫早压箱底烂了吧?我身上这件蓝布褂子,还是前年李根他姐给的,袖口都磨破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早,天刚蒙蒙亮。李根还在睡,我轻手轻脚爬起来,去灶房烧火。锅里咕嘟咕嘟煮着玉米粥,我蹲在灶门口,拿根柴火扒拉着火星子,心里乱糟糟的。二柱那句“喜欢我”,像颗小石子扔井里,明明该沉底,偏在水面晃悠,一圈圈荡开。 喂猪的时候,老母猪哼哼唧唧拱我的裤腿,我没好气地踹了它一脚:“拱啥拱!没你的食啊?” 踹完又后悔,它跟我一样,不都是被圈在这院子里,天天吃喝拉撒,有啥意思? 晌午李根从地里回来,满头大汗,一进门就喊:“水!” 我递给他搪瓷缸子,他咕咚咕咚灌下去,抹了把嘴问:“下午去把东头那片豆子薅了,草快把苗吃了。” “知道了。” 我应了一声,把饭菜端上桌,玉米饼子、炒青菜,还有一碟咸菜。李根埋头就吃,吃相不好看,吧唧嘴,以前我还说他两句,现在也懒得说了。 下午薅豆子,日头毒得很,我戴个破草帽,弯着腰一把一把扯草。扯着扯着,手指头被豆荚尖扎了一下,血珠冒出来,我放嘴里吮了吮,咸咸的。突然就想起二柱的消息,他说“喜欢我”,是真的假的?他见过大世面,城里姑娘那么多,咋会喜欢我这黄脸婆? 正琢磨呢,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二柱:“秀莲姐,我下个月回村,到时候去看你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我?看我啥?看我这双粗糙的手,还是看我脸上的晒斑?我回:“别来了,家里忙。” 他回:“忙啥?我帮你啊。” 我没再回,把手机塞回兜里,使劲薅了把草,草根带着泥,甩了我一脸。 晚上李根洗完脚,躺炕上就打起了呼噜。我坐在炕沿,摸出手机,二柱又发了好几条,问我是不是生气了,还说以前就觉得我好,要不是当年他娘不让他跟外村姑娘处对象,他……后面的字我没看,直接把聊天记录删了。 删完我对着漆黑的窗户发呆。外面有虫叫,还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其实我知道,二柱那话当不得真。就像井里的月亮,看着亮堂,捞起来啥都没有。我跟李根,是刨出来的土,实打实的,能种庄稼,能活命。 我把手机关了机,塞进枕头底下,躺下来,挨着李根。他身上有汗味,还有泥土的腥气,以前我嫌难闻,现在闻惯了,倒觉得踏实。老井是静,可静里头有根,扎在土里,拔不掉的。明天还得早起喂猪呢,不想了。
老王到某地出差,在当地找了个姑娘。事情结束后,两人闲聊起来。老王问:“干你们这
【8评论】【35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