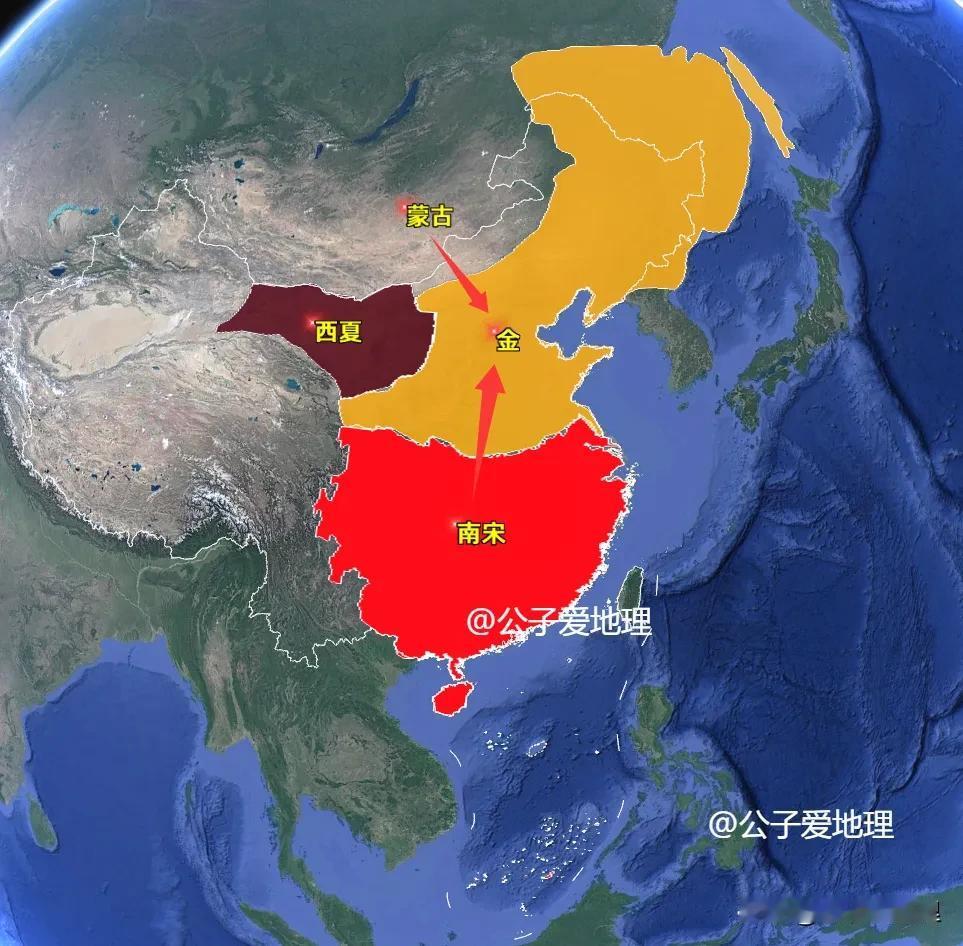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这话说出口的时候,他已经56岁,经历了一次从意气风发到千夫所指的漫长转变。 他当年入主中枢,就是想改一改宋朝那摊子攒了几十年的老毛病。 钱紧,就推青苗法,春荒时候提前放款,农民不再东借西凑; 用度不均,就推市易法,朝廷亲自下场稳定物流,把商人从中间抽掉一层油水; 役法不公,就推免役法,让老百姓交点钱,换取不用服劳役,由政府聘人完成工程; 治安有漏洞,就设保甲,把全国百姓按五五十十编起来,不光看家护院,出事还能拉出来打仗; 军中臃肿,兵员虚报猖獗,就推裁兵法,把闲人撤了,只留能打的; 边防不稳,就鼓励王韶收复河湟五州,这是北宋少有的正面大捷。 表面一派兴旺,实则干群两头怨。 有的老百姓确实得了实惠,也有不少人在执行过程中吃了亏。 书记错填一个数,农民家就莫名欠账; 差役上门要债,不管歉收还是火灾,抠得比高利贷还紧; 一些官吏趁机上下其手,该减的不减,不该收的全收。 京城的老臣们看见这些,把矛头对准王安石,说他的法子是折腾人。 司马光带头号召保守派在洛阳搞起诗会,写满讽刺新政的句子; 苏轼写的诗被传遍大街小巷,说农民都要逃荒了,还钱没处逃。 王安石原本一身正气,谁知不光外头骂,自己提拔的人也靠不住。 吕惠卿自我膨胀,曾布揽权争势,再加上条例司的贪腐丑闻频出,他只觉又疲又灰。 宋神宗原先是他最大靠山,后宫整天在耳边说苛政弄得人心浮动,神宗也渐渐失了热情。 折腾到最后,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改革铺得太快了。 三年不到,十几条法令全部下地,地方官员都还没摸清套路,百姓就被新规压得喘不上气。 熙宁七年西北大旱,反对派说是天意示警,神宗再扛不住,干脆把他外放江宁。 王安石也不争,默默收拾好箱笼,领着数人南下。 刚到江宁,他先是认真当几年知府,案牍上还是事无巨细,田间水利亲自走访,农户租税逐一过问。 后来身体不好,风湿发作,手指僵硬,写字都吃力,人慢慢沉静下来。 他不再写奏章,也不再议政,只寻了钟山半腰一块地皮,搭了几间简房,取名半山园。 园子建得极素净,门外没围墙就几株老竹,屋前有地埂种菜,天气好时他出去走两圈,天冷时披衣望山发呆。 朝廷没几年就真批了他的辞呈,他也不高调辞官,没设宴送行,收拾几件书籍衣物悄悄搬进园中。 江宁老百姓常看到一个老头穿布衣骑只毛驴满街晃,边走边看书,烧饼揣兜里,饿了啃口他吃口,连毛驴也咬一口。 他偶尔收几个零散学生,不讲大义不谈治国,点几本书一起读。 有一次苏轼路过江宁,特地来拜访他。 两人曾政见相左,今日在半山园,一老一中,居士相会,不谈旧怨,畅谈诗文,前后住了近一个月。 王安石专程跑去江边接东坡,东坡衣着未整满脸激动,他却一副淡然模样。 别人一见他俩举止言语,还以为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元丰末年,神宗去世,司马光重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废新法,连免役、青苗都一并除。 王安石此时早已卧病不起,据说听到消息后只是摇头,说了句这法终究不能废。 他没再写任何反驳信,也不再作诗陈情,就像从这场失败中彻底抽身了。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在半山园病逝,终年66岁。 他用遗愿叮嘱家人:不要立碑,不要写墓志铭。 人走了,只剩园中几畦蔬菜,一片幽竹,还有不起眼的茅屋静默在山腰之间。 等到后来朝廷再起风波,他的改革再被评说,已经无人记得那个骑着毛驴、口袋揣着烧饼的倔强老头。 有人说他是空想家,有人说他是先知,更多的人在历史洪流中早已懒得细究。 但当我们回顾那个时代,会发现他是那个最早把制度当回事的人。 他或许太超前,但却从没有放弃改一改旧世界的冲动。 他的一生,就是把自己扔进滚烫现实里,等到被烫得遍体鳞伤后,依旧不说一句后悔。 信息来源:《中国大历史》、《王安石传》、《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