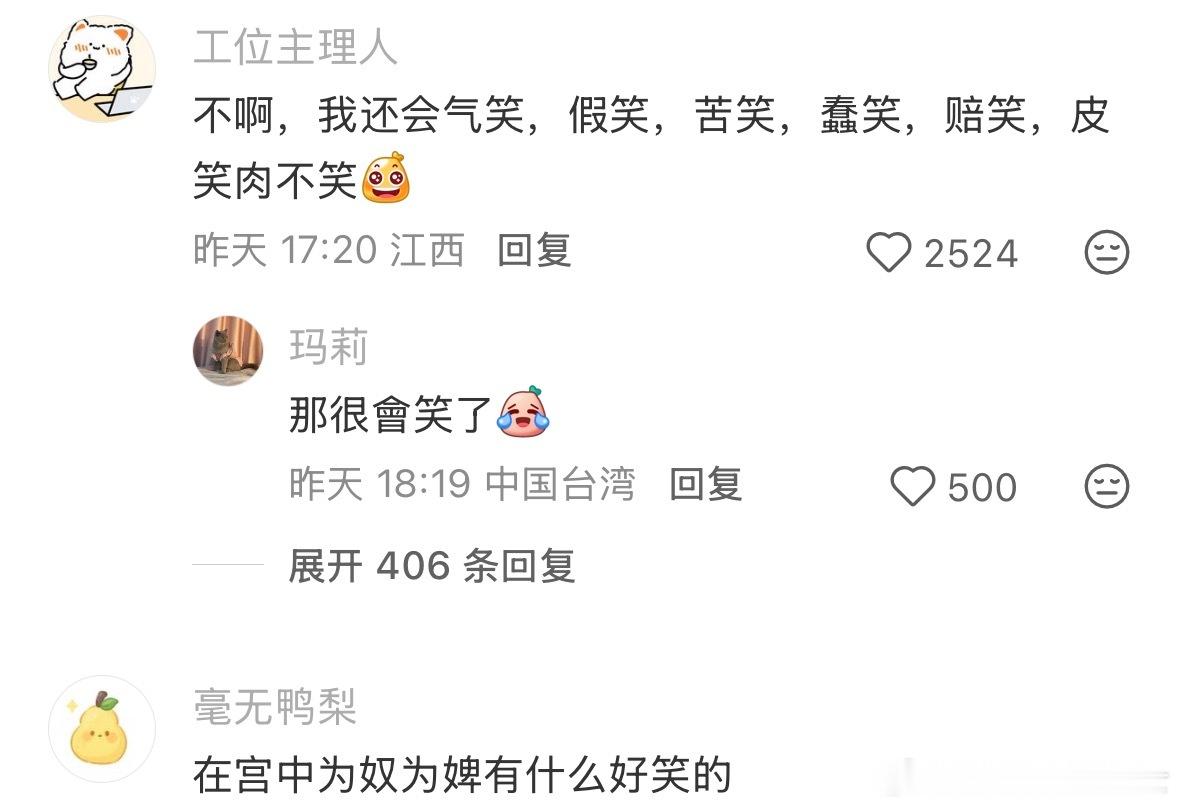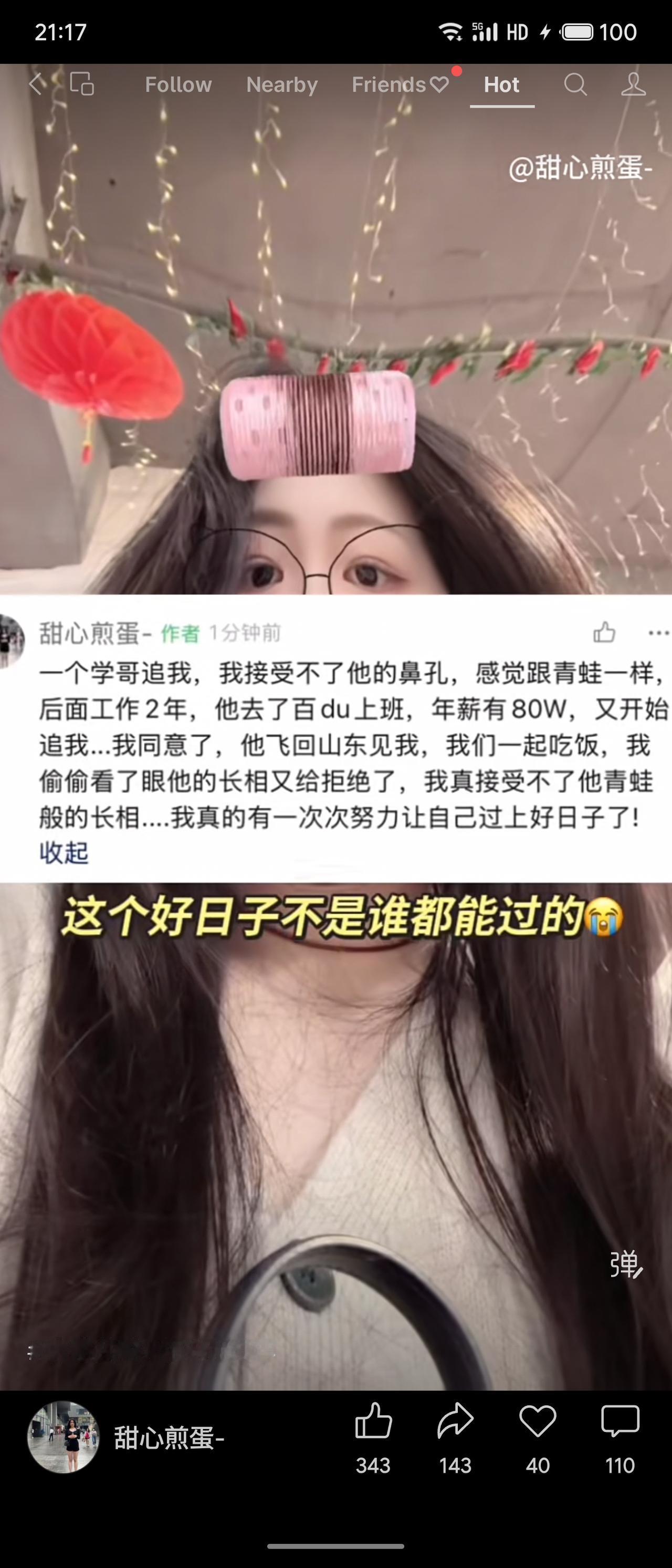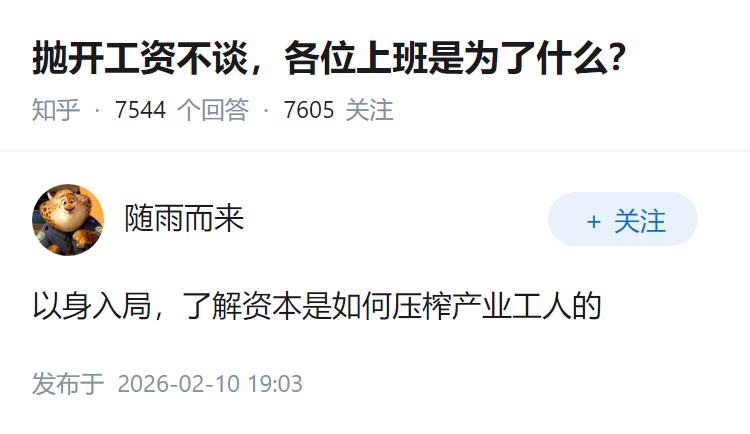你们知道吞金有多痛吗?不是吞金条,是把贴身的金锁片、金链子、金手镯混着热水咽下去。 1950年2月26日的深夜,在寒风阴冷的牢房里,朱枫悄悄从大衣肩衬里掏出一只藏已久的金手镯,又把项上的金锁片和金链子一同取下来,趁着发烧虚弱之中,用牙齿一口一口咬烂,分四次用热水吞进肚子里。不规则的金属边缘划破喉咙,割开肠胃,每咽一块都伴随着钻心的疼。那只金镯掰断时的锋利程度,即便是年过半百的老医生见了都摇头,说自己从医几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硬气的女人。 吞金不是为了求死,也不是一时冲动。朱枫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一旦招供,那些还没暴露的同志就全都危险了。她知道敌人要挖出她手里握着的线索,尤其是与她存在联系的几位高级人员。因此她用近乎自残的方式给自己制造濒死状态,企图拖住敌人节节逼近的步伐。最少拖一天,就可能让更多人转移出去。也许她也想过死,但那时死太容易,活着不说一个字,才最难。 次日清晨,看守打开牢房门时,朱枫已经蜷在床角,满脸苍白,几近昏迷。她的海勃绒大衣肩衬被撕破,地上落着几块金渣。敌人立刻慌了,连夜将她送往医院。一开始用泻药灌她,没有反应,照了X光才知道金饰还停在胃里。特务们急得团团转,不断催医生抢救。毛人凤下令必须保住她的命,因为她是案中关键一环,一旦人没了,整张大网就要崩掉。 医院反复灌药、拍片,两天后金属碎片才完全排出,但折腾到这一步,朱枫身体已经极度虚弱。而接下来等着她的,不是安生养伤,而是最残忍的酷刑。监狱里有个叫龚德柏的人,后来写了一本《黑狱记》,里面记下了当年施刑手段:老虎凳、坐飞机这些是基本操作。火刑才最狠,会拿火焰烧着身上皮肉,甚至点着后往犯人口中烫,一旦不招,就轮番上来。她一边恢复身体,一边对抗人为制造的疼痛,有时昏死过去,醒来继续咬牙撑。她知道,只要口不开,机会就在。 抓她的人说不准她是不是会招,但他们都清楚,朱枫完全有活命的机会。她本可以借被捕之机选择配合,自保脱身。事实上,敌人也确实给过她机会,但她压根没接受。她知道自己身上连接的不只是某个情报,更是一整条地下交通线。吞金不过是开头,真正艰难的是之后这三个月的牢狱煎熬。 朱枫不是天生的硬骨头,她也曾是香港街头送情报时会给孩子带糖的女子。大衣里藏着的那只金镯子,本是她丈夫留下的念想,在最关键的时刻,她选择把它咬碎吞进肚子里。这不是简单的物理行为,而是一次彻底的觉悟与牺牲。当别人还试图活下去的时候,她已经把生死置于脑后,用伤痕累累的身体,在为身后的战友们争取多一点时间。 有个年轻特务试图逼她开口,走过去想拽她的手臂,她一个眼神扫过去,眼神冷得像冰,对方立马退开。她没有高声呐喊,也没有愤怒回击,就是用一副沉默的身体,死死地抗住每一次逼问和抽打。 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押往马场町执行枪决。她临刑前理了理自己的衣襟,站得笔直,一句废话没留。特务连开六枪,将她彻底打倒。 有人说,她吞的不只是金子,更是对信仰的绝对捍卫。这种信仰,撑得住常人难以忍受的疼,也撑得住三个月的酷刑与孤独。金子可以被咬碎,可以被吞进肚子,但那股子不服输的劲,谁也掰不弯。 那个年代,没有天生的英雄。她只是一个发着高烧的女人,在深夜里偷偷咬碎了随身佩戴的金子,然后一步步将自己耗尽,只为了对抗不愿妥协的一句话。 她的故事后来在坊间传开,人们用沉默的敬意讲述她的名字。曾经的影子如今已熔进民族记忆里,也成为红色血脉中的一小节,但却清晰如昨。在很多人心中,朱枫没留下大声喊出的口号,也没给世界留下遗言,但她吞下金子那一刻,就已下定了心,哪怕一滴血都不会留下给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