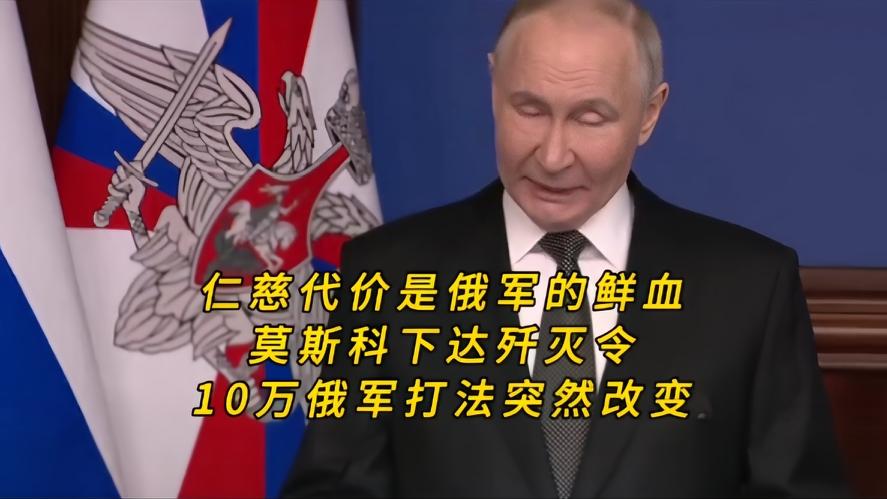1979年,一个叫高华忠的士兵,接到了掩护全营撤退的死命令。 1979年2月23日的那个深夜,云南边境95号高地死一般寂静,这地方刚刚经历过一轮绞肉机般的厮杀,空气里还挂着未散的硝烟味,几个掉队的炊事班战士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归队路线,黑暗中有人脚下一软,踩到了一团湿漉漉的东西。 那触感不对,不像是岩石,也不像是被炮火翻开的焦土,战士打开手电筒,光柱颤抖着扫过地面,所有人瞬间头皮发麻,那是一团“烂泥裹着血”的混合物,再凑近一点,这团“烂泥”竟然有一双眼睛,还在微弱地转动。 这根本没法称之为“人”他的膝盖和手肘处的军裤已经磨烂,白森森的骨头直接露在外面,伤口里嵌满了黑色的砂砾和草屑,最恐怖的是脸。下巴像个破布袋一样耷拉着,原本应该是口腔的位置,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血洞。 几个战士壮着胆子辨认了半天,才敢确认:这是二连一班的班长,高华忠,那个两天前就已经“失踪”被大家默认牺牲了的老兵,要把这具躯体抬上担架成了难题,军医赶到时,试图托起他的头部,结果手刚一碰,高华忠嘴里哗啦一下,吐出来的不是血块。 是碎牙和骨头渣子,那一瞬间,没人敢说话,在场的都是见惯了生死的汉子,但看着这具还在呼吸的残躯,有人当场背过气去。 48小时之前就在这片阵地上,当时高华忠正带着全班9人死守高地,给一营主力撤退争取时间,那颗子弹从左腮打进去,动能瞬间释放,又从右腮穿出来,这种贯穿伤在医学上几乎是判了死刑。 人类的口腔结构瞬间崩塌,下颚骨粉碎性消失,24颗牙齿瞬间变成了锋利的弹片,把舌头搅成了一团烂肉,按照常规战损逻辑,他应该当场休克,或者死于窒息,副连长当时就急了,下了死命令,强行指派两名新兵用担架抬着他撤往后方救护所。 这本该是一次常规的医疗后送,但在战场上,意外总是比明天先到,天黑路熟的新兵少,那个负责护送的小组在丛林里彻底迷了路,这是个绝望的博弈:带着重伤员盲目乱撞,三个人都得死,把他藏好,分头去找路找救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两名新兵做出了符合逻辑的选择,他们把高华忠藏在草丛里,留下了水和干粮,转身没入黑暗,随后的两天两夜,这里发生了什么,只有高华忠自己知道,当救援队后来顺着记号找回来时,原地只剩下一滩干涸的血迹,高华忠不见了。 一个下巴碎裂、失血过多的重伤员,能去哪,现场的痕迹给出了答案:他没有在这个“安全点”等死,也没有试图往后方逃命,地面上拖拽的血痕,指向了95号高地,那是他原本坚守的阵地。 这完全违反了求生本能,在意识模糊的边缘,这个1975年入伍的老兵,大脑里可能只剩下最后一个导航坐标:归队,他不是在爬行,他是在冲锋,但这几十个小时的路程,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没办法吞咽,饥饿感烧得胃里冒火,他就拔起路边的野草,混着泥浆硬塞进那个血肉模糊的喉咙洞里,渴了,就爬到泥坑边,嘴唇已经闭合不上,他只能像荒野里的受伤野兽一样,把脸埋进浑浊的脏水里,依靠本能去舔舐。 白天,云南边境毒辣的太阳把伤口晒得流脓化水,晚上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手掌磨烂了,就用手肘撑着。膝盖磨穿见骨了,就用大腿根部蹭,一寸一寸,硬是把自己从鬼门关拖回了阵地边缘。 直到被炊事班踩到的那一刻,他这口吊着的气的才算松下来,送到后方医院时,医生检查完口腔,摘下口罩时手都在抖,哪怕是最资深的外科大夫,也无法解释这种生理极限下的存活机制,只能插着流食管维持生命。 每次换药,纱布都要从新长出来的肉芽上硬生生撕下来,疼得他全身抽搐,冷汗把床单湿透,但他一声不吭,因为发声器官已经没了,等稍微清醒一点,高华忠用那双还能活动的手,颤颤巍巍地向护士比划,他没有问“我的脸还能好吗”也没有问“以后怎么吃饭”。 他反复比划着同一个动作,直到护士看懂了那个意思:“大部队,都安全撤回来了吗”后来,上级给他记了一等功,授予了“战斗英雄”称号,但在那个年代,这些勋章的分量,往往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这不是一个关于杀敌数字的统计报告,这是一个士兵关于“忠诚”最原始的生理反应,在下巴碎裂、孤立无援的48小时里,支撑他爬过炼狱的,或许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仅仅是因为,他是个班长,他不接受自己掉队。要死,也要死在战友身边。 信息来源:天下贵州人——贵州英雄谱丨十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贵州英雄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