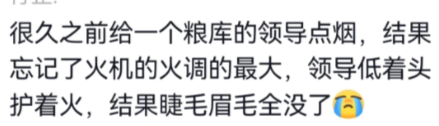1979年的黑龙江农村,红烛摇曳的新房里,上海知青戴建国刚掀开新娘程玉凤的盖头,脸上就挨了一拳。 鼻血滴在红嫁衣上,像极了他背包里那本被撕烂的诗集。 岳母冲进来拽住他胳膊,“你现在走还来得及”,他却抹了把脸笑出声,“没事,我喜欢”。 七年前的夏天,戴建国背着帆布包站在麦地里发愣。 18岁的城里学生哪见过这阵仗,镰刀在手里转得像风火轮。 “顺着麦芒割,手腕别较劲。”程玉凤的声音从麦垛后传来,她递过一块粗布手帕,“擦把汗,知青同志”。 那天的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和他的影子在田埂上叠成了个“人”字。 1971年春节前,戴建国回上海探亲。 临走时程玉凤塞给他个布包,里面是晒干的野山枣。 “等我回来带你去看松花江开江。”他说这话时,没看见程玉凤眼里的泪光。 等他揣着上海奶糖返村,却听说她三天前嫁给了邻村养蜂人。 迎亲队伍路过知青点那天,有人看见程玉凤从花轿里吐了口血,染红了胸前的鸳鸯帕。 戴建国在村头老槐树下找到了程玉凤。 她抱着膝盖蹲在雪地里,看见人就抓挠,棉袄袖子全是窟窿。 “她是被灌了酒抬走的,半夜跑回来就成这样了。”村长叹着气递过张字条,是程玉凤歪歪扭扭写的“等你”。 那一刻,他觉得心口像被镰刀割过,疼得喘不上气。 1978年冬天,知青返城的通知贴满了公社墙。 戴建国收拾行李时,程玉凤突然从门后钻出来,死死抓住他的帆布包带。 她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却把包带攥得发白。 “我不走了。”他对赶来送站的父母说,把上海带来的电子表塞给弟弟,“帮我照顾爸妈”。 那天黑龙江的雪下得很大,他转身时,程玉凤的脚印跟在他身后,像串歪歪扭扭的省略号。 红烛燃尽时,戴建国把撕烂的诗集一页页粘好。 程玉凤蜷缩在炕角发抖,他把她揽进怀里,闻到她发间还留着野山枣的清香。 “当年你教我割麦子,现在我教你认字。”他指着诗集上的“爱”字,“这个字念‘爱’,就像咱俩这样,手拉手”。 她突然咬住他的手腕,他却笑着往她嘴里塞了颗糖,是当年没来得及给她的上海奶糖。 1982年春,儿子出生那天,程玉凤突然抓住接生婆的手说“轻点”。 戴建国冲进产房时,看见她正低头亲婴儿的额头,动作轻得像怕吹破个肥皂泡。 后来她每天抱着孩子坐在门槛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国”和“凤”,画得歪歪扭扭,却再也没撕过书。 2003年的某个傍晚,戴建国在黄浦江畔的长椅上削苹果。 程玉凤靠在他肩膀上,看着对岸的东方明珠。 “当年撕了你的书,赔你本新的。”她从布袋里掏出本崭新的诗集,扉页上是她写的“爱”字,笔画工整得像印刷体。 江风吹乱她的白发,他突然想起那年麦地里,她递过来的粗布手帕,也是这样带着阳光的味道。 那本粘了又粘的诗集现在躺在上海图书馆的展柜里。 泛黄的纸页间还能看见暗红色的斑迹,讲解员说那是鼻血和泪痕混在一起的痕迹。 玻璃柜旁的老照片上,戴建国和程玉凤坐在松花江畔,身后的冰排正顺着江水往下游漂,像极了他们那些年没说出口的话,终于在时光里汇成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