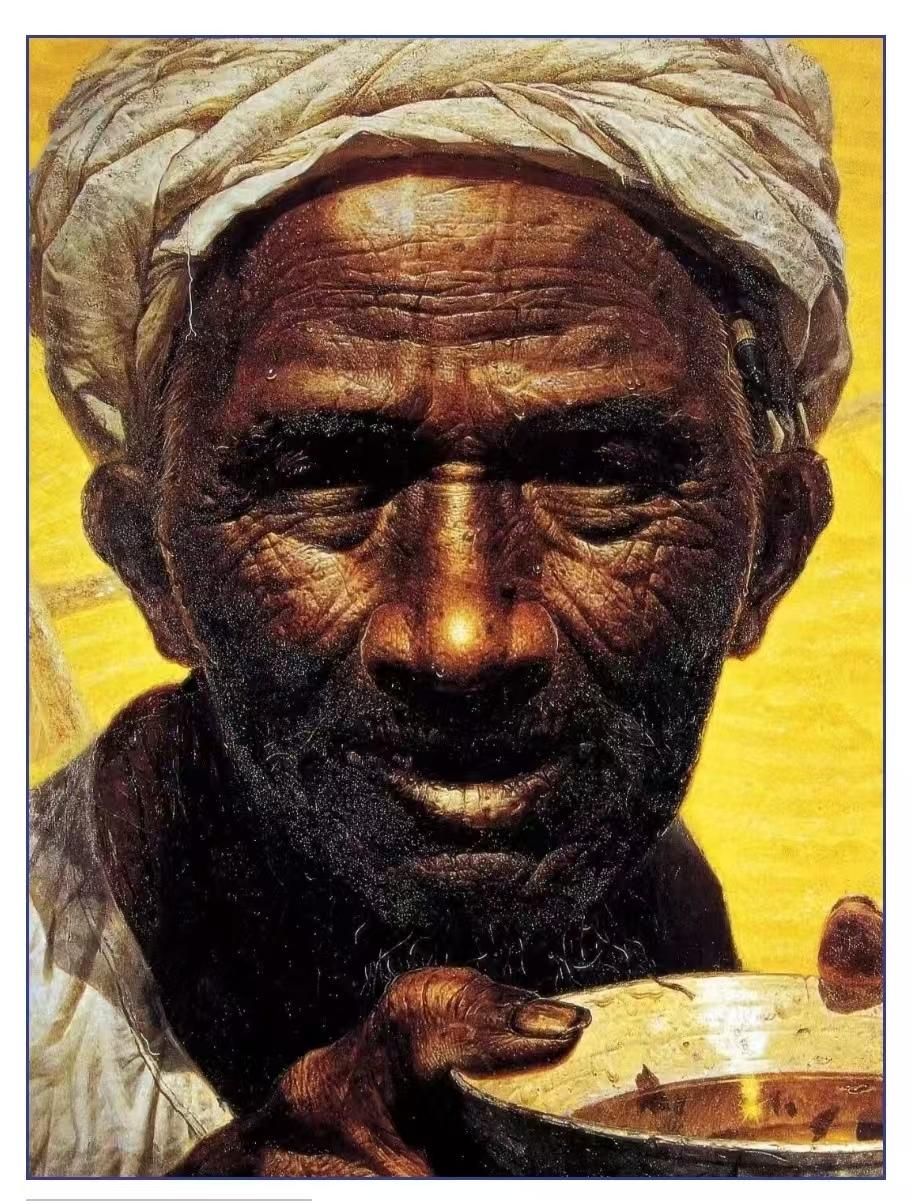《父亲的队长生涯》(二) 黄学勤/文 父亲在三庄工作期间,很少回家,他充分发挥在公社管水电的经验,在三庄的退水闸旁,修建了全乡最大的水磨房。这座双盘磨,给三庄几百口人带来了极大便利,引得周边各村的人路过时都要进去参观。我们庄子的水磨磨面速度慢,乡亲们也常常跑去三庄磨面,因为父亲的缘故,几个生产队之间交往十分热络。也是在父亲的牵线搭桥下,我们党家的几位姑妈都嫁到了三庄,联姻结缘。 常年在三庄辛劳奔波,再加上长期离家、生活得不到妥善照料,父亲积劳成疾,病倒了,时常咳血。经检查,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这可是要命的大病。三庄的百姓们,在我们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将父亲送到了区人民医院治疗,直到父亲住进病房,他们才派人通知我们家——他们早已将父亲当成了自家人。 我清楚地记得,为感谢父亲为三庄作出的贡献,在他住院期间,三庄百姓特意送来了满满一牛车红萝卜,足足有好几百斤。那时的红萝卜市价一斤两元钱,我们把这些萝卜卖掉,换了钱给父亲治病。等到父亲病愈回家时,已是一九六零年的开春了。 一九六零年的情况愈发糟糕。县里浮夸风盛行,即便我们队农业获得大丰收,可那时施行“一平二调”的政策,再好的收成也无济于事。父亲回乡时,县里好多地方都饿死人,田埂上尽是被剥了皮、光秃秃的白杨树。田野里到处都是弯腰扫草籽、秕谷的人,扫起一堆土,背回家用清水漂洗,把草籽沉淀出来晒干捡净。忙活大半天,也弄不到一斤,能收获几两,就算是不错的收获,晒干后好歹能填填肚子。 那时,田野里能吃的野菜被挖得几乎绝种,连开春刚冒芽的柳树嫩条,也成了果腹的食材。吃老鼠肉、吃狗肉,甚至有人割死去娃娃的肉来吃——这些东西,我都吃过。在此之前,没人知道柳芽能吃,是饥饿逼得人们发现了这道“菜”。这个法子流传至今,仍有人会采摘开春的嫩柳芽,给家里的孙辈尝鲜。 那时的人们不放过任何能寻到吃食的地方。种过白菜的地里,常常趴着老人和娃娃,埋头挖取残留的菜根;就连菜地挖过的土块,也不会被放过,人们把土块砸开,在里面翻找菜根和甜梗。饥饿的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长滩大队有个老太太,饿得实在撑不住,竟然把自己的亲孙子带到铺子坑里烧死吃了。老太太最终被判了死刑,枪毙那天,县里在中宁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法院当众阐述她的罪行并宣读判决结果,随后将她押在汽车上游街示众。车开到一家饭馆门前停下,犯人吃了人生最后一碗饭。吃过之后,汽车驶出南门,她被拉下车,在路边的稻田旁受刑。 行刑时,她连挨三枪,竟还坐起身来,笑着说自己没死。最后,还是一个叫大麻子的警察,用手枪补了一枪,才结束了她的性命。事后,她的家人前来收尸。这件事震惊了整个中宁县,甚至传遍全国。 我们队的情况虽没那么严重,可许多人也只能靠吃糠、吃草、吃榆树皮度日,不少人饿得浑身浮肿,娃娃们更是饿得整日啼哭。集体大灶上,每餐都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或是用野菜炒麸皮充饥。 父亲回乡后,挨家挨户调查,发现队里的老人们几乎都浮肿了,只能等着吃“病灶饭”勉强活命。队上有个叫毛万仁的三十多岁光棍,给牲口磨饲料时,趁机偷吃了大量生料,竟活活胀死了,最后还是队上出面帮他安葬。 人命关天,这难关总得想办法渡过。父亲下定决心,冒着风险启用了当年储存的备荒粮。他没有向上级汇报,私自做主将储备粮按人头分给大家救命——这在当时可是犯法的事。 乡亲们的日子暂时好过了,父亲的灾难却随之降临。他被抓去蹲了班房,其实父亲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却依旧义无反顾地做了,只留下少量的种子粮。一个月后,父亲才被释放出来。熬过那段苦难岁月后,不知多少人感念父亲的救命之恩。 不久之后,公社和大队又任命父亲担任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只管一个队的事,头绪少了许多,父亲得以大展拳脚。他将队里十五亩枸杞园分到各家各户打理,萝卜等作物收获后归自己所有,谁投入得多、种得好,谁就能多得利。他又动员全队人,在沟渠两侧都种上蓖麻,沟渠里的杂草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蓖麻长势喜人,到了秋天,枝头挂满了蓖麻籽。全队的吃油问题一下就翻了身,人均分到四斤油。 在这之前,胡麻油一年每人只能分一斤多,家家户户平日里都舍不得用油,只有亲戚登门或是逢年过节时,才能炸点油香尝尝鲜。没有油水,人们的饭量格外大,小伙子一顿能吃下三斤粮食。如今油分多了,村里时常能闻到炸油香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