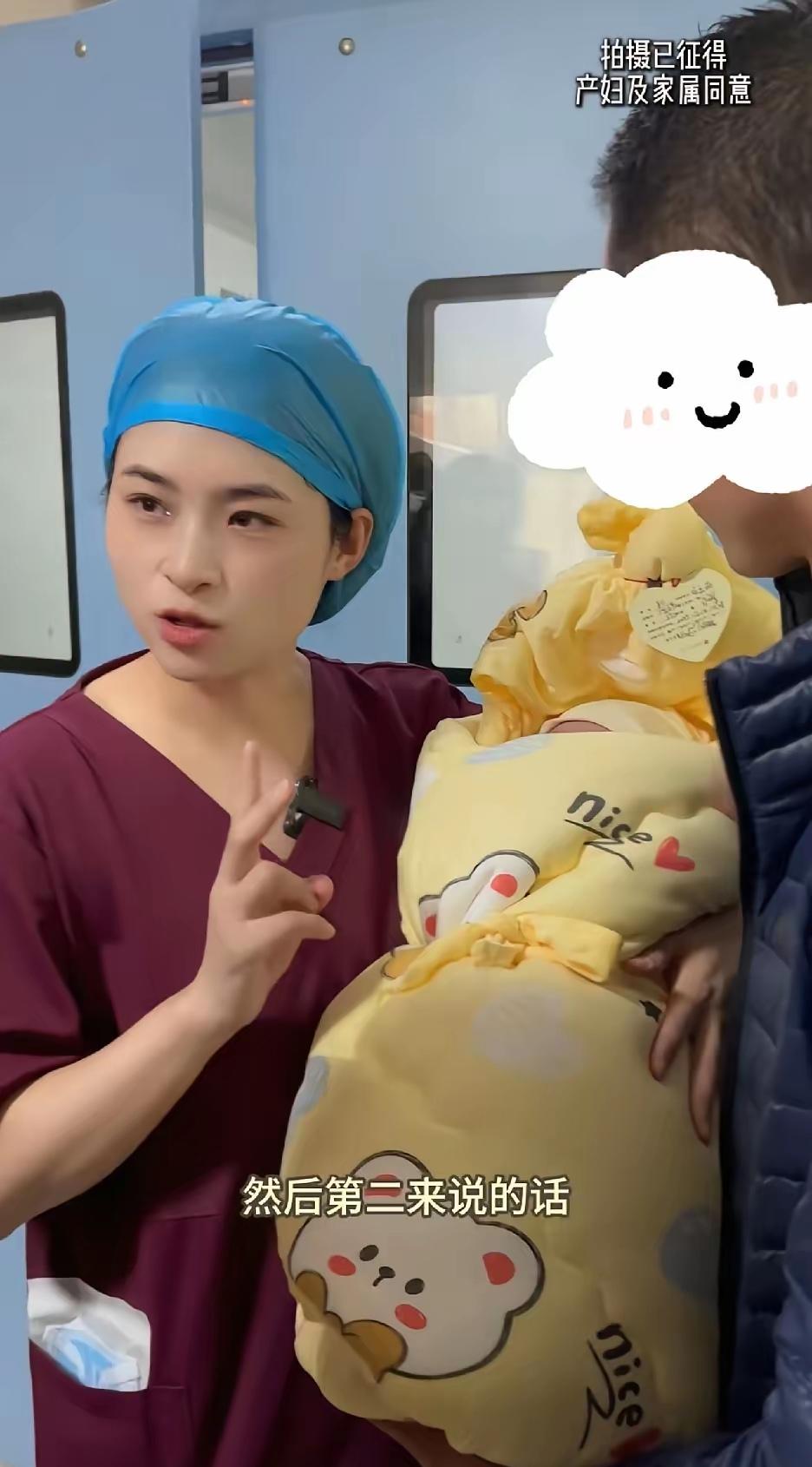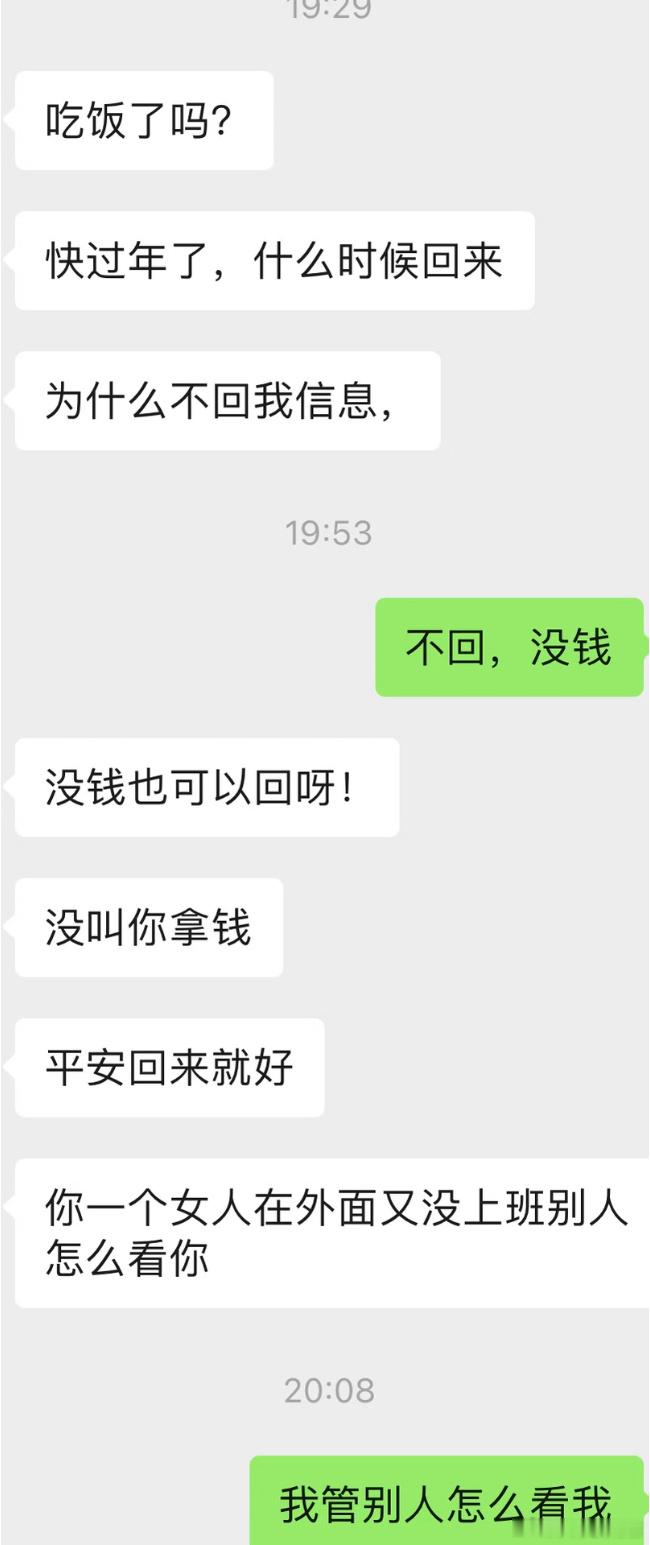同学的母亲去世了,哥哥都没告诉他,一个人操办了丧事,他在康复理疗中心,每月付费2400,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母亲在世时身体不好,父亲腿脚也不得力,所以也只能花钱请人照顾,哥哥心疼他,没让他回来也是情非得已。 康复中心的消毒水味总带着点冷意,阿明坐在轮椅上,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膝盖上的薄毯——那是母亲去年秋天织的,针脚歪歪扭扭,却暖了他一整个冬天。 每月2400的理疗费像座小山,压得全家喘不过气;父亲的腿脚早不利索,拄着拐杖走三步就得歇,母亲在世时总咳,夜里躺不平,家里常年请着护工,哥哥阿强白天跑工地,晚上还得往医院跑。 上周三下午,哥哥提着保温桶来,眼圈红得像熬了几个通宵,阿明问“妈怎么没打电话”,哥哥低头盛粥,声音闷着:“她跟护工阿姨去公园了,走不动,在长椅上晒太阳呢。” 阿明没多想,他连自己穿衣都得护工帮忙,胳膊上的石膏还没拆,哪顾得上琢磨话里的破绽——只是那天的粥,咸得有些异常,像是混了眼泪。 直到昨天,护工收拾床头柜,掉出一张揉皱的缴费单——收款人是殡仪馆,日期正是哥哥说母亲“晒太阳”的那天,备注栏写着“骨灰盒,黑檀木”,是母亲念叨过好几次的款式。 阿强后来在电话里跟护工叹气:“他连自己擦脸都费劲,回来能做什么?灵前跪都跪不稳,难道要让他看着爸拄着拐杖磕头,自己瘫在轮椅上掉眼泪?” 2400块不仅是理疗费,是父亲的降压药,是母亲生前的氧气瓶,更是阿明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哥哥怎么敢让这希望被丧事的尘土埋了? 可瞒着就真的对吗?阿明摸着薄毯上母亲留下的体温,忽然想起小时候发烧,哥哥背着他跑三公里去医院,那时哥哥的背那么宽,现在怎么就弯了呢? 阿明没哭,只是让护工把轮椅推到窗边,看着楼下的树影发呆,手里攥着那张缴费单,指节泛白。 有些爱啊,是明知会疼,也得往心里藏的刺——藏着的人疼,被藏的人,早晚也会疼。 或许下次,我们可以试着说“我需要你”,而不是“你别担心”? 消毒水味好像淡了点,薄毯上母亲的气息却浓了,阿明轻轻把脸贴上去,像小时候躺在她怀里那样——只是这次,没有温温的手拍他的背了。
同学的母亲去世了,哥哥都没告诉他,一个人操办了丧事,他在康复理疗中心,每月付费2
勇敢的风铃说史
2025-12-25 23:21:44
0
阅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