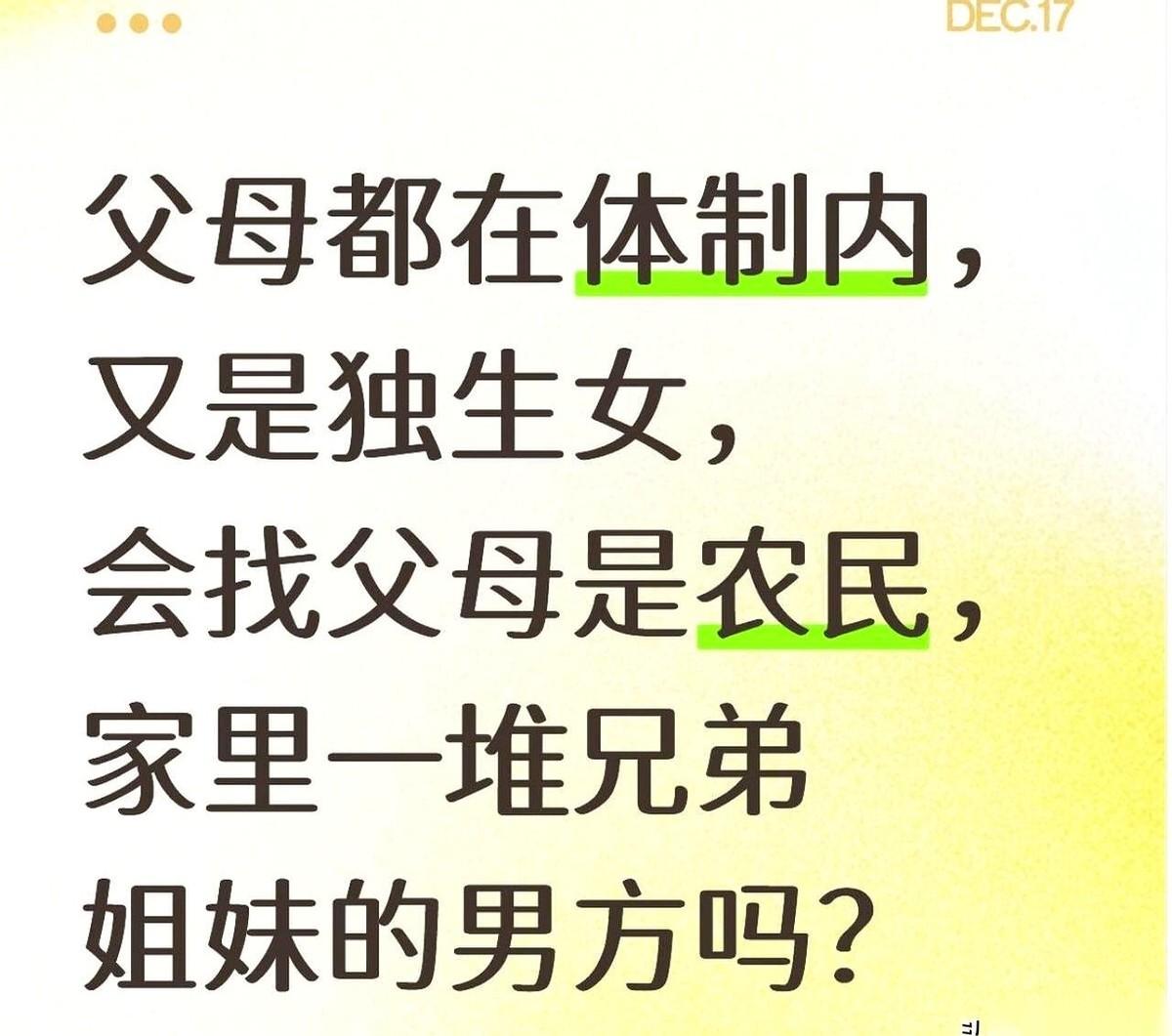我十二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戴眼镜的右派,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他瘦得像根竹竿,衣裳永远洗得发白,却叠得整整齐齐。村里人都叫他“老右”,小孩们见了他就起哄,往他门口扔泥巴。我娘总拉着我说:“离他远点,是犯过错误的人。”可我总看见他在牛棚门口看书,阳光透过棚顶的破洞照在他脸上,眼镜片反射着光,像藏着星星。 十二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戴眼镜的男人。 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村里人都喊他“老右”——大人们说那是犯过错误的右派。 小孩们见了就起哄,往他门口扔泥巴;我娘总拽着我的胳膊:“离远点,当心沾染上坏毛病。” 他瘦得像根晾衣杆,蓝布褂子洗得发毛,却永远叠得方方正正,连补丁都缝得整整齐齐。 可我总看见他坐在牛棚门口看书,阳光透过棚顶的破洞漏下来,在他洗得发白的衣角上晃,眼镜片反着光,倒像是落了两颗星星。 那天我去牛棚附近捡弹珠,听见他在哼歌,调子软软的,像山涧里的水。 他突然抬头看见我,镜片后的眼睛眨了眨,没像其他人那样挥手赶我。 我攥着弹珠僵在原地,他却先开了口:“小朋友,能帮我个忙吗?” 原来他的煤油灯没油了,想借我家火塘的余烬引个火。 我端着燃着松针的破碗往牛棚走,松脂的香气混着牛棚的干草味扑过来。 他接过碗时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凉得像块玉。 “谢谢你啊,”他从怀里掏出颗水果糖,糖纸皱巴巴的,“这个给你。” 糖是橘子味的,甜得我舌尖发颤——那是我那年吃过最甜的东西。 后来我常借口给牛送水溜去牛棚,他教我认“苜蓿”“菘蓝”这些草的名字,还给我讲书里的故事。 有天他翻出本破字典,在扉页上写我的名字,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像春蚕啃桑叶。 “认字是好事,”他说,“字能带你去看更远的地方。” 我问他:“你犯了什么错呀?”他只是笑,眼镜片后的光晃了晃,没说话。 直到某个下雨的清晨,我看见生产队长揪着他去批斗,他的眼镜掉在泥里,碎了一片镜片。 小孩们围着拍手,我却想起他教我写字时,手指在字典上划过的温度。 那天我偷偷把攒了很久的鸡蛋塞给他,他攥着鸡蛋的手直抖,掌心全是汗。 “快走吧,”他推回鸡蛋,从怀里掏出那本字典,“这个你拿着,别让你娘看见。” 后来他被平反回城,走的那天我躲在槐树下,看他背着帆布包,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褂子,背影还是像根竹竿。 他回头望了一眼,好像看见我了,抬手在额前比划了一下——是我们偷偷打招呼的手势。 那本字典我藏在床板下,后来考上大学的那天,我摸着扉页上模糊的字迹,突然想起他眼镜片里的光。 原来那些星星,从来不是藏在镜片里,而是藏在一个人不肯熄灭的眼睛里啊。 现在想想,那天的阳光,牛棚的干草香,还有橘子糖的甜味,其实都是在告诉我:别用标签定义任何人,人心深处的光,要走近了才能看见。 要是再遇到当年那些往他门口扔泥巴的小孩,我真想问问他们:还记得牛棚里那个会讲故事的“老右”吗?他教会我的,比任何课本都多。 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那本字典的纸页都黄了,我还留着。
我十二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戴眼镜的右派,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他瘦得像根竹竿,衣裳永
小杰水滴
2025-12-20 15:28:57
0
阅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