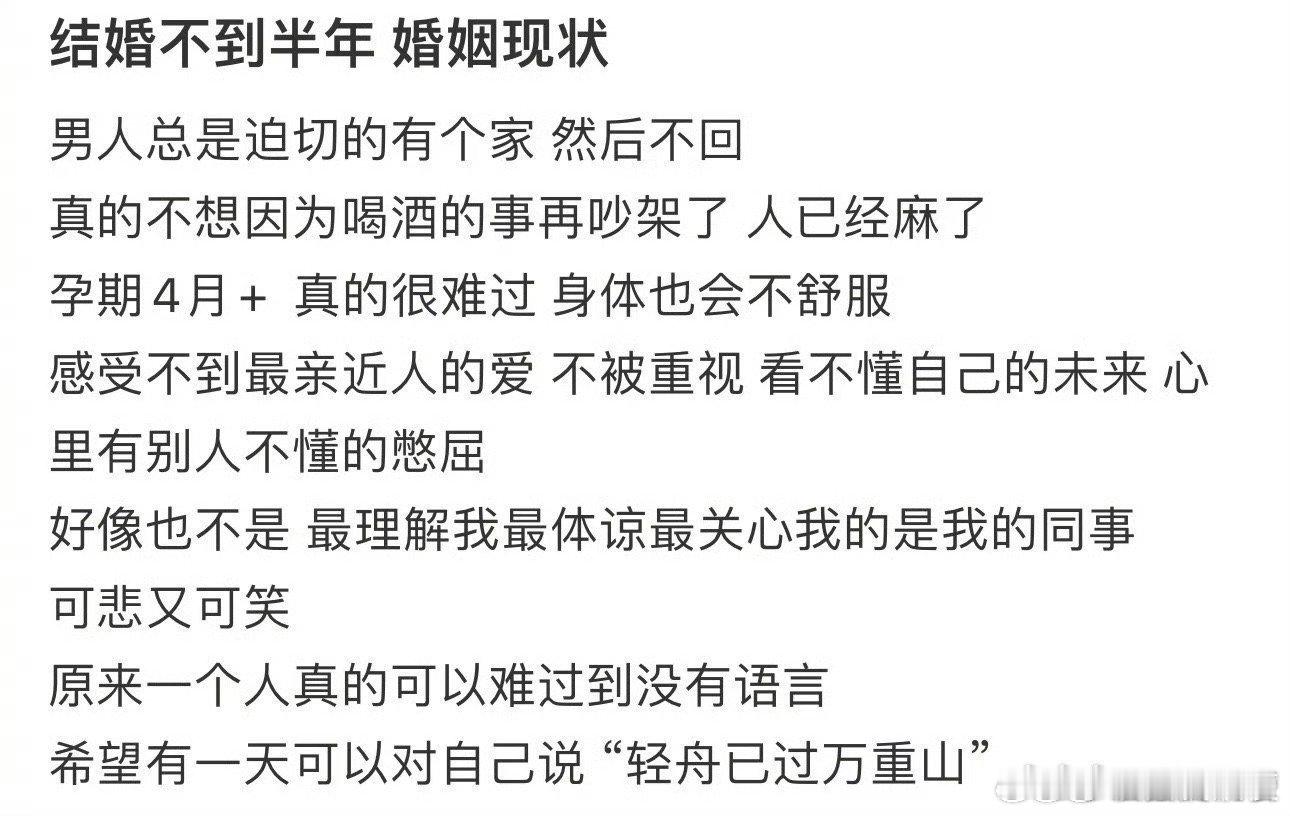“要是她发现了,就说胃疼吃药。” 原来,我坚守了十五年的婚姻,他早把所有台词都写好了。 那张纸条仅有拇指般宽,边角卷曲且脆弱发脆,上面的墨迹是用蓝黑钢笔写下的,字迹工整得如同打印出来的一样。既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却好似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析开我记忆里所有的“偶然”“巧合”和“解释”。 ——2013年冬天,他连续三周在凌晨两点以胃疼为由出门,药盒里空得只剩铝箔残片; ——2016年夏天,我撞见他和女同事在车库交谈,他立马转身捂住上腹说:“又犯病了,得去输液。” ——2020年疫情封控期间,他的手机总是在深夜静音,我询问时,他揉着太阳穴叹气:“胃痉挛,睡不着,怕吵到你……” 我深信不疑。信得那般虔诚,他递来的止痛药我都用温水帮他服下,他蜷缩在沙发上冒冷汗的模样,我还拍下来发给医生朋友,询问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复发了。 可这张纸条,静静地躺在他最常穿的那件藏青色西装内袋里。而那件西装,我熨过十七次,挂了八年,却从未伸手去探过深处。 原来并非他演技高超,而是我太过配合。 并非他隐瞒得深,而是我亲手为他搭建好舞台、递上剧本,甚至在他忘词时,还主动帮他圆场。 最让人寒心的并非背叛本身,而是这背叛早已被预演、校对,反复排练成一套毫无破绽的逻辑链。而我,是唯一不知情的主演,也是唯一认真入戏的观众。 领完离婚证的第三天,我烧掉了那张纸条。火苗蹿起时,灰烬中浮现出最后一行未燃尽的字: “……别提及孩子,她心软。” 我突然笑了。 十五年的婚姻,他没写错一句台词,却漏写了最重要的一句: ——“她心软,但心软的人,也会在灰烬里,第一次看清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