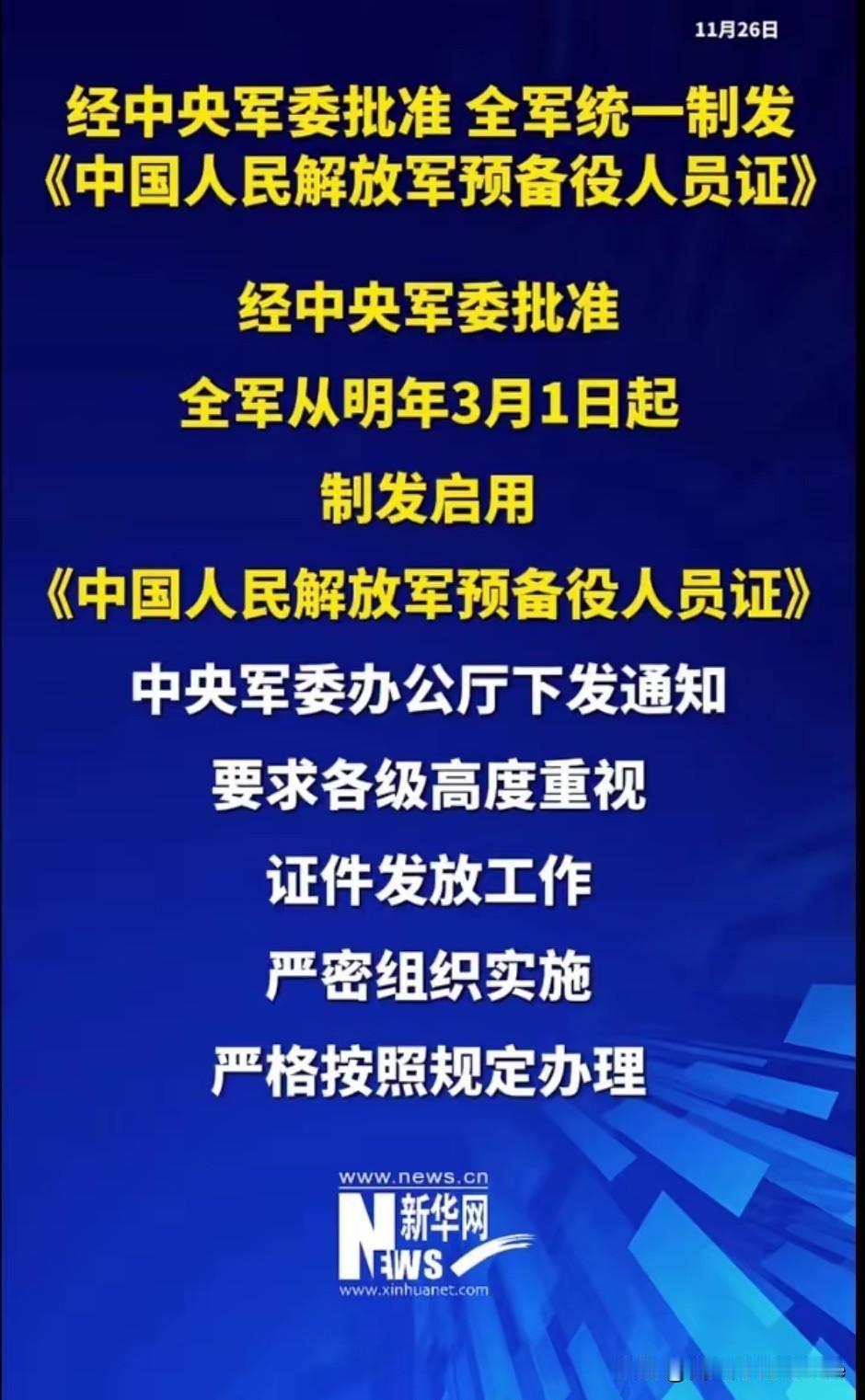我有一位战友,退伍时,就是不离队,非得部队给开带病离队证明才肯走。结果开了,现在领着补助。这事在当时的连队里闹得沸沸扬扬,不少人背后议论他 “钻空子”“斤斤计较”,连平时跟他关系好的几个战友,也觉得他太执拗 —— 大家退伍都是揣着荣誉证、带着行李就走,哪有像他这样,在连长办公室门口蹲了三天... 退伍那年秋老虎正凶,营区的白杨树叶子打着卷,蔫头耷脑地垂着。 我那战友背着半旧的迷彩包站在连部门口,脚边的行李袋拉链都没拉严实,露出里面叠成豆腐块的被子,棱角分明得像块砖头。 我们当时都以为他舍不得走,毕竟一起摸爬滚打了五年,谁退伍时眼眶不红?可他蹲在连长办公室台阶上,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病历单,上面的钢笔字都洇开了边,看着就有些年头。 头天早上出完早操,他没去收拾行李,径直蹲在连部门口的老槐树下,树影在他军靴上晃啊晃。 连长出来打水,铝壶磕碰着台阶叮当作响,他噌地站起来,把病历单往桌上递,“连长,我这膝盖在演习时受过伤,阴雨天疼得站不直,得开个证明。” 连长皱着眉看了看单子,又看了看他,“退伍手续都办好了,荣誉证在文书那儿,下午就能走。” 他没接话,又蹲回树下,手里的病历单被指节攥得更皱了。 第二天炊事班送早饭,老李端着粥盆路过,喊他,“强子,吃点热乎的,凉了伤胃。” 他摆摆手,军用水壶底磨得发亮,里面的凉白开喝了半壶,见了指导员过来,声音都哑了,“不是我胡搅蛮缠,这伤真影响干活,回家种地都使不上劲儿。” 指导员拍了拍他肩膀,没再说啥,转身进了办公室。 第三天晌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直接把小马扎搬到办公室门口,迷彩服后背汗湿得能拧出水,顺着裤腿往下滴,在水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连长从里面出来,手里捏着张印好的纸,“签吧,后续复查拿着这个去军区医院,别耽误了。” 他接过来,手抖着签了名,纸角都被汗浸湿了。 那会儿我们背地里没少嘀咕,宿舍夜聊时,老张拍着大腿,“他这不明摆着钻空子吗?谁身上没点小伤?演习时谁没摔过几跤?” 老李叼着烟,烟雾缭绕里眯着眼,“平时看他挺实在,帮新兵叠被子,替岗哨站夜班,咋这会儿拎不清?” 连跟他睡上下铺的小王,都叹着气说,“荣誉证不比这证明金贵?揣着荣誉回家,不比啥都强?” 我也觉得他执拗,大家退伍都是揣着红本本,带着行李就走,哪有像他这样,在连部门口蹲三天的? 后来半年,我回老家探亲,顺路去他家看看。 推开那扇掉漆的木门,院子里堆着半人高的柴火,屋檐下挂着串干辣椒,红得发亮。 屋里墙上贴着张泛黄的奖状,是他爹的,“烈士光荣之家”五个字边角都卷了,用透明胶带粘着。 他娘坐在炕沿上,腿上盖着厚棉被,见我来,咳嗽着起身,“快坐快坐,让你战友受委屈了,那年我查出尿毒症,每周透析得花钱,他爹走得早,家里就他一个劳力,不去地里干活,吃啥?”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出话。 他从里屋出来,手里攥着个红本本,翻开是那张带病离队证明,“现在每月能领点补助,够我娘透析的药钱,医生说再养两年,我这膝盖就能下地了。” 那天我没多待,走的时候回头望,他正扶着他娘在院子里晒太阳,阳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跟他在连部门口蹲三天的样子重叠在一起,突然就明白了。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被大家议论“斤斤计较”的兵,蹲在连部门口的三天,心里装的不是自己的荣誉,是老娘的透析单? 后来再跟战友们聊起这事,没人再说他钻空子了。 老张摸着刚领的退伍纪念章,叹了口气,“咱当时光看见他蹲门口,没看见他家里的难处,这世上的事,哪能只看表面?” 前阵子连队搞战友聚会,有人提起强子,说他现在在镇上开了个小超市,生意不错,逢年过节还给老连队寄家乡的苹果。 连长喝了口酒,慢悠悠地说,“有些人的执拗,不是为自己争啥,是为身后的人能喘口气。” 我想起他蹲在老槐树下的样子,阳光晒得他脖子通红,手里的病历单皱得像团废纸,可那上面,分明写着一个儿子的担当
我有一位战友,退伍时,就是不离队,非得部队给开带病离队证明才肯走。结果开了,现在
张郃高级
2025-11-27 12:15:19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