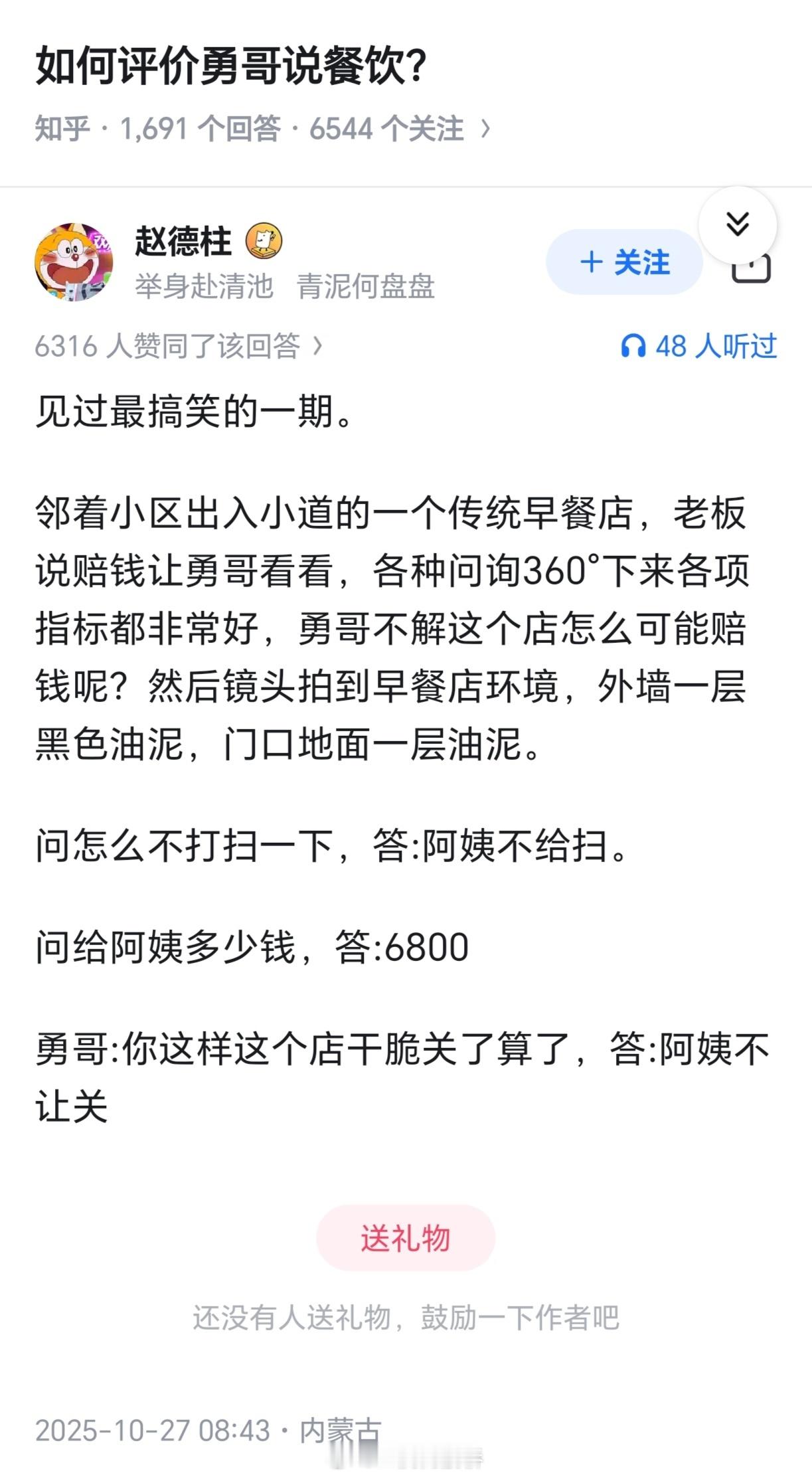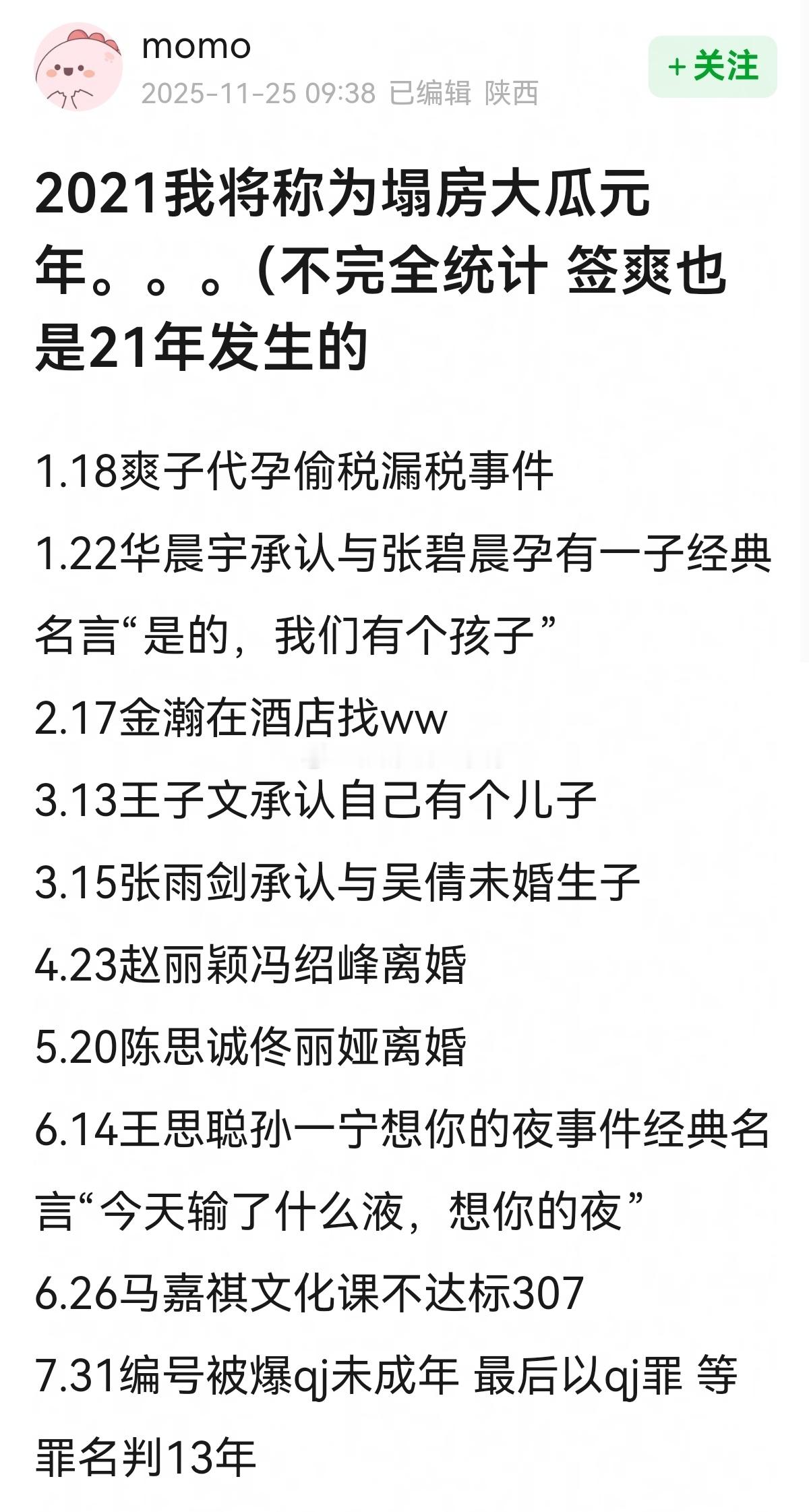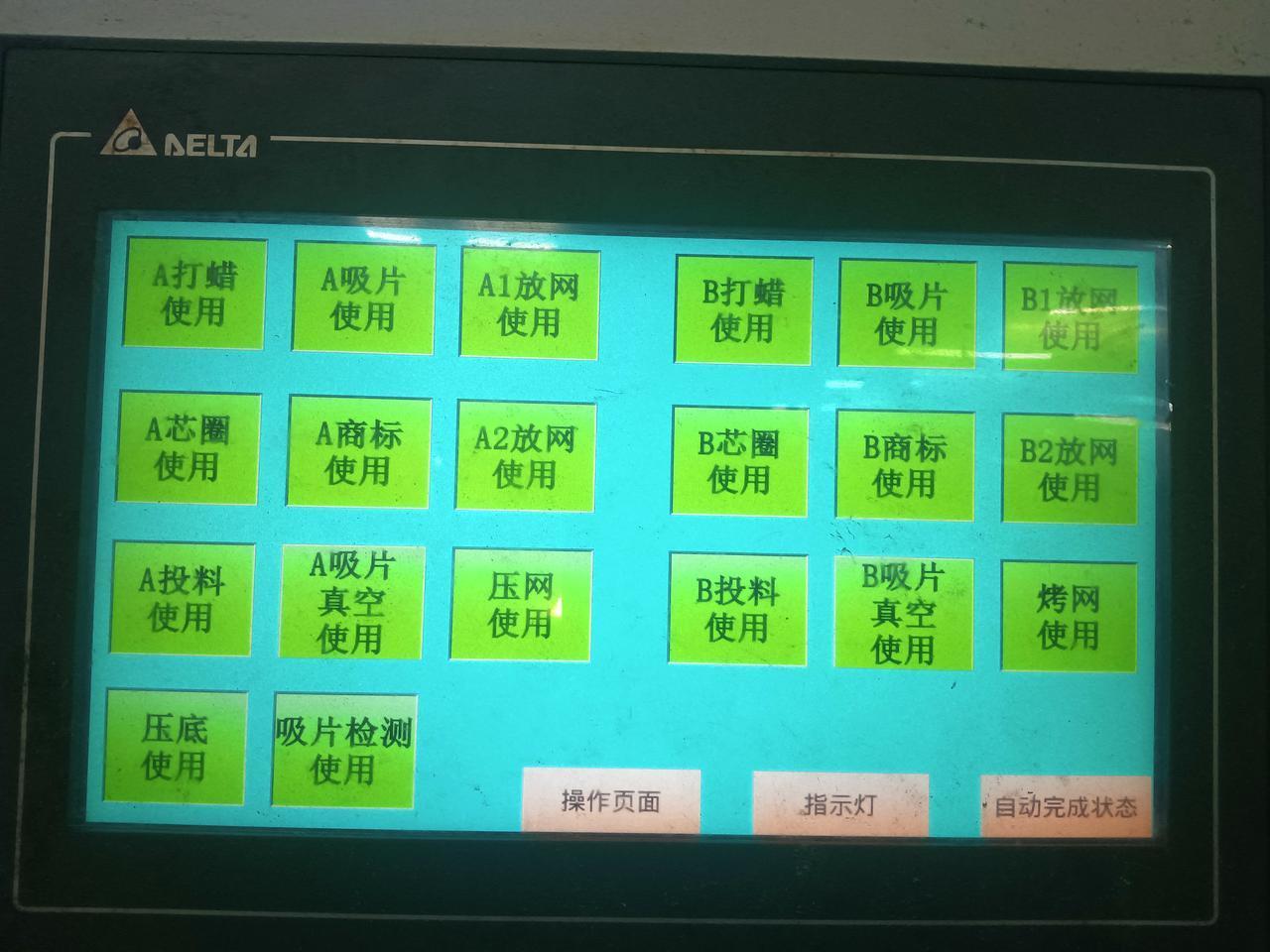当年一家大央企的多辆大轿子车,车前扎着大红花,浩浩荡荡开进我们县城,来迎接即将入职的216名新工人。第一次看见有小姑娘驾驶那么大的客车,感觉非常有精气神儿。那天早上太阳刚冒头,县城的小路上就挤满了人,街边的树上挂着临时扯的彩旗,孩子们在车流里钻来钻去,手里攥着从学校发的小红旗。我站在人群最前面,胸前别着一朵纸做的红花,脚上的新布鞋还没捂热,裤腿还沾着早起割猪草时蹭上的泥点。车队一停下,车门哗啦一声打开,下来一群穿着蓝灰色工装的年轻人,肩上背着帆布包,脸上全是笑。 那年我十七,刚从村小毕业,地里的活儿还没干利落,就被选上了县里的招工——216个名额,我是其中一个。 前一晚娘连夜纳的新布鞋,针脚密得硌脚,我套上时,鞋底还带着浆糊的硬挺。 裤腿没来得及拍干净,早上割猪草时蹭的泥点,在朝阳下泛着土黄。 胸前那朵纸红花是村支书给别上的,边角被我攥得发皱,像颗跳得太急的心。 太阳刚冒头那会儿,县城的小路就活了;彩旗从街边的老槐树上垂下来,红的绿的,被风吹得哗啦响。 孩子们举着学校发的小红旗,在人群里钻,裤脚扫过我的脚踝,带着青草的潮气。 我站在最前面,踮着脚望,突然听见一阵引擎响,浩浩荡荡的车队过来了,每辆车前都扎着大红花,红得晃眼。 打头那辆客车停下时,我才看清——驾驶座上坐着个姑娘,蓝灰色工装袖口卷到小臂,方向盘在她手里稳得很,一点不像我想象中开大车的该有的样子。 车门哗啦一声开了,下来一群年轻人,帆布包在肩上晃,脸上的笑能把早起的凉都烘化。 有人拍我肩膀,“新来的?”我点头,手不自觉摸向裤腿的泥点,怕人看见。 他却指着自己的裤脚,“俺也刚从地里上来,泥点洗不掉,带着吧,都是咱的根。” 那一刻突然想起村支书说的“城里的工厂,地是水泥的,脚不沾泥”,可看着眼前这些带着泥点、帆布包磨出毛边的人,谁不是从泥里长出来的? 姑娘从驾驶座下来,手里拎着个搪瓷缸,冲我们喊:“快上车嘞,食堂早饭还热乎着!”声音脆得像刚摘的黄瓜。 我跟着人群往上走,新布鞋踩在车门台阶上,咯吱响了一声,像在替我说——这下,真要从泥地里,走到水泥路上了。 以前总觉得开大车的得是膀大腰圆的汉子,没想到姑娘握着方向盘时,眼里的光比车头上的红花还亮,原来“精气神儿”跟力气大小没关系,跟心里有没有劲儿有关。 事实是我攥着发皱的纸红花,新布鞋硌脚,泥点没拍掉; 推断是我怕自己土气,配不上这“大央企”的名头; 影响是后来在车间里,每当觉得难,就想起那天的泥点和姑娘的笑——谁不是从土坷垃里往外挣呢? 短期里,那车把我们拉进了厂区,蓝灰色工装成了新的“皮肤”; 十年后同学聚会,有人说我“没了当年的土气”,我却总想起裤腿上的泥点——那是我站得住的根; 当下要是觉得慌,就想想最初的样子,脚沾过泥,才更知道踏实走有多重要。 如今再路过县城那条小路,彩旗早没了,老槐树还在,只是太阳照下来时,我总想起那年刚冒头的朝阳,和一群带着泥点、眼里有光的年轻人,背着帆布包,笑着往车上挤
这阿姨…对你有救命之恩?
【8评论】【3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