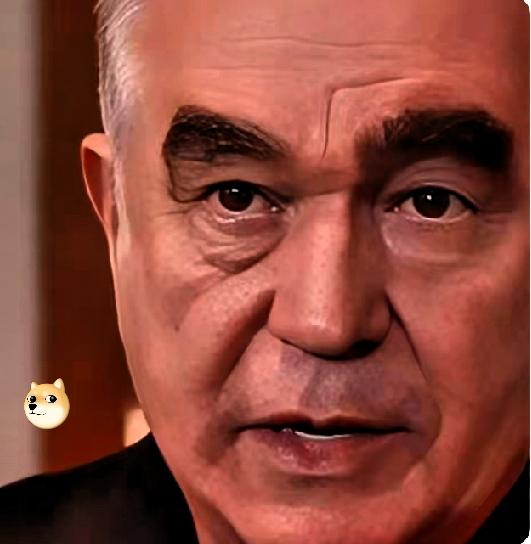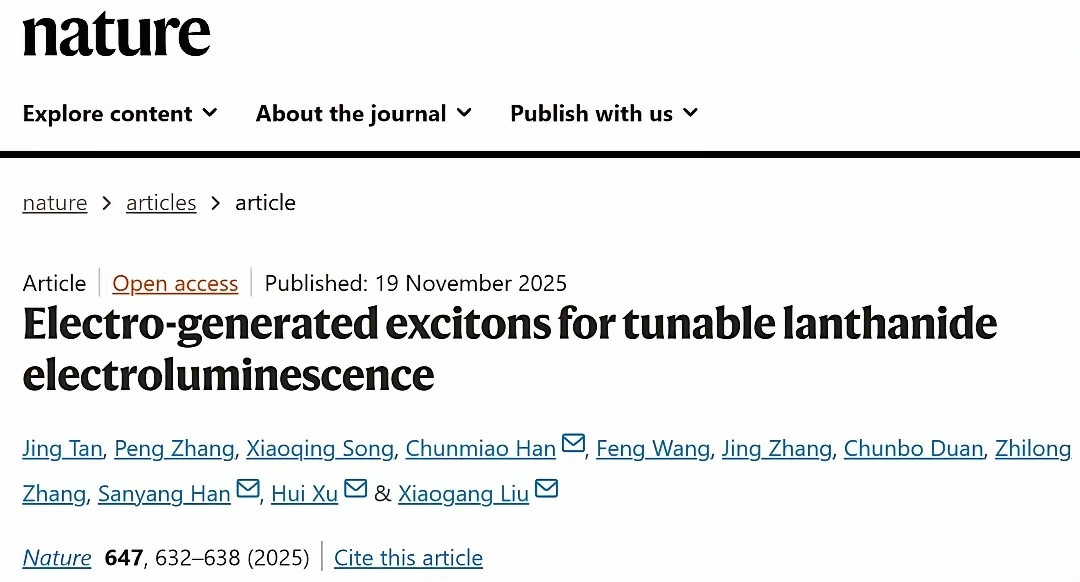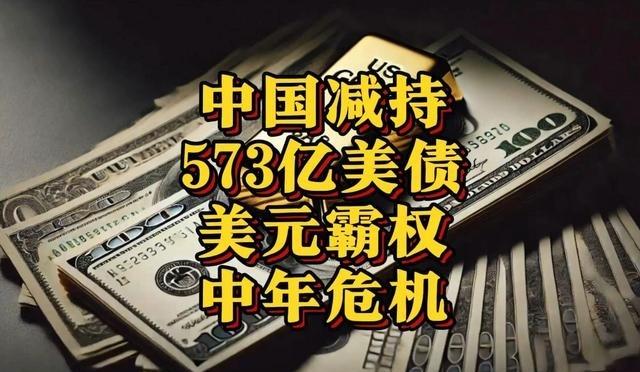不查不知道,原来我国之所以在稀土方面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名叫徐光宪的大科学家,“从0到1,创造性地开创出了一种全新的“串级萃取法”,这才使得我们开始在稀土产业独占鳌头。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2年初春,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到一份加急军工令,任务很简单,却世界罕见:分离镨和钕两种稀土元素,这两个元素化学性质极其相似,像孪生兄弟,国际上几代化学家都在镨钕分离上栽过跟头,当时已经52岁的徐光宪没有退缩,他决定放下手中的量子化学研究,转身迎向这个几乎没人敢碰的难题。 当时国际通行的分离办法是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法,这两套路子生产速度慢如蜗牛,一吨产品要花几个月,成本堪称天价,最令人失望的是分离出来的纯度仍然达不到要求,徐光宪决定换个思路,借用自己早年核燃料萃取的积累,用萃取法来试水,他翻出美国矿业局解密的资料,发现了推拉体系这条被国外放弃的技术路线,美国人曾试过,却只做到纯度85%就宣告失败,最后把专利当废纸一样解密了。 北大改造的一间旧锅炉房变成了实验室,条件简陋得没法说,徐光宪和团队成员开始了最原始的摇漏斗实验,白天摇漏斗、记录数据,一摇就是几小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晚上埋头推导公式,黑白连轴转,有时候一个流程的试验,短的要几个月,长的拖上一年多,一旦某个环节出了岔子,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得推倒重来,他们每周工作80个小时,为了找到准确的配比和工艺参数,反复试验了上百次。 关键突破来自一个看似简单的发现,徐光宪通过深入分析络合平衡的过程,发现了为什么推拉体系在串级后会失效,问题在于,水相和有机相配合不当,到了后面就开始互相拆台,他改变了思路,让有机相里也含有稀土,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相与相之间的有效交换,他选用季铵盐和DTPA络合剂组成新的推拉体系,一次次调整参数,最终让镨钕的分离系数从原来的1.4跃升到4,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1974年9月,徐光宪赶赴包头稀土三厂进行工业试验,这是真刀真枪的考验,任何失误都可能意味着几个月的时光付诸东流,他在包头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待了8次,每次都不厌其烦地查看设备、调整工艺,幸运的是,这一次出人意料地成功了,工厂试制出的镨钕产品纯度达到99.99%,这在国际上还从未出现过。 但徐光宪面临新的困题:怎样把实验室的成果真正转化成工厂能用的生产工艺?为了找到一套可靠的设计原则,他又投入了数年的摸索,经过无数次的模拟试验和实际生产调试,他终于建立起一套串级萃取的数学模型,这套模型的妙处在于一个词叫"一步放大",以前从实验室到工业生产要经历小试、中试这些繁琐的中间环节,流程冗长且容易失败,徐光宪的办法是用计算机直接模拟整个生产流程,实验数据输进去,生产参数算出来,不用再摸黑蹚浑水,这样原来要花一百多天完成的摇漏斗试验,现在只需七天左右。 复杂的工艺一下子变成了傻瓜式操作,一排排萃取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连在一起,你只需在入口投入原料矿浆,各种高纯度的单一稀土元素就从不同出口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项技术一被公开,国内的稀土厂纷纷引进,上海跃龙厂第一个试用,四小时就能完成一轮循环,产量翻了倍。 1976年秋天,徐光宪在包头主持了全国第一次稀土萃取会议,向业界介绍了这套串级萃取理论,震撼波立刻传开,全国各地的稀土工作者都想学这个新方法,1977年,他在上海办起全国讲习班,把核心技术无偿传授给国营企业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短短几年内,技术像火种一样蔓延,包头、赣州、内蒙古的稀土厂全部上马。 到了1980年代初,国际稀土市场彻底变了天,中国高纯稀土大量涌出,价格从每公斤几百美元跌到几十块,那些原先垄断全球市场的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美国莫尔道克矿业公司扛不住冲击,纷纷选择减产甚至停产,人们开始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中国冲击,一个资源大国终于靠自己的技术翻身,从卖原矿的命运中彻底解脱出来。 信息来源:从受制于人到全球领先,他如何改写中国稀土命运? | 徐光宪——中国科学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