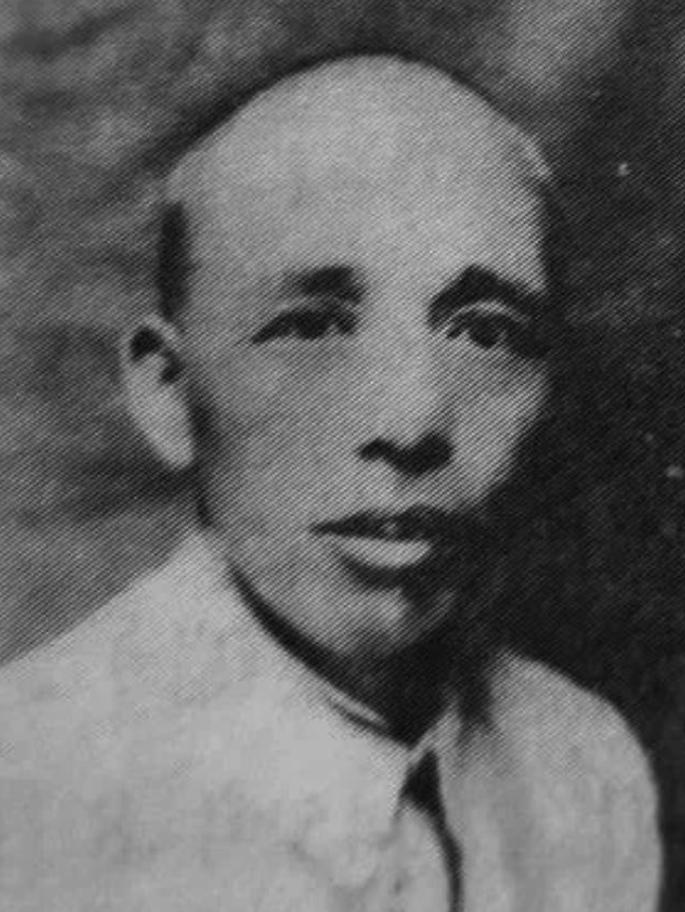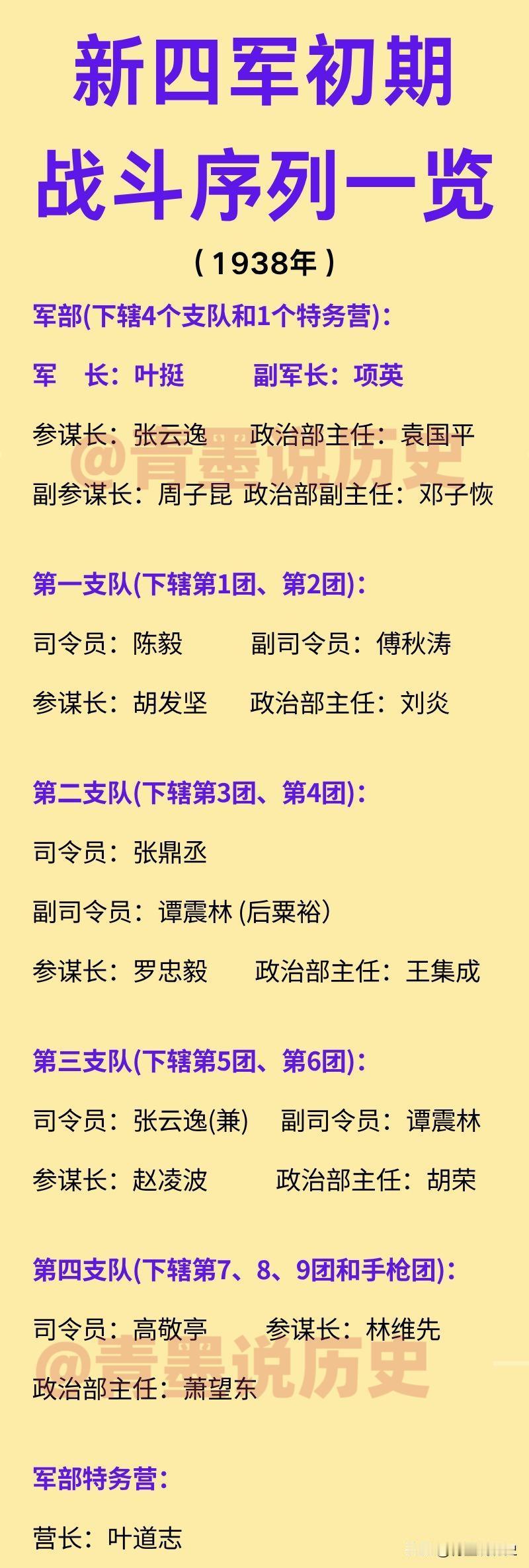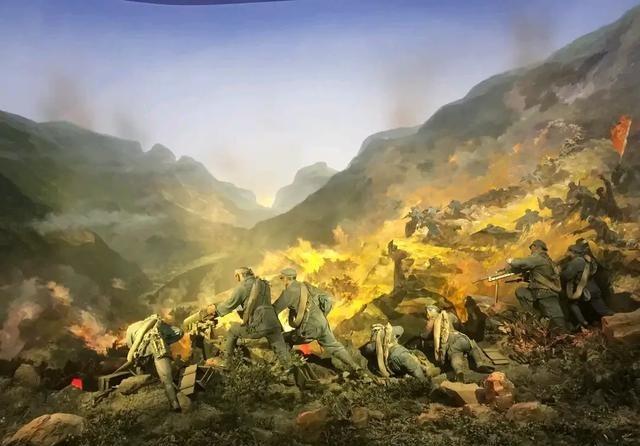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离开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所付出的牺牲之惨烈是令人极为震惊的。蒋介石明令对江西中央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匪区壮丁一律处决”。 没人知道他们何时归来,只知道身后有蒋介石调来的10多个师兵力,带着地方民团,端着步枪、扛着火把,要对苏区进行“梳篦式清剿”。 “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这不是纸上的狠话,是1934年冬至1935年春赣南闽西的真实写照。 国民党军每占一村,便刨开灶台查藏粮,敲遍墙根找夹墙,连田埂边的茅草都要点燃。 福建长汀楼子坝村34户143人,除一名八旬老妪外出探亲,全村被屠戮殆尽江。 西兴国县23万人口,1.2万留守党员和群众被杀害。 青壮年遭“断代性”牺牲,村庄十室九空,连婴儿的啼哭都被恐惧淹没。 留守者手里的武器,多是主力留下的旧枪、土铳,有的只有梭镖大刀。 项英、陈毅领导的中央军区,加上各县区委干部,总共不过万余人,却要牵制几十万敌军,掩护主力突围。 这哪里是战斗? 分明是“用血肉之躯填枪眼”的绝地求生。 绝境中最动人的,是普通人用生命守护的信仰。 福建长汀的深山里,红军伤员隐蔽在山洞。 村民周阿婆每天天没亮就提竹筒装米汤上山,坚持一个多月。 民团发现后,将她绑在村口老樟树上,问“还敢给共匪送吃的吗”,老人梗着脖子答“红军为穷人打仗,我死也得让他们吃饱”,最后被活活烧死。 这场景不是个例,赣南闽西的村村寨寨,都有“周阿婆”。 比群众更悲壮的,是留守党员干部的牺牲。 瞿秋白因体弱未能长征,1935年2月转移中被俘。 国民党当局先派叛徒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却始终戴着圆框眼镜,平静陈述“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甚,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28天后,36岁的他在福建长汀罗汉岭选了块平地坐下,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从容吟诵《赤潮曲》。 枪声响起时,衣襟上还沾着狱中写诗的墨痕。 年过六旬的何叔衡,是苏区“五老”之一,长征时被留下来。 转移途中遇敌军包围,为不拖累战友,他毅然跳下悬崖。 敌军发现时,老人浑身是血,手里紧攥党员证和一支旧钢笔。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陈毅的《梅岭三章》,写于1936年冬的绝境。 当时他和警卫员被敌军围困梅岭山洞,断粮断水七天,靠嚼野果、喝山泉活命。 山洞外浓烟滚滚,他摸着腰间手枪,已做好与敌同归于尽的准备。 最后是猎户冒死引路,才转移到更隐蔽的山洞。 这三年,游击队员过着“吃野菜、住山洞、兽皮裹身”的日子。 即便如此,他们仍坚持学习,收集书报学国文算数,分析形势前途,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 陈毅的《赣南游击词》,道尽了生存的关键。 正如俗语所说“人心齐,泰山移”,民心向背,才是革命最硬的后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号角吹响。 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改编为新四军,前赴后继奔向抗日前线。 这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队伍”,带着三年游击战的烙印,纪律严明、与群众血肉相连、敢打硬仗。 而留守者的牺牲也没有白费。 他们用生命守住的“革命火种”,在新四军身上延续。 从皖南到苏南,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根据地,新四军将士用“铁军精神”,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 如今,赣南的青山依旧,梅岭古道的石板缝里,仿佛还嵌着游击队员的脚印。 瞿秋白就义的罗汉岭、何叔衡跳崖的悬崖、周篮嫂送饭的山路,都立起了丰碑。 那些“石头过刀”的山坳,“茅草过火”的村落,早已绿树成荫,但留守者的故事,从未被忘记。 蒋介石想用“三光政策”抹去红色印记,却忘了“人心不是石头,信仰不是茅草”。 留守苏区的“死亡之师”,用三年游击战证明,真正的革命,不是靠枪炮取胜,是靠“为有牺牲多壮志”的信仰,靠“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民心。 他们的血,染红了国旗的一角,他们的魂,化作照亮后来路的星火。 正如老话所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正是这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留守者,用生命换来的。 铭记他们,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让“信仰”二字,永远滚烫! 主要信源:(安徽省人民政府——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1.6万将士悲壮的留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