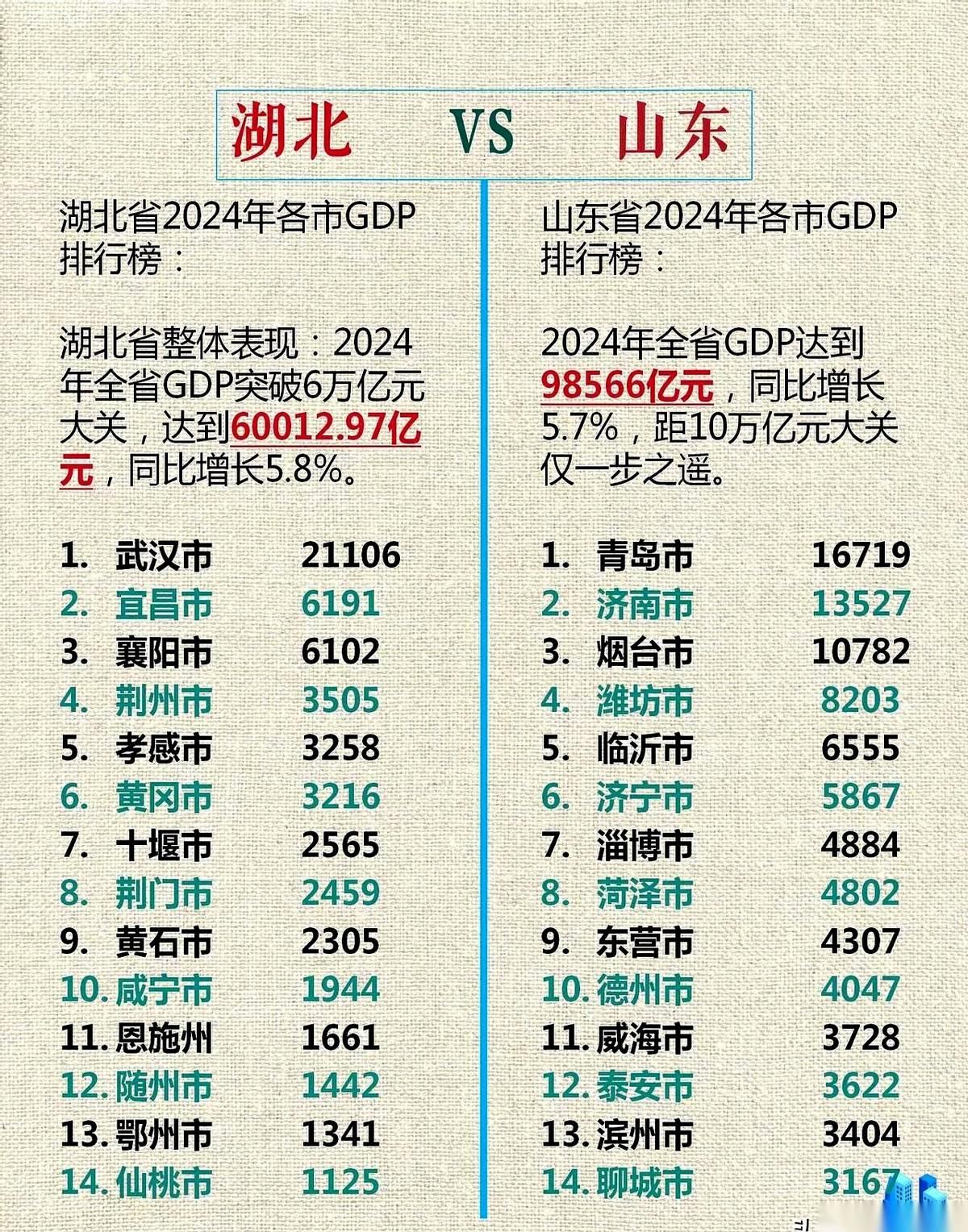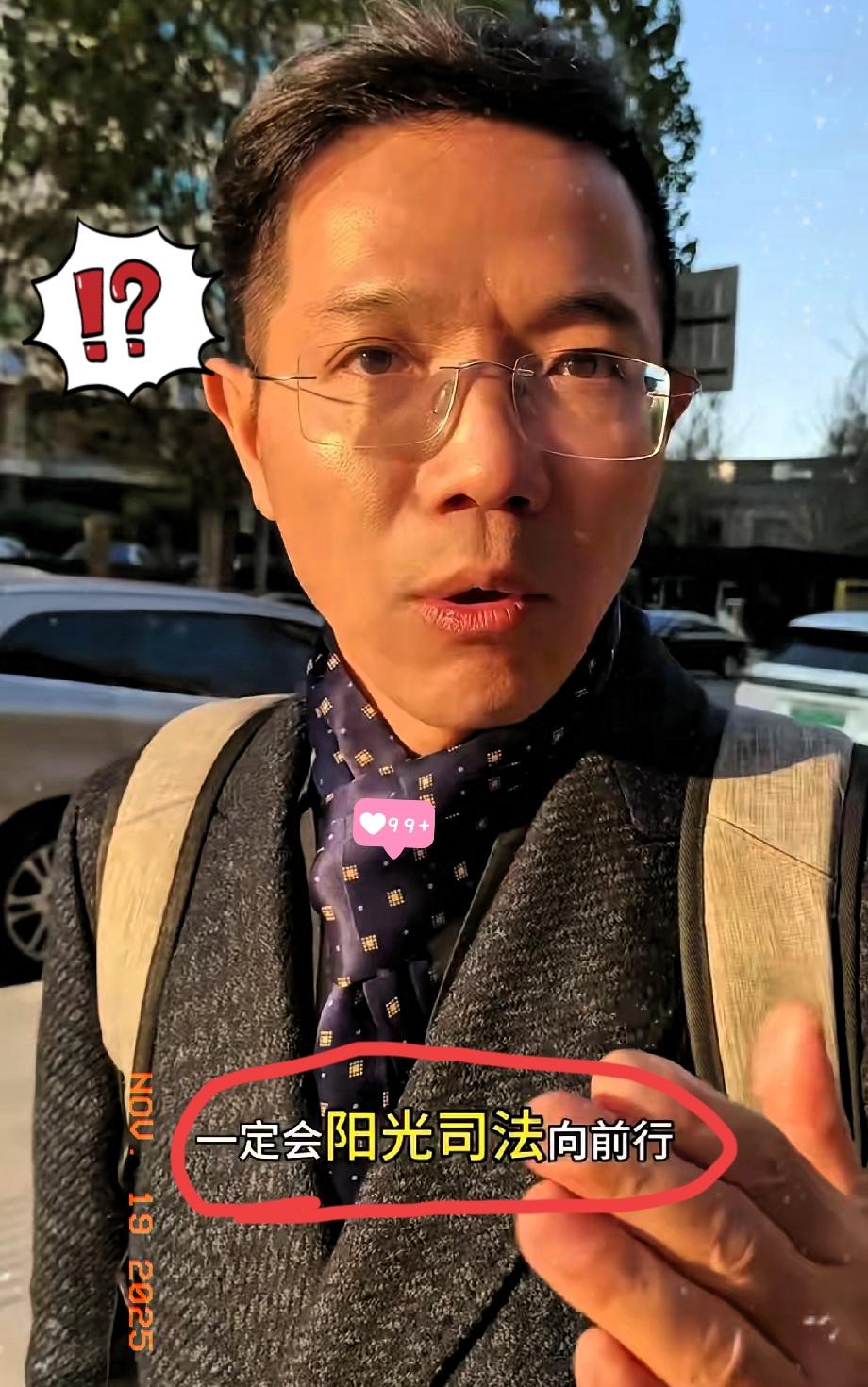“比离婚还伤心!”湖北一女老师上完课,刚回到办公室,突然崩溃大哭!旁边老师问她咋了,她说:以后我们班又是倒数第一了!原来,她班里的第一第二名学生,竟然同时转学,本来靠着他们俩,班级还不至于垫底,现在他们一走,彻底完了,女老师直呼:气死了,这比我离婚了还伤心! 一名湖北女教师,在办公室里当着同事的面,情绪突然失控,哭得话都说不出来。原因听着有点让人意外:班里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要一起转学了。 她甚至哽咽着说,这种难受的感觉,比自己当年离婚时还要强烈。 这串眼泪,到底是什么滋味?它的背后,究竟是一位教师那份质朴无华的责任心使然,还是整个教育评价体系如巍峨大山般沉甸甸地压在个体肩头?此问引人深思。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老师的崩溃,最直接的原因是害怕。她怕班级成绩会再一次成为年级倒数第一。这可不只是面子问题,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捆绑。绩效、评优、职称,每一项都和班级的平均分、优秀率、及格率这些冰冷的数字挂钩。 教师这份工作,早出晚归,操心费力,可最终的评价却常常被简化成一份成绩单。尤其是在她带的这种生源本就一般的普通班里,那两个高分学生,就像定海神神针,凭一己之力就能拉高全班的平均分。 现在神针要被抽走了,她过去无数个日夜“熬”出来的心血,感觉瞬间就要被清零,换谁谁不急? 当然,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典型的“优等生依赖症”吗?确实,关于优等生的作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在普通班级,尖子生就是全班的“主心骨”和“小引擎”。他们就像拔河比赛里那个在最前面带头使劲的人,能激活整个队伍的士气和节奏。老师为失去这样的学生而痛心,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其他可能失去榜样的同学而难过。 但另一种声音立马会反问:那其他几十个孩子的努力,就被看不见了吗?如果一个班级的成败,要靠一两个天才来维系,这是不是本身就说明了教学模式的脆弱?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现实中,教学资源悄悄向少数尖子生倾斜的例子并不少见。当老师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保住那几个“高分”时,大部分中不溜秋和暂时落后的学生,就容易被“放养”。 这就像一个看起来华丽的“面子工程”,靠几根柱子撑着,一旦柱子撤了,整个建筑就摇摇欲坠。这暴露出的,正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教学心态,它依赖少数人,却忽视了大多数。 说到底,老师的眼泪引出了一场关于教育价值的博弈。我们到底是要不惜代价地“拯救分数”,还是要踏踏实实地“成就人人”? 真正的教育韧性,从来不是靠守护几个高分带来的虚假繁荣。而在于,即便没有了那个最耀眼的第一名,老师依然有办法、有信心,去帮助暂时落后的孩子补上基础,去激励处于中间层的学生冲破瓶颈。 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一个孩子,无论起点如何,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最大程度的成长。这不只关乎成绩,更关乎教育本该有的公平和温度。 所以,这位老师的眼泪,我们同情。它至少证明,她是在乎的,是有责任感的。但同情之外,这眼泪更应该成为一个反思的契机,提醒我们所有人,教育的终极目标,永远不该是“不当倒数第一”,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