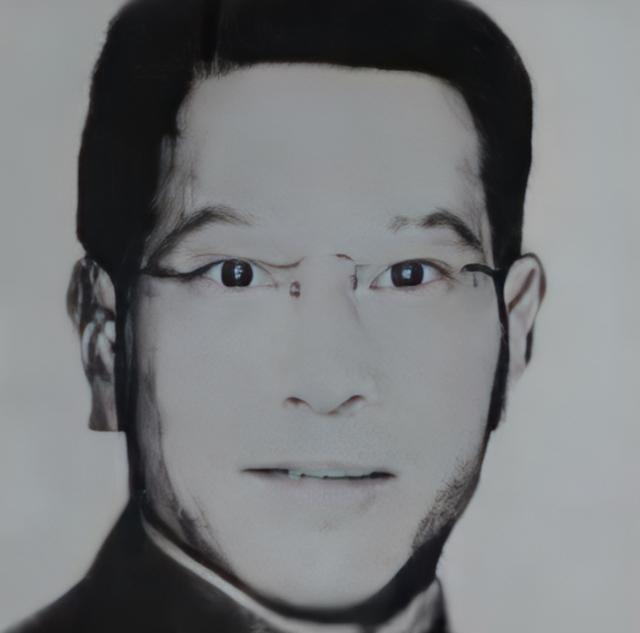1945年,中统的徐恩曾被撤职后,无事可干的他改经商卖黄豆,囤了30万斤黄豆后,黄豆价格却大跌,妻子提议:“何不把黄豆磨成豆腐卖?” 1945年的重庆,天刚入秋就带着股寒意,徐恩曾揣着蒋介石“永不录用”的手令,站在自家空荡荡的客厅里,心里比天气还凉。执掌中统十五年,当年出门前呼后拥,签个字就能定人祸福,如今却成了没差事的闲散人。 看着家里一天天减少的积蓄,这个留过洋的硕士咬咬牙,决定下海经商——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栽在一袋袋黄豆上。 徐恩曾选黄豆不是瞎蒙的。抗战刚结束,市面上啥都缺,粮食更是金贵。他想起之前开碾米厂时,借着流动船坊避开空袭,赚得盆满钵满的光景,觉得农产品肯定稳赚。 揣着当官多年攒下的家底,他跑遍重庆周边乡下,硬生生收了30万斤黄豆,租了城郊一个大仓库囤着。 那时候黄豆价确实不错,一斤能换两斤玉米面,他摸着仓库里堆得像小山的黄豆,心里盘算着等运输线恢复,价格再涨点就出手,这笔钱够全家舒舒服服过好几年。为了防霉变,他还特意雇人定期翻动,觉得自己把啥都考虑到了。 可现实给了他结结实实一巴掌。过了没俩月,黄豆价跟坐了过山车似的往下跌,到最后一斤连半斤玉米面都换不来。徐恩曾急了,跑到粮市打听,几个粮商的话让他浑身发冷:“战后乡下丰收,新豆子全涌上来了,谁还买你囤的陈货?”他这才想起,自己当惯了官,只懂靠权力抢资源,压根没摸透市场的脾气。 30万斤黄豆,每天光仓库租金、雇工费就不是小数,更要命的是,仓库再潮,也挡不住虫蛀鼠咬,有些豆子都开始发潮结块,再卖不出去就真成一堆废料了。 妻子费侠看着他愁得饭都吃不下,小心翼翼提了句:“要不咱把黄豆磨成豆腐卖吧?”这话刚出口,徐恩曾就炸了。 他一拍桌子,官威还没全散:“荒唐!我徐恩曾就算坐吃山空,也不能挽着袖子磨豆腐!”这话喊得硬气,可晚上他看着米缸快见了底,仓库钥匙在手里攥得发烫,心里比谁都清楚——权力没了,以前的同僚下属躲都躲不及,没人再卖他面子。 那几天,他偷偷去街头看豆腐摊,看着摊主麻利地切豆腐、称重量,围观的人排着队,心里的傲气一点点磨没了。 真上手磨豆腐,他才知道这活儿比审问犯人难十倍。找了两个伙计,买了石磨大缸,第一次泡豆就没掌握好时间,磨出的浆又粗又涩。 点卤时更糟,盐卤放多了,豆腐硬得像石头,咬都咬不动。伙计们憋着想笑,徐恩曾脸上火辣辣的,这才明白,当官时呼风唤雨的本事,到了豆腐坊里一文不值。 费侠没法子,托人从乡下请了个磨豆腐的老师傅,老师傅看他一眼,直截了当:“做官我不懂,磨豆腐得凭良心,豆子泡足六个时辰,磨要转匀,卤要点慢,差一点都不行。” 徐恩曾放下了身段,跟着老师傅学了半个月,手上磨出了厚茧,终于摸出了门道。豆浆磨得细腻,点卤时手腕稳了,压出来的豆腐嫩得能掐出水。 可新问题又来了,让伙计去卖,路人看是生面孔,问都不问。费侠拉着他一起站摊,他换上粗布褂子,把西装皮鞋锁进箱子,心里五味杂陈。以前他穿绫罗绸缎,听的全是奉承话;如今沾一身豆腥味,要笑着给顾客装豆腐,还要跟人讨价还价。 没想到,转机就这么来了。有个以前中统的小职员路过,认出他来,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徐主任?您怎么在这?”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怀着好奇来买豆腐,尝过之后都竖大拇指:“徐大官磨的豆腐就是不一样!” 其实哪里是身份的功劳,是他不敢偷工减料——3斤黄豆出1斤豆腐,他从不少放一两豆子,卤也是老师傅传的秘方,味道自然地道。渐渐地,他的豆腐摊前排起了长队,每天几十斤豆腐早早就卖光了。 有次以前的老部下提着礼品来看他,见他在院子里晒豆腐渣,叹气说:“您当年何等风光,怎么沦落到这步?”徐恩曾递给他一块刚做好的热豆腐,苦笑一声:“风光都是权力给的,现在凭双手挣饭吃,心里踏实。” 他这话没说错,后来他又折腾过不少生意,开皮鞋厂缺原料,搞打捞公司没捞到值钱东西,唯独磨豆腐那阵,虽然累,却从没这么踏实过。 徐恩曾的遭遇不是个例。当年跟他一起失势的官员不少,有个姓周的同僚,囤了大批棉纱,最后价跌了没人要,只能当废品卖,最后连房子都卖了。 反观那些踏实做小生意的,比如重庆街头卖汤圆的老张,从不囤货,每天现做现卖,抗战时没倒,战后生意更红火。这就像磨豆腐,看着不起眼,却藏着过日子的真门道:不贪大求全,凭手艺凭良心,比啥都牢靠。 后来徐恩曾去了上海,靠着以前的人脉搞过不少投机生意,却再也没像磨豆腐时那样安稳过。晚年他回忆起重庆的豆腐坊,总说那是他这辈子最清醒的日子。 是啊,他手握过权力,囤过30万斤黄豆,却栽在了不懂市场的傲慢上;可当他放下身段磨豆腐,反倒靠这不起眼的小生意稳住了生计。 这道理其实很简单:权力会消失,投机靠运气,唯有脚踏实地的手艺和良心,才是最稳当的饭碗。就像他磨的豆腐,看着普通,却能在每一个寻常日子里,撑起一家人的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