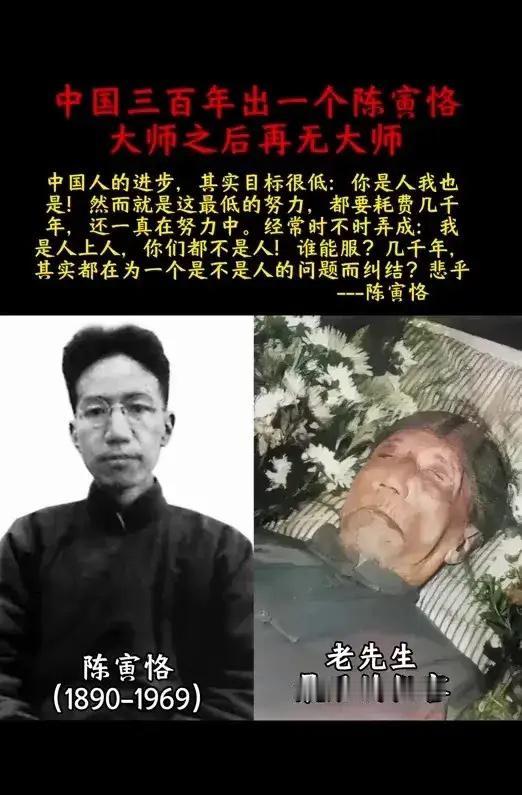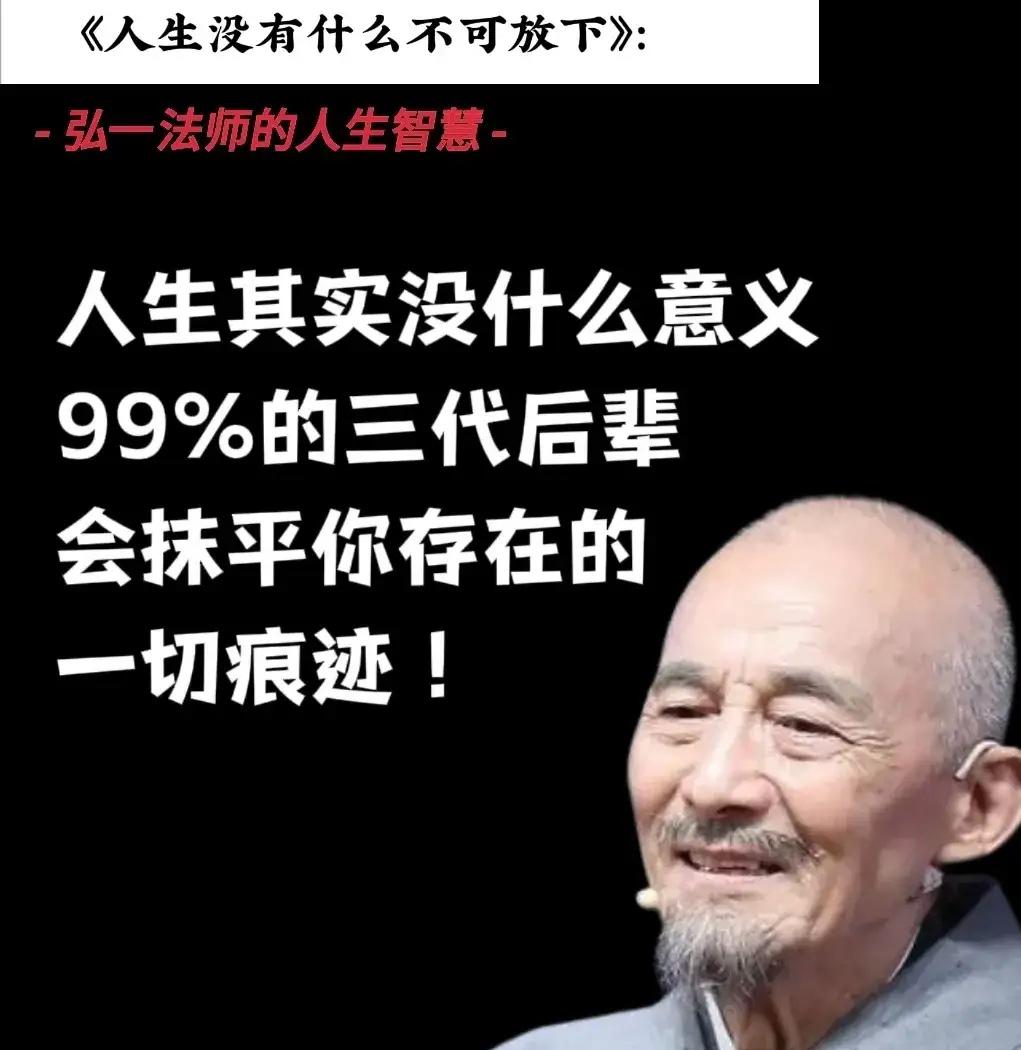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他就是钱穆,江苏无锡人,打20岁站上小学讲台起,这辈子就没离开过“中国历史”这四个字。 没上过一天大学的他,全靠自学啃完了二十四史。无锡乡下的油灯下,青年钱穆抱着线装书读到深夜,书页被手指磨得发毛,批注写了密密麻麻好几本。23岁在小学教历史,他不讲枯燥的年代事件,专挑“岳飞背上的刺字是不是‘精忠报国’”“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删了哪些故事”这类细节,学生听得入迷,下课铃响了还围着他追问。后来辗转中学、大学讲台,从北平到昆明,抗战时期躲在西南联大的茅草屋里,空袭警报声中仍在修改讲义,《国史大纲》的初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笔一划写就。 他的史学研究从不用“批判”标榜深刻,反而带着骨子里的温情。有人说他“保守”,不认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论调,可他在《国史大纲》里写得明白:“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这种敬意不是盲目吹捧,而是在梳理数千年历史脉络后,看清文明传承的韧性。他讲秦汉制度,会追溯到西周的礼乐;谈宋代文人,会联系唐代的科举;哪怕分析乱世分裂,也能找出隐藏的统一基因。北平教书时,学生们最爱听他讲“中国历史的精神价值”,课堂挤得满当当,窗台上都坐着人,他声音洪亮,讲到动情处会拍案而起,眼里闪着光。 1949年,钱穆辗转去了香港,不是想远离故土,而是放不下“让中国人读懂中国史”的执念。在九龙的贫民窟里,他创办新亚书院,初期连像样的教室都没有,学生们在铁皮屋里上课,夏天闷热难耐,他却穿着长衫,一丝不苟地讲课。书院经费短缺,他自己掏腰包垫付,甚至变卖藏书,只为让流亡学生有书可读、有学可上。后来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成为华人学界的重镇,他培养的学生里,不少人成了日后的史学中坚。 可命运对这位老人太过苛刻。晚年迁居台湾后,他在台北外双溪建了间小屋,取名“素书楼”,本想在此安度晚年,继续整理史学手稿。没想到199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房屋产权纠纷,让95岁的他被迫搬离。那间装满了他毕生藏书和手稿的屋子,成了他再也回不去的家。搬离时,他坐在轮椅上,回头望了一眼素书楼的匾额,浑浊的眼睛里满是不舍,嘴里反复念叨着“无锡的太湖,该到杨梅熟了的时候了”。两个月后,老人在孤独与思念中离世,床头还放着一本翻旧的无锡地方志,上面画满了他童年生活过的街巷。 钱穆的一生,是为中国历史“续命”的一生。他没见过多少荣华富贵,却用毕生精力证明:历史不是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根基。哪怕晚年遭遇不公,哪怕至死未能归乡,他留下的史学著作,依然像一盏灯,照亮了中国人认识自己历史的路。如今再读《国史大纲》,仍能感受到他笔下的温度——那是对故土的眷恋,对文明的坚守,对后世的期许。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