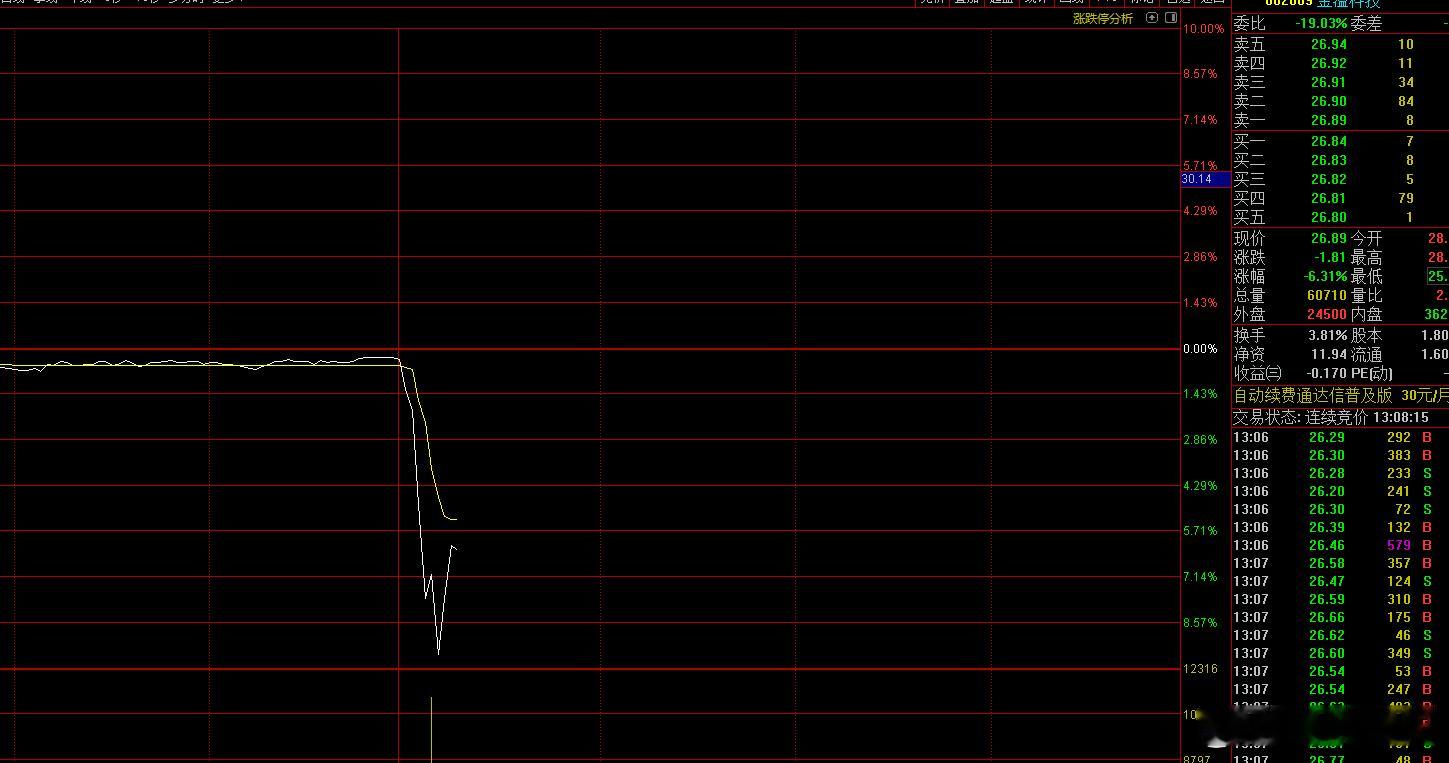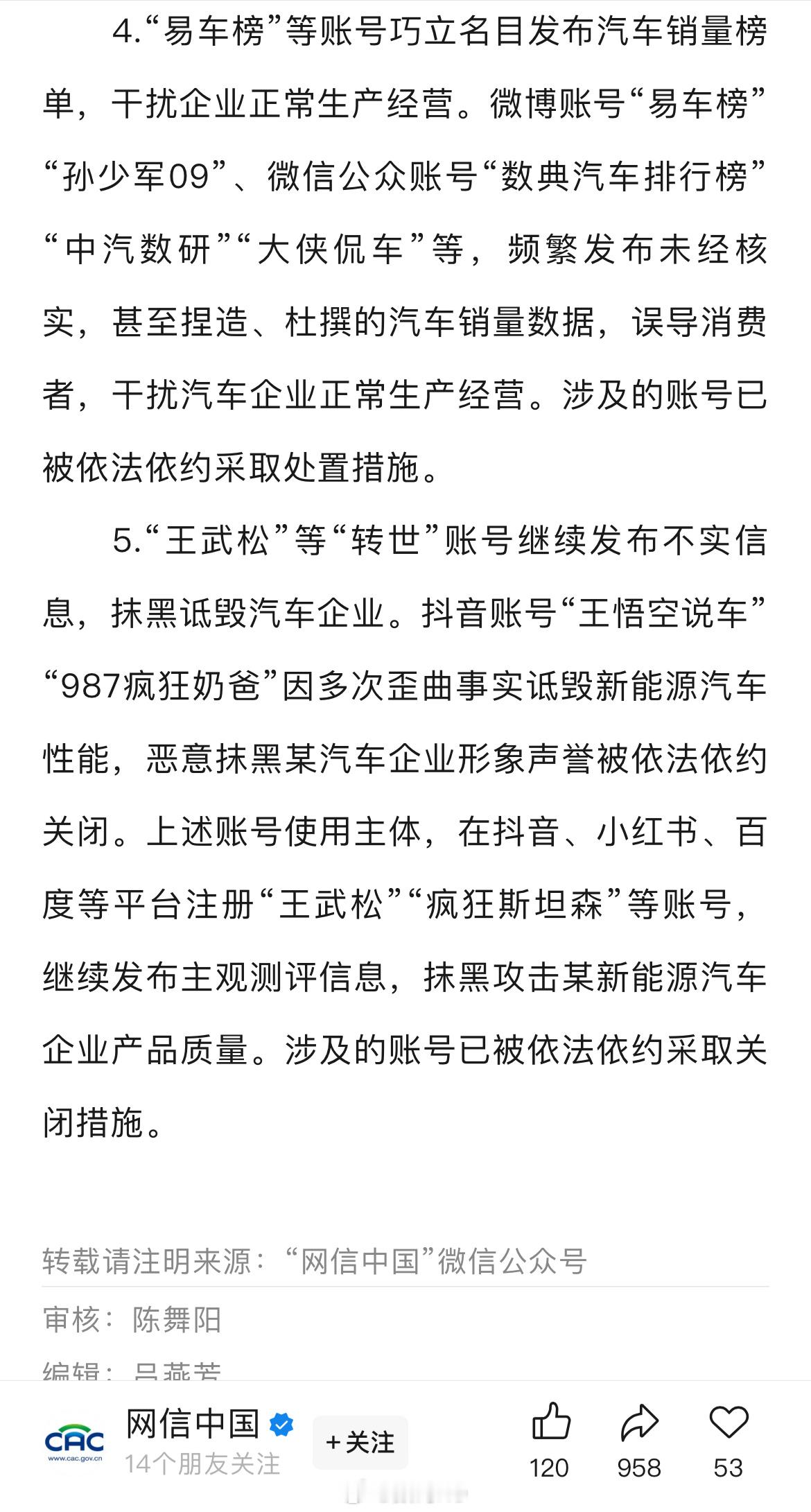1854年,英国一商船偷载了47名中国幼女出发,其中最大的只有8岁,谁都想不到,这艘船上正进行着一场“猪花”交易。 在宁波港的码头,一艘英国商船“英格伍德号”鸣笛启航。 除了甲板上堆着茶叶和丝绸,底舱还锁着47个中国小女孩,最大的8岁,最小的刚满四岁。 她们不是去海外投亲,而是被当成“会喘气的货物”,即将踏上横跨太平洋的“猪花”贩卖之路。 故事要从“猪仔”说起。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砸开了中国的国门。 英国人盯着的不光是茶叶丝绸,还有“人口红利”。 起初他们拐骗年轻力壮的男人,签“契约”运去美洲糖园、东南亚种植园。 这些人被称为“猪仔”,像猪一样能吃苦、好管,一去不回,死在异乡的比活着的多。 可“猪仔”越来越多,海外的华人劳工社区壮大了,麻烦也来了。 男人们远离家乡,生理需求成了大问题。 劳工主子们眼睛一亮。 这不正是“商机”? 于是,“猪花”登场了。 所谓“猪花”,就是被贩卖到海外安抚“猪仔”的中国女人。 她们大多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四五岁,被当作“配给品”,和“猪仔”一起被塞进货船。 名字里的“花”,不是美,是侮辱。 因为在这些洋人眼里,中国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能标价的“牲口”。 而贩子的算盘打得精,从中国沿海穷人家拐女孩,成本40块大洋,转手卖到美国能翻20倍1000大洋。 巨大的利润,吸引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的船队往中国跑,。 1854年的这艘“英格伍德号”,就是“猪花”贸易的典型。 女孩们大多来自宁波周边的渔村和穷乡。 有的甚至被父母自愿以40块大洋卖掉。 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这点钱够买半袋米。 有的被拐子夜里摸进村子,捂嘴扛走。 还有的被船工哄骗:“带你去看大船,给你糖吃。” 一上船,她们就被赶进底舱。 舱门用铁钉钉死,只留拇指宽的缝透气。 排泄物、呕吐物混着海水味,在密闭空间里发酵出令人作呕的臭气。 女孩们挤成一堆,大的搂着小的,小的哭着喊“娘”。 更狠的是,人贩子怕女孩生病闹出动静,连水都不给多喂。 航行到厦门时,一个中国船工偷偷溜下船,闻到底舱的臭味不对劲。 他扒着舱缝往里看,孩子们浑身长疮,有的已经没了呼吸。 船工连夜报给英国领事。 领事派人撬开舱门,47个女孩蜷缩在粪便里,最小的那个已经没了心跳。 剩下的被紧急送往澳门安置,总算捡回半条命。 这47个女孩是极少数“幸运儿”。 绝大多数“猪花”,连见到阳光的机会都没有。 在澳门或香港的中转站,她们被赶上拍卖台,像牲口一样被人围观。 买主多是妓院老板、富商或白人殖民者。 价格按年纪和模样定,越小的越贵,因为“好调教”。 长得周正的能卖1000大洋,是买入价的20倍。 运到旧金山的,进的是华人社区的暗娼馆,运到澳大利亚的,给白人当“玩物”,运到秘鲁的,塞进糖园当“免费劳力”。 这些女孩年纪小,身体扛不住感染梅毒的、得肺病的、被折磨疯的,每天都在增加。 活下来的,得在鞭子下接客十几年,到老了被扔街头,自生自灭。 “猪花”贸易能猖獗20多年,根子在清政府的无能。 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忧外患。 太平天国闹得长江流域鸡飞狗跳,列强的军舰在沿海横冲直撞。 海关、港口全被外国人把控,英国商船来去自如,谁管你贩的是“人”还是“货”? 清朝法律明明规定贩卖人口是死罪,可咸丰年间的官员,连镇压起义都顾不过来,哪有精力管沿海的“小买卖”? 葡萄牙人在澳门设关卡,西班牙船往古巴运“猪花”,英国议会还假惺惺出了个《华人乘客法》,规定船上要通风、给饭吃。 可这些漏洞百出的条款,挡不住贩子们换个船名继续干。 整条产业链从中国内地到海外港口,层层盘剥,利润全进了洋人腰包。 1854年的“英格伍德号”早已沉没,可“猪花”的血泪不该被遗忘。 这些女孩本该在家乡玩泥巴、跟着娘学织网,却被人塞进货船底舱。 本该在父母怀里撒娇,却在异国的暗娼馆里耗尽一生。 她们的悲剧,不是“命不好”,是一个国家衰弱到连子民都护不住的必然。 后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新中国成立,我们才慢慢堵住这些窟窿。 现在的孩子能坐在教室读书,能在海边奔跑,不是因为“洋人发了善心”,是因为国家强了。 强到能护着每一个百姓,不让任何人把他们当“货物”。 历史书上写得少,但档案里藏着。 “猪花”的故事,是一面镜子,照出国家弱时的屈辱,也照出民族醒后的力量。 我们现在记住这些,不是为了恨,是为了让后代知道唯有国家强,人民才能活得像个人。 主要信源:(光明数字报——“猪花”比“猪仔”的命运更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