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想再提她!”85岁的阿菊提到继母朱枫时,声音像结了冰。 就那么坐着,窗户没关,风吹进来,人好像更安静了,阿菊都八十五了,一说起朱枫,嘴唇都在抖,手里的筷子都握不稳,差点掉下去,嘴里念叨着再也不想提她了,那声音小得快听不见。 朱枫是谁,外面的人就知道她是1949年春天,睡在阿菊家阁楼上的那个人,天天帮小姑娘梳头,做饭,算是个后妈,可外面没几个人真明白,这个女人不一般,朱枫去台湾是干大事的,上面直接派她过去,就是为了搭上线,建个交通网,谁都摸不清她到底在忙活啥,连睡在她身边的男人都蒙在鼓里,她为什么来台湾,一个字都没跟人透过。 阿菊那会儿才刚结婚,丈夫在国民党的情报圈里头混,天天回家带一堆内部消息当笑话讲,一边吃饭喝汤,嘴里还念叨,今天又截了封密电,共产党的特务藏得真深,朱枫就坐在桌子对面,帮大家添汤夹菜,脸上带着笑,耳朵可尖着呢,问得不多,晚上回到阁楼里,该干嘛干嘛,饭桌上那些“闲话”转头就成了情报,手里还不停地做着针线活,打个掩护。 大伙儿都以为她是个香港回来的寡妇,来投靠亲戚,顺便带了点东西,谁能想到她带的是情报,全塞在那些线装书里,胶卷藏得那叫一个严实,后来嫁给阿菊的父亲,也是组织安排的,觉得这个家能当个好幌子,位置好,背景也干净,人脉方便,是个绝佳的掩护。 朱枫心里跟明镜似的,冷静,有主意,别人看不懂。 阿菊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这个后妈比亲妈还亲,小时候认字,朱枫一笔一划地教她,“家”、“国”、“光明”,还说这些字以后要一辈子记住,总给她带回来漂亮的花裙子,给她穿上,讲外面的新鲜事,还亲手给她梳头,说头发理顺了,心就不会乱。 她那时候就认定,这人就是来当她妈的,虽然没血缘关系,可日子过得暖烘烘的。 没过多久,1950年的春天,天还没亮透,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了,屋里给翻得乱七八糟,一群人冲了进来,朱枫一声没吭,自己穿好鞋,把衣领扣好,就站在阿菊的房门口,看了她一眼,那眼神特别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早就定下来了,然后转身就跟着人走了。 没人晓得,她头天晚上,偷偷把一枚金戒指塞进了窗台的缝隙里,那是组织的经费,是用来跑路,换身份的,可她没碰,一分没动,就留在了那儿。 打那以后,阿菊什么都不敢多问,丈夫告诉她,说她是共党特务,她也只能把这事烂在肚子里。 后来很多人写她的故事,写得特别英勇,说她在牢里吞金子,宁死不屈,嘴巴硬得很,特务怎么都撬不开,说她死的时候就像个真正的信仰者。 可有谁问过阿菊,她心里是怎么看这个人的。 她总说,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把她当亲闺女,可她自己,是真把她当妈了,一门心思地当。 这事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不是什么间谍,也不是牺牲和烈士,是阿菊在什么都不懂的年纪,用尽了一个孩子全部的力气,去相信一个心里始终装着任务的人,朱枫对她再好,再温柔,中间也总像隔着一堵墙。 朱枫为了信仰没回头,阿菊也没办法不觉得自己好像被利用了一场。 有时候别人再问她,怎么看朱枫,她就咬着牙说,不想再提这个人了。 可小时候哭着喊妈的是她,现在一辈子不跟人细说那段往事的,也是她。 你要问她心里到底咋想的,阿菊常常不吭声,跟没听见一样。 那枚金戒指,直到八十年代才被人从窗台缝里给翻了出来,那时候阿菊早就离开台北了,谁也不知道她再看到那枚戒指的时候,是会掉眼泪,还是会笑一笑。 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热闹的谍战剧,也没有英雄传里写的那些铁骨铮铮,朱枫只是在另一个女人的家里,用一个母亲的身份藏着自己的信仰,她的手很温柔,做的事却很锋利,最疼的不是她的对手,而是那个曾经把她当成全世界的孩子。 这事儿谁也说不清对错,这个疙瘩,这块伤疤,就这么一直留在了那些谁也不愿意去碰的角落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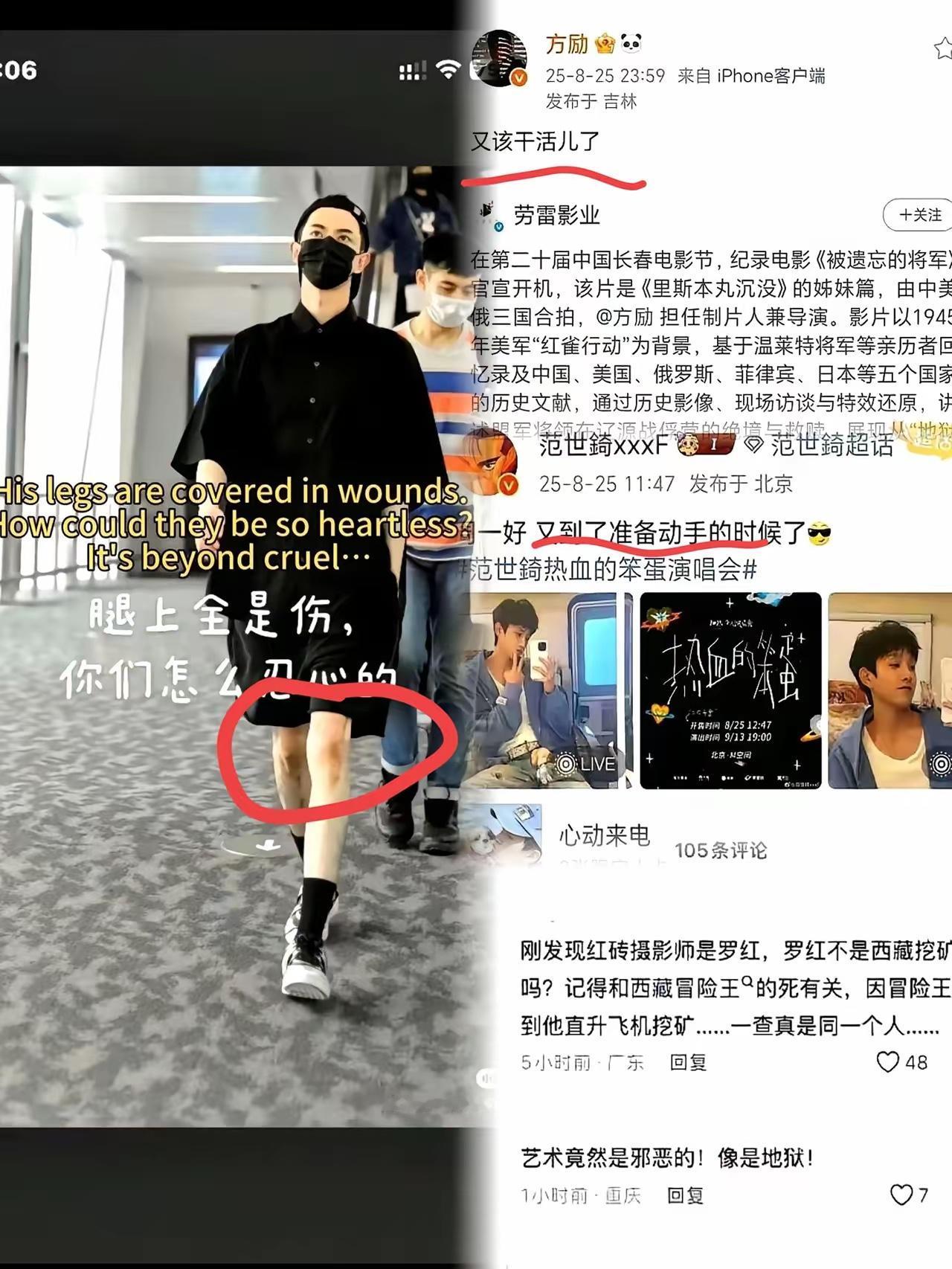





爱情钥匙
心痛到极致所以才不想解开这道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