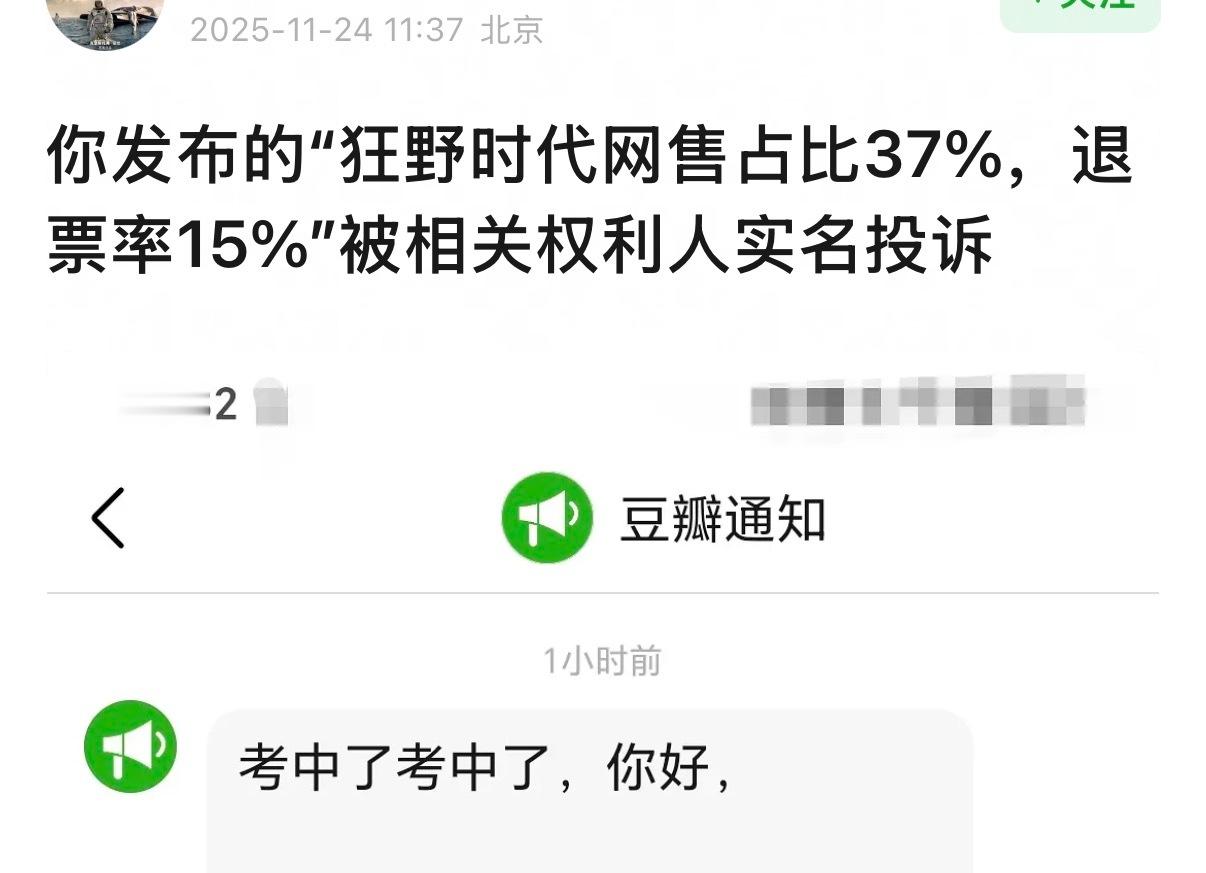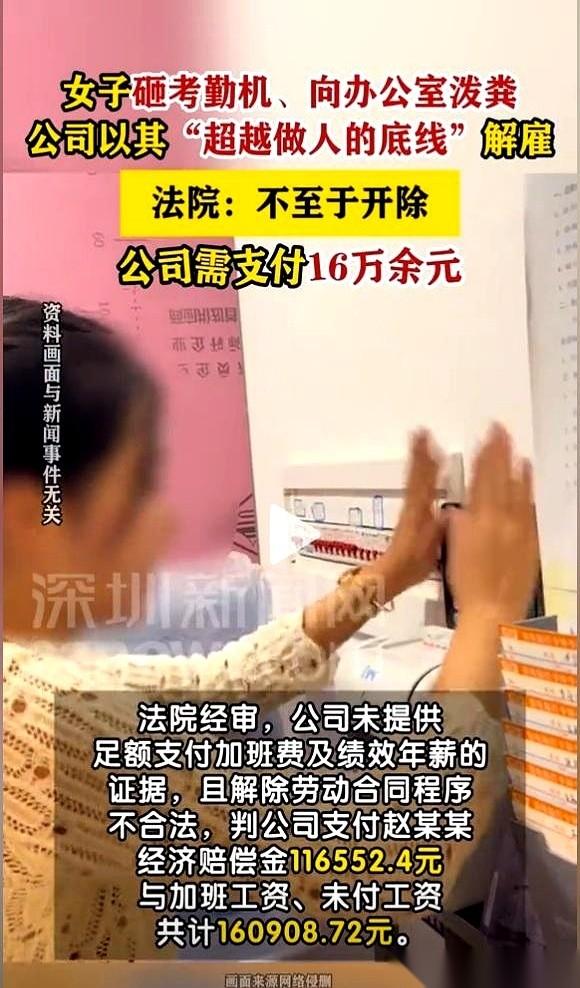生产队那阵儿,村东头的杨文田是队里出了名的壮劳力,肩膀能扛,手能提,干起活来从不惜力。他媳妇秀芳,三十刚出头,本该是女人最水灵的年纪,却得了个磨人的怪病——吃饭咽不下去,硬咽两口就憋得满脸通红,人一天天瘦成了一把骨头,没法睡炕,只能在堂屋地上打了个简陋的地铺,就那么常年躺着熬着,最后还是没挺过来。要知道,秀芳当年可是全队人都认的,最好看的女人。 秀芳没生病那几年,走在村里就是道风景。个子高挑,皮肤是那种晒不黑的白净,扎着两条油亮的粗辫子,辫梢还总系着块小花布。她不光长得好看,干活更是麻利,跟杨文田一起下地挣工分,割麦子能跟男人齐头并进,掰玉米的速度队里没几个女人赶得上。傍晚收工,别家男人还在田埂上歇着,她已经挎着篮子往家跑,灶房里的烟囱很快就冒起烟,杨文田的粗布衣裳永远洗得干干净净,带着皂角的清香味,小院子扫得连片草叶都没有。那时候杨文田走哪儿都带着笑,有人打趣他“娶了这么好的媳妇,真是烧高香了”,他就挠挠后脑勺,眼睛笑成一条缝,嘴里不说啥,那得意劲儿全写在脸上。 谁能想到,好端端的人说病就病了。一开始只是觉得吃饭费劲,嚼半天咽不下去,还以为是嗓子发炎,杨文田给她煮了点姜汤,可没见好。后来越来越严重,喝口稀粥都要憋得眼泪直流,脸憋得发紫,去公社卫生院跑了五六趟,医生也说不出个准毛病,只让回家慢慢养着。人一天比一天瘦,原先圆润的脸蛋凹了下去,胳膊细得跟麻杆似的,连坐起来都要杨文田扶着,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杨文田急得满嘴起燎泡,队里的工分不能少挣——那时候工分就是口粮,少一分都可能饿肚子。可他每天中午、傍晚,都揣着两个凉窝窝头往家跑,火急火燎地烧锅,给秀芳熬最稀的小米粥,熬得黏黏糊糊的,放凉了一点,再用小勺子一点点往她嘴里喂。秀芳咽得难受,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他就拿手帕轻轻擦,声音放得柔柔软软:“慢点儿,不着急,咱歇会儿再喝,啊?” 队里人都看在眼里,没人说闲话,反倒都想着帮衬一把。队长李大叔特意跟记工员交代,杨文田要是家里有事,晚来会儿、早走会儿,工分照样给,不用扣;东头的王婶,每天早上都多熬一碗红薯汤,端到杨文田家门口;西头的张奶奶,隔三差五就来帮着给秀芳擦身子、缝补磨破的衣裳,嘴里念叨着“芳丫头命苦,文田你也别太熬着自己”;村里的半大孩子,放学了就扎堆跑到杨文田家院外,捡点枯树枝堆在门口,喊一声“杨叔,柴火给你放这儿啦”,就撒腿跑没影了。秀芳虽然没力气睁眼,可听见这些声音,就知道是邻里来了,总虚弱地挤出点笑,轻声说“麻烦大伙了,真是……添麻烦了”。 杨文田从没跟人抱怨过一句苦。晚上队里记完工分,别人都回家歇着了,他还得守着秀芳。秀芳咽不下东西,肚子总胀得慌,他就坐在地铺边,用温热的手给她揉肚子,力道轻了怕没用,重了又怕弄疼她,就那么一点点揉着,嘴里还哼着年轻时哄秀芳的小调——那是他从货郎那儿学来的,当年秀芳就爱听这个。有回王婶起早去挑水,撞见杨文田蹲在灶房门口,手里拿着个干硬的窝窝头,啃两口就着凉水咽,眼睛红红的,王婶偷偷抹了眼泪,回去就把家里攒的两个鸡蛋煮了,给杨文田送过去。 秀芳走的那天,天飘着毛毛雨,凉飕飕的。杨文田刚给她喂完小半碗米汤,秀芳突然拉着他的手,声音轻得像棉花:“文田……我走了以后,你好好过日子,别太倔……队里人好,多跟大伙走动……”话没说完,手就慢慢松了。杨文田没哭出声,就那么坐在地铺边,握着秀芳冰凉的手,坐了好半天,直到李大叔过来叫他,他才抬起头,眼睛红得吓人,却只说“麻烦大叔,帮我招呼下大伙”。 队里人闻讯都来了,男人们帮着搭灵棚、找木料做棺木,女人们帮着缝寿衣、蒸馒头,连村里最调皮的孩子都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没人打闹。杨文田没垮,该忙的事一样没落,只是脸上没了笑。 后来日子慢慢过着,杨文田还是每天早早下地,工分挣得比以前还多。傍晚回家,他还会习惯性地先往灶房走,愣一下才想起灶房里没人等他了。但他没孤单多久,谁家有事他都主动搭把手:张家小子娶媳妇缺木料,他上山砍了两天柴,换了几根好木料送过去;李家老奶奶腿脚不好,挑不动水,他每天早上都先去给李家挑满水缸;队里分责任田,他种的麦子收成最好,还把自己留的好种子分给邻居,教他们怎么施肥、怎么除虫。 有人问他,为啥总帮别人,他就想起秀芳走前说的话,挠挠头笑一笑:“都是乡里乡亲的,帮一把不是应该的?秀芳在的时候,大伙也帮了咱不少。”村里人都说,杨文田这人心实,身上有秀芳的影子,不管日子多难,都能把日子过暖了,把人心焐热了。 出处:据村里老人回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