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怕侍候黑人了”,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了讨好美军,强迫国内平民女性,给美军当慰安妇,一名慰安妇一天最多要接待50多名美兵,她们直言生不如死。 当东京街头挤满欢呼“和平终于到来”的普通民众时,一座名为RAA(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这不是军事设施,而是日本政府为占领军特设的“慰安所”运营组织。 在东京都涩园区,第一家官方慰安所“小町园”开业时,门前美军排起的长龙蜿蜒数个街区…… 一位化名“松子”的妇女在四十年后的口述中回忆:“门口的黑人士兵特别显眼,他们个子高大,说话声音洪亮,我们这些躲在帘子后面的女人都在发抖。” 日本战败后第七天,内阁紧急通过《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决议,由国家财政拨款500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30亿日元)筹建慰安所。 时任内务省官员公开宣称:“用专业娼妓的腰包来捍卫良家妇女的贞操,是必要的牺牲。” 这个决定让超过5万名女性被卷入国家设计的“肉体盾牌”计划,其中既包括职业娼妓,更有大量被生活所迫的平民女性、战争寡妇甚至原女学生。 在横滨的“乐园”慰安所,23岁的战争寡妇美代子每天从清晨6点开始接待,房间外的队伍从未少于20人。 她在1983年出版的回忆录《破碎的菊》中写道:“最害怕深夜轮到黑人士兵,他们常因白人士兵优先而积压怨气,有时会发泄在我们身上。有个女孩因为拒绝同时接待两名黑人士兵,被所长罚三天不准吃饭。” 历史档案显示,RAA管理层内部流传着“颜色分级制度”的潜规则:白人士兵收费3日元,黑人士兵仅收2日元,这种定价策略并非种族平等,而是为了快速分流人潮。 时任厚生省官员在内部会议记录中留下这样的话:“利用他们对黑人的恐惧,可以促使她们更顺从地接待白人主顾。” 在大阪湾的美军基地附近,慰安所“碧玉庄”实行严格的时段划分——黑人士兵被集中安排在晚上10点后的“折扣时段”。 原侍女清子在1991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透露。 “那些女孩都说黑白交替的时刻最难熬,身体已经到极限了,还要面对被歧视者的加倍粗暴。有个叫千惠的女孩每次看到黑人进来都会干呕,后来得了严重的神经性胃痉挛。” 1946年3月,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收到多起美军性病报告后,突然下令关闭所有慰安所。 这个看似道德的禁令实则将女性推向更危险的境地——失去官方监管后,她们被迫转入黑市,卫生条件和安全保障彻底归零。 神户港区的原慰安妇春子回忆:“转地下后接待量反而翻倍,有时一天要应付60多个美国兵,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历史在日本官方叙事中长期被模糊处理。 直到1992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在防卫厅图书馆发现RAA原始文件,政府才被迫承认参与事实。 而当年亲自批准该计划的首相币原喜重郎,在回忆录中仅轻描淡写地写道:“那是非常时期的必要措施。” 在横须贺基地外经营小吃摊的佐藤老人(其姊曾是慰安妇)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国家战败时,最先被献祭的从来都是弱者。那些女人用身体缓冲了占领初期的混乱,等到秩序稳定,她们就像用过的纱布被丢进垃圾桶。” 对比德国战后处理的彻底性,日本对这段历史的暧昧态度尤其刺眼。 2007年曾有民间团体要求国会立法补偿原慰安妇,最终不了了之。 致力于相关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山田朗指出:“RAA问题的本质不是娼妓制度,而是国家在和平时期继续将公民工具化的恶劣先例。” 如今在东京新宿御苑,每个周日下午都会聚集着讲述战争记忆的老人。 当问及RAA往事时,多数人选择沉默。 只有一位不愿露脸的老妇低声说:“我姐姐当年被送去时18岁,回家时得了败血症。她临终前一直重复“最怕天黑后的那些人”,直到现在,我看到深肤色外国人还是会发抖。” 这段被刻意尘封的往事提醒众人:当国家以集体利益之名剥夺个体尊严时,所谓的“爱国”就变成了系统性的背叛。 而那些在制度碾压下发出的恐惧呻吟,恰恰丈量着一个文明社会的良心尺度,但如今,那段惨不忍睹的往事儿,似乎已经被堙灭在历史长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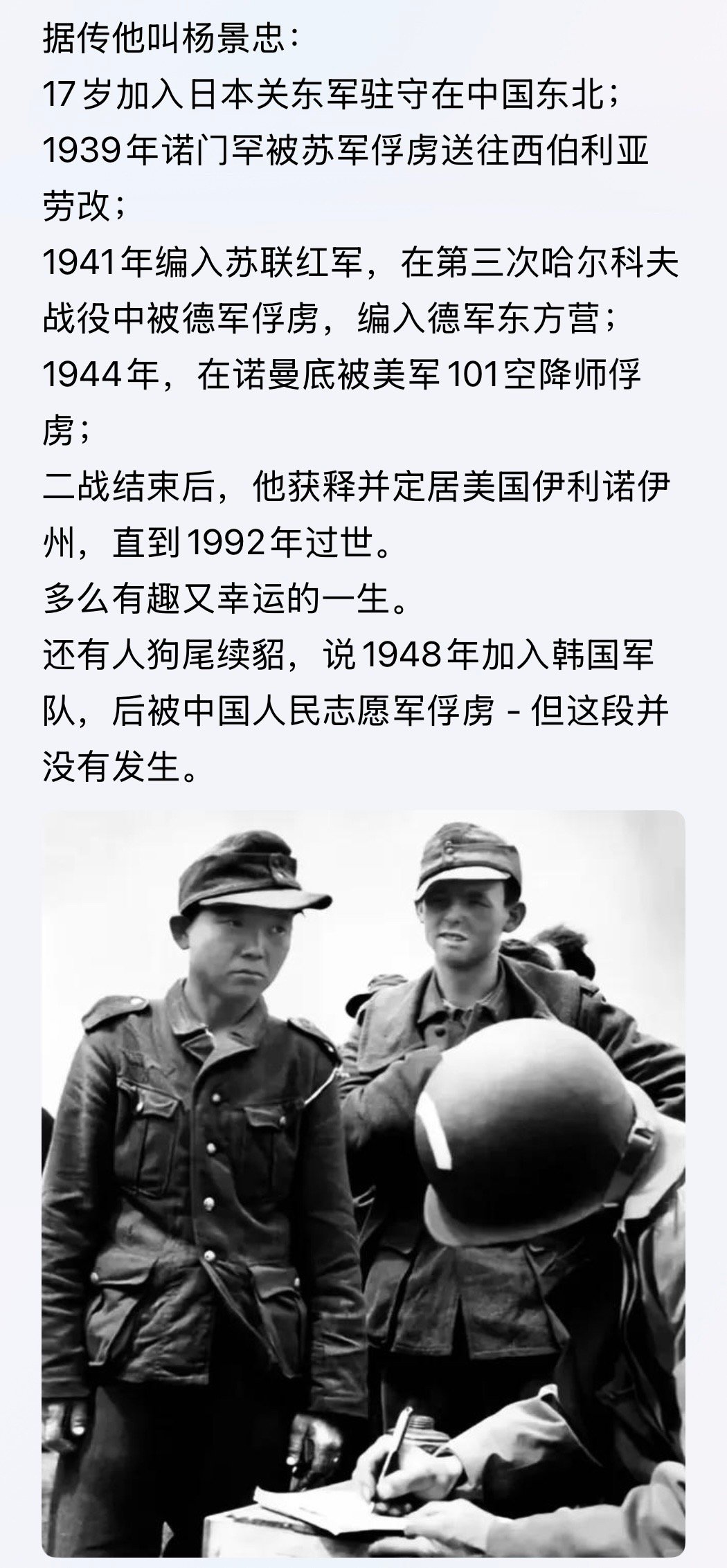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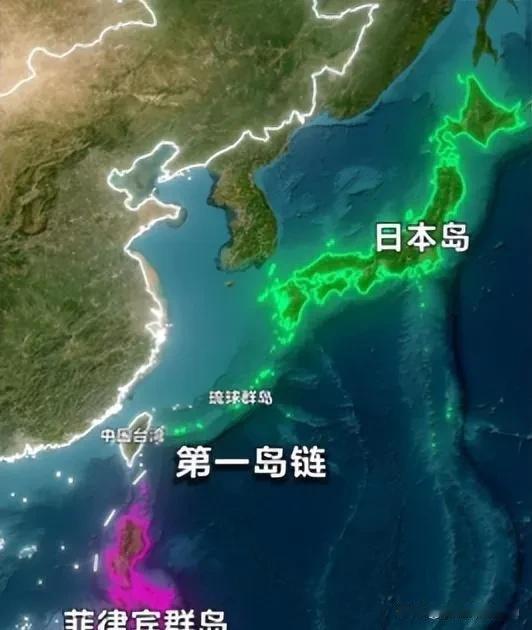




Numb
是鬼子干的出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