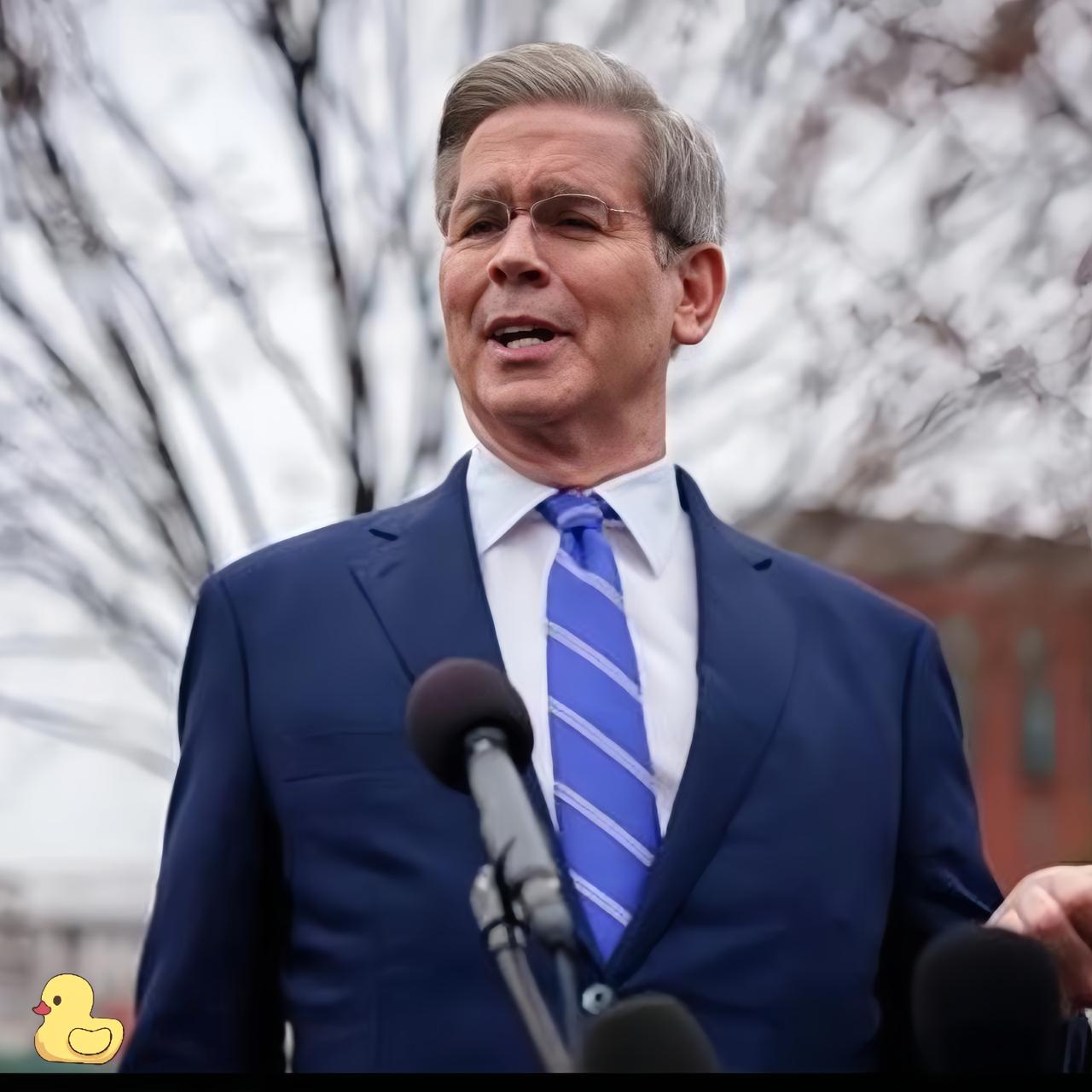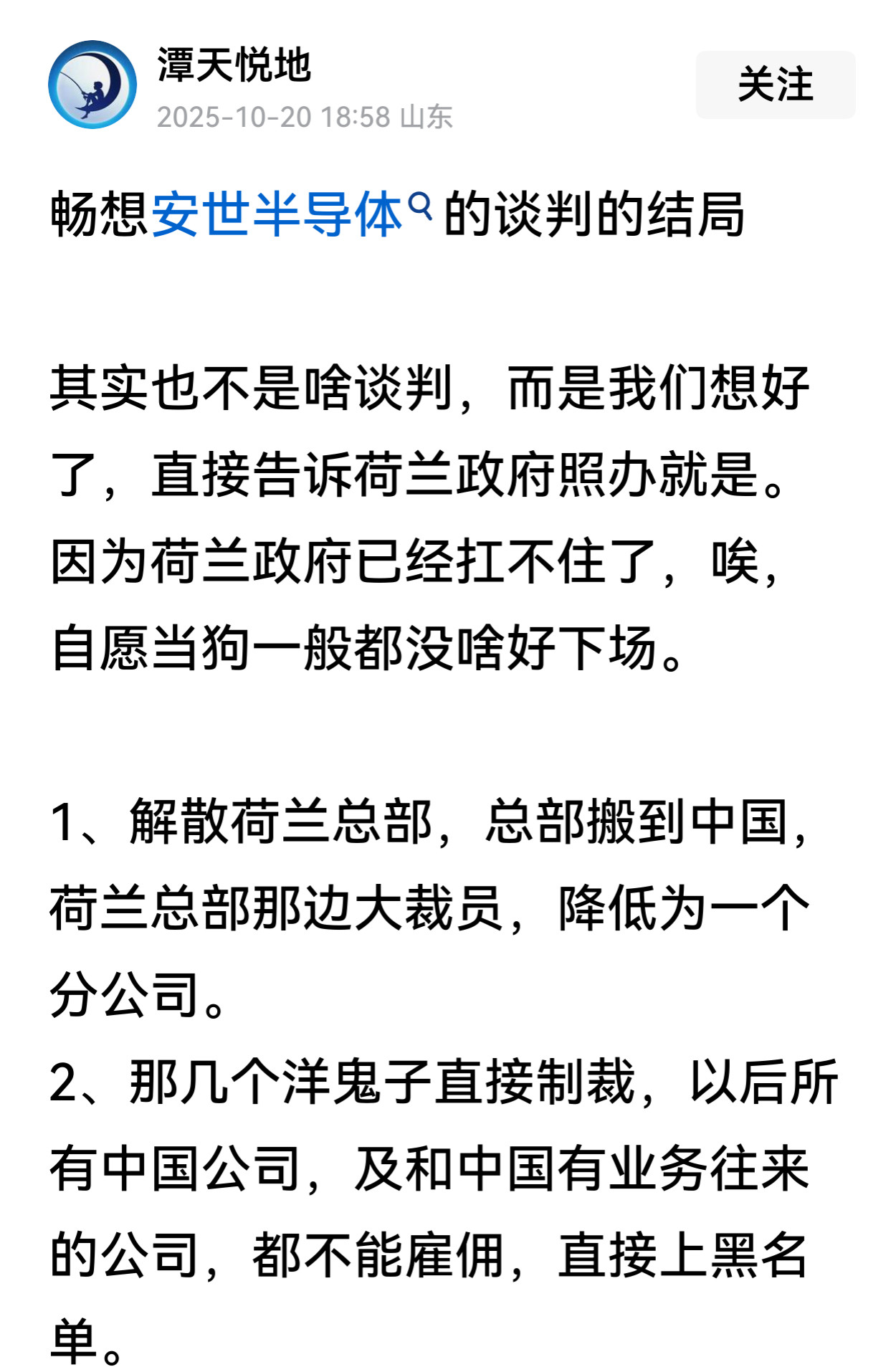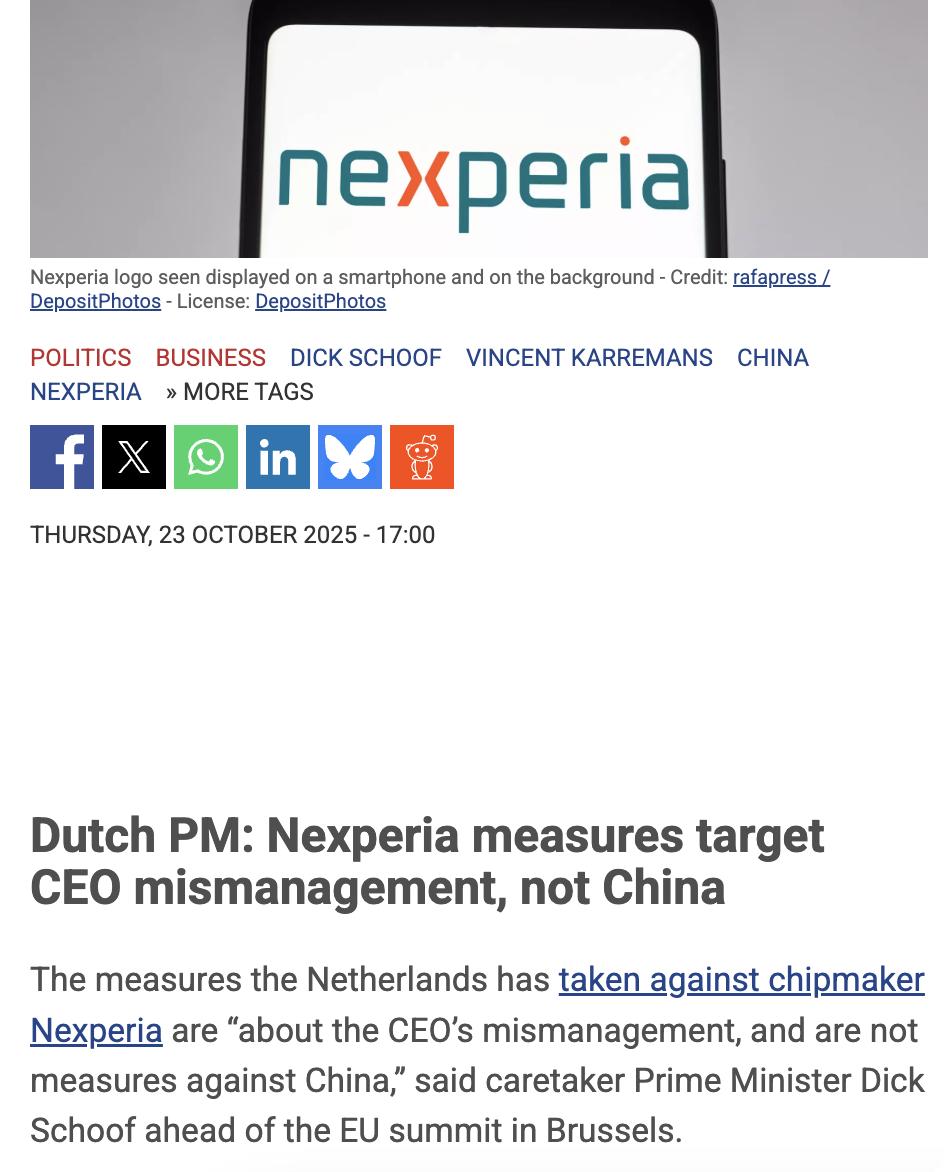“我必须假装爱上他。”1996年,美国一苏丹裔女子邂逅本·拉登后,被囚禁6个月,成了他的性奴。谁知,却因此有了意外收获。 事情得从摩洛哥的一家豪华酒店说起。 一位名叫科拉·布夫的苏丹裔美国作家,正和朋友在马拉喀什的餐厅里用餐。 布夫相貌出众,人群中吸引了酒店里另一位住客的注意,那个住客,就是乌萨马·本·拉登。 很快,本·拉登的手下找上了布夫,礼貌但坚决地传达了主人的邀请,布夫拒绝了,邀请接二连三,一次比一次强硬。 当拒绝不再是选项时,布夫被带到了本·拉登的套房。 这个后来震惊世界的人物,此刻就坐在她的面前。 没有太多寒暄,本·拉登直接表明了意图:他看中了布夫,希望她成为自己众多妻子中的一员。 布夫的人生轨迹被强行扭转。 从摩洛哥的繁华都市,她被转移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阿富汗山区里一处戒备森严的营地。 高墙、铁丝网和持枪的守卫,成了她生活的新背景。 在这里,布夫成了一名囚徒,或者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性奴。 她被迫接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过去在美国习惯的自由穿着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包裹全身的罩袍。 营地里的规矩严苛到近乎荒谬,西方音乐是禁忌,收音机里传出的任何流行歌曲都可能招来麻烦。 她带来的书籍被没收,只能阅读得到许可的宗教读物。 为了活下去,布夫选择了一种特殊的生存策略。 她开始“假装爱上他”,面对这个控制自己一切的男人,顺从和伪装是唯一的武器。 最让布夫感到震惊和怪诞的,是本·拉登对一个人的病态迷恋。 这个人,是远在美国的流行天后,惠特尼·休斯顿。 本·拉登会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位女歌星,认为她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女人。 他觉得惠特尼·休斯顿被美国文化“洗脑”了,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这种迷恋甚至演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疯狂的计划。 本·拉登不止一次对布夫念叨,说自己想去美国,不是为了发动什么袭击,而是为了一个私人目的。 他想找到惠特尼·休斯顿的丈夫鲍比·布朗,然后干掉他。 在他看来,除掉这个障碍后,自己就能顺理成章地把这位歌星娶回家。 为了这个幻想,他甚至愿意为之投入巨额财富。 这种将国际恐怖主义头目与追星族幻想相结合的荒诞场景,构成了布夫囚禁生活中最超现实的一部分。 除了这些私密的细节,布夫也得以近距离观察本·拉登的核心圈子。 她看到了那些追随者的狂热,也感受到了组织内部的等级森严和紧张气氛。 囚禁的生活没有以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大逃亡告终。现实往往比电影平淡,也更残酷。 几个月后,本·拉登对布夫渐渐失去了兴趣。 或许是她的不驯服,或许只是单纯的厌倦。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经过一些内部人员的周旋和一笔金钱交易,她被“处理”掉了。 她被允许离开。就像一件被用旧的物品,被主人随手丢弃。 重获自由的布夫回到了西方。那段经历像一道烙印,刻在了她的生命里。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这段痛苦的回忆,即将转化为一种意想不到的价值。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布夫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主动联系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 她要说出自己知道的一切。 起初,情报官员对这个女人的讲述半信半疑。 一个自称当过本·拉登“情人”的作家,故事听起来太过离奇。但随着谈话的深入,他们意识到,布夫提供的信息具有独特的价值。 她不知道任何具体的恐怖袭击计划,也无法提供基地组织的战略蓝图。 她拥有的,是更私密、更个人化的情报——这正是当时情报机构所缺失的。 这就是她的“意外收获”。 布夫详细描述了本·拉登的性格。他的极度自恋、偏执以及对美国根深蒂固的仇恨。 她讲述了他的生活习惯,比如他不喝酒,喜欢吃什么,每天的作息安排,甚至他如何管理自己的几个妻子。 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细节,为情报分析人员勾勒出了一个更立体、更人性化(尽管是扭曲的人性)的本·拉登形象。 通过这些信息,分析人员可以更好地推断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 她还提供了关于本·拉登核心圈子成员的观察。谁是他的心腹,谁负责财务,谁在内部更有话语权。这些第一手的人物关系速写,为了解那个封闭王国的权力结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 曾经的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了对抗恐怖主义链条上一个特殊的情报提供者。 这段被囚为性奴的黑暗经历,最终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让她拥有了对抗施暴者的力量。 后来,科拉·布夫将自己的全部经历写进了自传《一个迷失女孩的日记》里。 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关注。 很多人质疑故事的真实性,因为除了布夫本人的陈述,几乎没有独立的旁证。 但无论如何,这个苏丹女人的奇特经历,为那个神秘而危险的人物,提供了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充满矛盾和惊人细节的注脚。 信息参考: 环球网:《本-拉丹情人出自传 称拉丹欲谋杀休斯顿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