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是巨大骗局?”瑞士提供的安乐死服务,据说患者只需躺在自杀舱里,按一下按钮,就能无痛死亡。但事后在选择安乐死人的尸体上,发现了让人细思极恐的痕迹。
现代科技似乎总想把所有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就连死亡——这件生命中最失控的事,也想给它装上一个程序,一键搞定。
瑞士研发的 Sarco 胶囊舱,堪称这类构想的巅峰之作 —— 它向人们许下承诺:只需短短十分钟,就能让人彻底告别痛苦,迈入安宁之境。
可当它第一次启动后,留在使用者身上的那些痕迹,却让人细思极恐,也彻底撕开了技术与人性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缝。
这个胶囊舱的设计,与其说是医疗设备,不如说是一个被精心包装过的“死亡产品”。这款事物的缔造者弗洛里安・威利特,在人生早年,曾亲眼目睹父亲以猎枪终结自己生命的悲戚场景。
那画面让他觉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不是死,而是“没得选”。所以他想用技术造一个出口,一个有尊严的出口。
操作极其简单,躺进去,自己按个钮,舱内就会充满氮气,大脑缺氧,人在睡梦中就走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瑞士在传统安乐死程序上向来遵循一套极为复杂的流程。
人家那边要医生证明,要心理评估,最后还得你自己动手服药,每一步都充满了审慎的人类判断。而胶囊舱,把这一切都简化成了一道工业程序。
当然,有尊严的死亡从来不便宜,瑞士那些机构动辄几十万人民币的花销,还得先交几百块的年费入会,背后是一套成熟的商业逻辑。
然而,技术设想的完美闭环,在撞上真实的人体时,碎了一地。2024 年 9 月,一名 64 岁的美国女性成为该项技术的首位体验者。
彼时,颅底骨髓炎正困扰着她,不仅导致面部出现明显肿胀,剧烈的疼痛感更让她难以忍受。但她究竟是怎么离开的,却成了一桩罗生门。
有的说法是,程序进行得很顺利,她2分钟失去意识,5分钟后就没了生命体征。可另一种记录却描绘了地狱般的场景: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半小时,舱体剧烈抖动,她用手抓挠胸口,头撞击舱壁,发出沉闷的响声,刺耳的警报更是响彻了三十分钟。这哪里是安详,分明是缓慢的机械性窒息。
更诡异的是她身上的痕迹。两边都提到了类似勒痕的印记。一方说,官方证实这是疾病导致的皮下出血;另一方则说,调查显示这些痕迹在她死前就有了。到底是什么?没人说得清。真相,就跟那扇紧闭的舱门一样,成了一个谜。
这次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设备的生产方和运营方被警察带走调查,而发明者威利特本人,精神彻底垮了。
他开始出现幻觉,总听见那要命的警报声,感觉有人在敲舱门。今年5月,他从三楼摔下,腿骨严重骨折,最后还是选择了传统的药物注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终究没有躺进自己发明的那个“完美”终点站。
Sarco胶囊舱的争议,其实只是全球关于安乐死这场漫长拉锯战的一个缩影。关于这一议题的探讨,早在古罗马时期便已展开,就连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曾谈及:医者是否拥有让患者生命历程加速走向终点的权利。
时间的指针拨至 1967 年,来自英国的专家桑德斯,才真正意义上搭建起现代临终关怀机构的雏形,为这一关怀特殊群体的领域开辟了新路径。
可实践起来,风险太大了。1986 年,医者浦连升面对一位肝硬化终末期患者的煎熬,应其家属恳请协助结束痛苦,未曾想事后竟遭到患者女儿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虽然最后判了无罪,但他的职业生涯也毁了。
即便在观念更开放的英国,也是直到最近才通过相关法案,而在此之前,每年有大约5000名英国人,不得不踏上前往瑞士的“死亡旅行”。
如今,那个曾被寄予厚望的Sarco胶囊舱,被一块防尘布覆盖着,静静地躺在仓库里。它的沉寂像一个巨大的警示:死亡,不是一个能用代码“优化”的技术问题,它关乎人性、伦理和最深沉的关怀。
真正的尊严,也许从来就不在于按下一个按钮的便利,而在于一个社会,在面对生命终点时,所能提供的那个复杂、全面、又充满同理心的支持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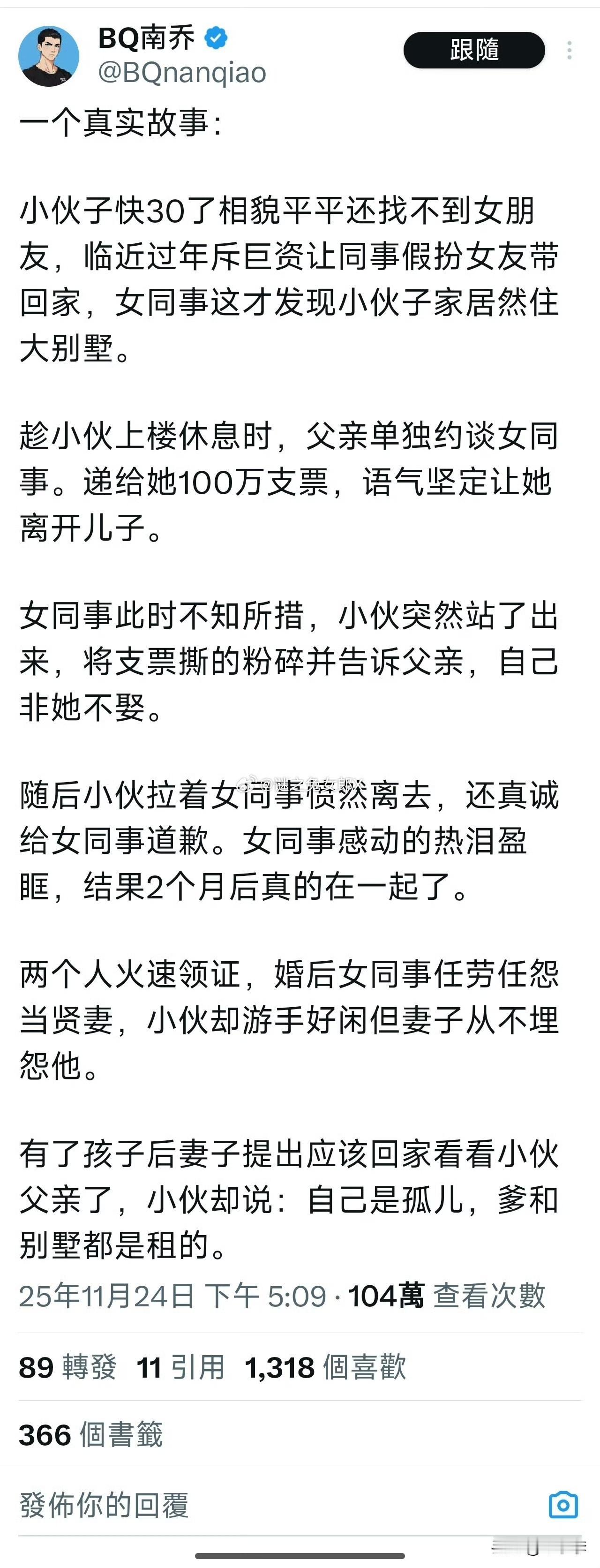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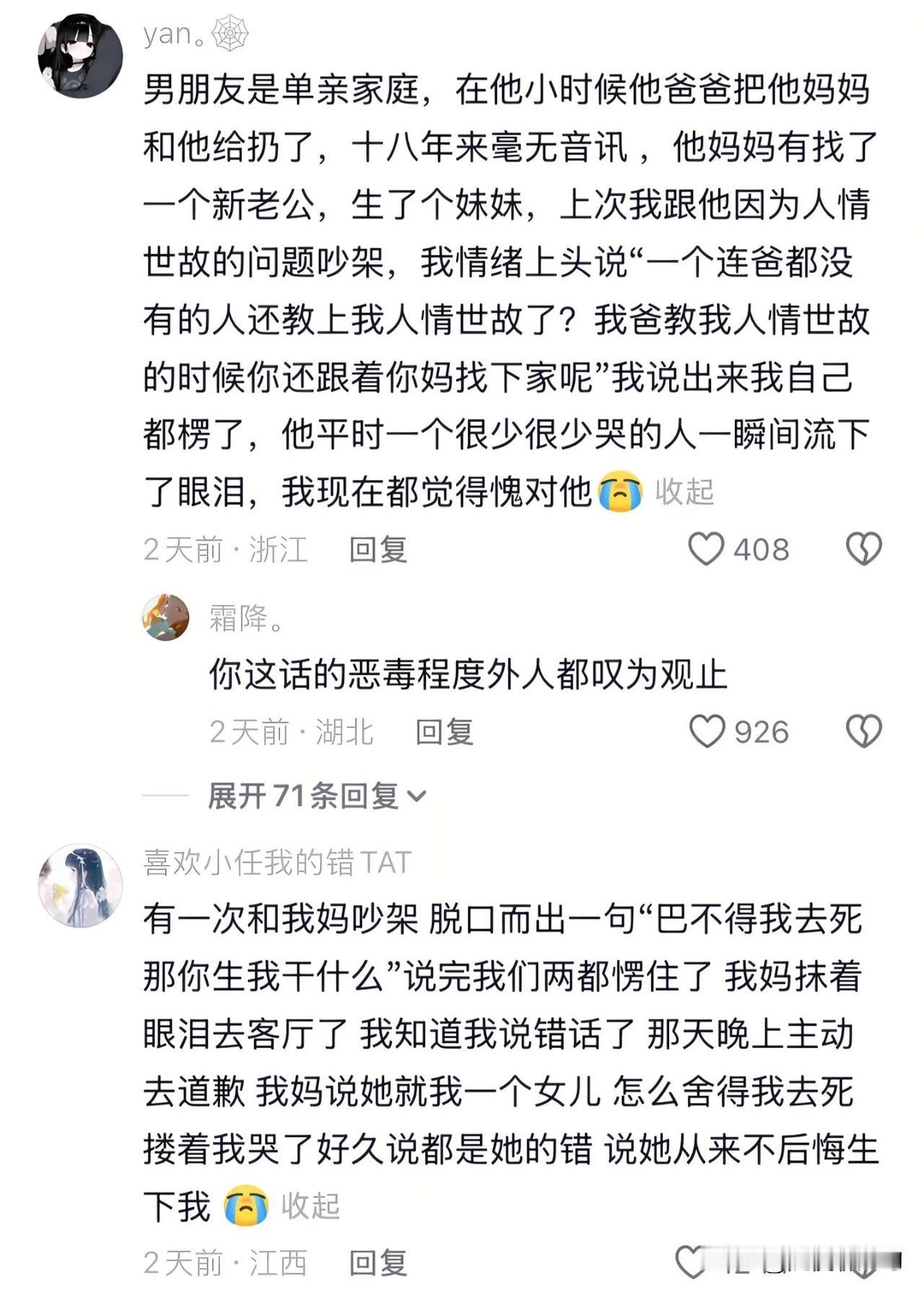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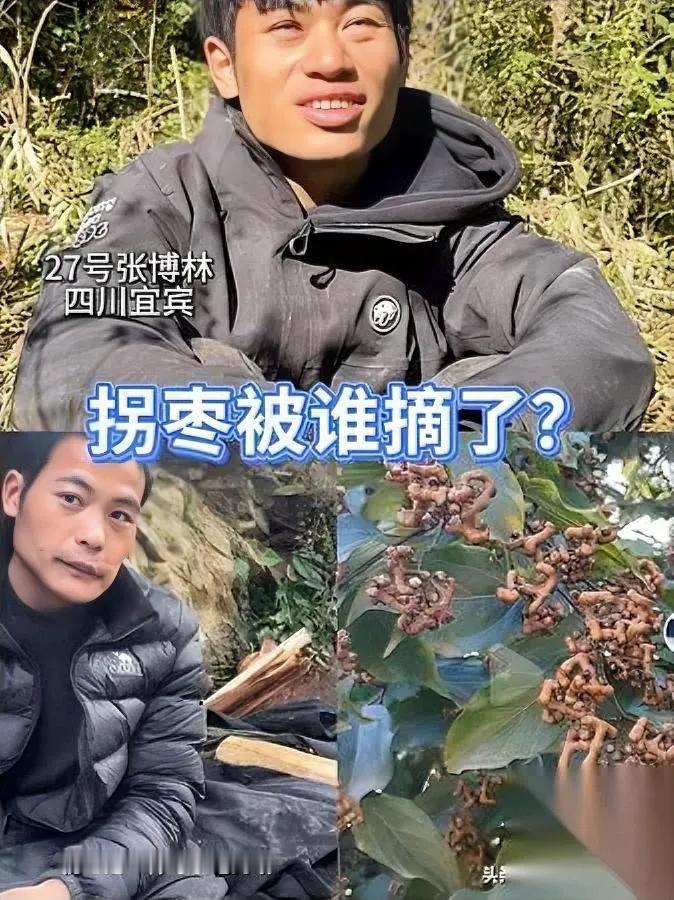




悠闲
都安乐死了,医院挣谁钱去
用户10xxx80 回复 09-08 20:07
你不给钱,谁给你安乐死❓
加勒比海带 回复 12-02 17:36
医院挣该挣的钱,和实不实行安乐死没有一毛钱关系
风云四季天
不用发明虚夸,生命终极瓦丝于液化气打开不就完成西天取经了?生命靠的坚强。不是去终极所有,下地狱后也还是烦是忧,顺其自然天长地久就是好!
用户10xxx80
安乐死,最怕被安乐死!
我是谁
直接氰化钾,就算有点病苦也很短暂。
宝贵
都没有屠宰场的猪走的安详
用户16xxx37
狗头铡,直接把头切了,这个痛苦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