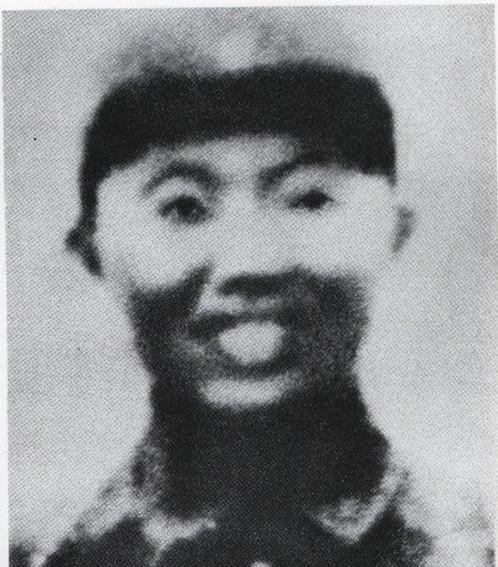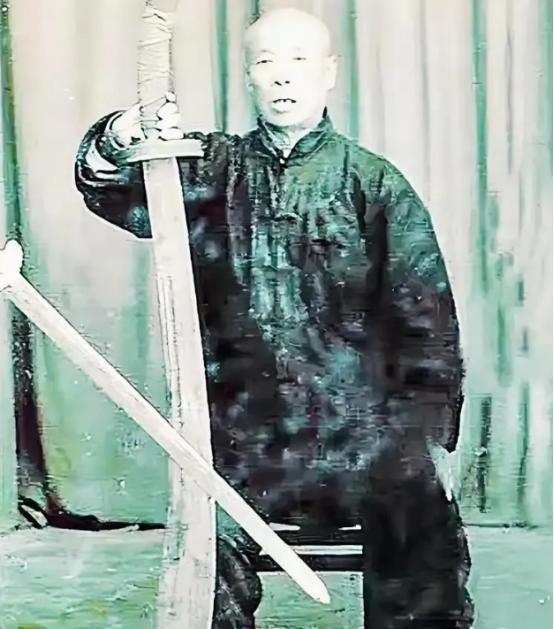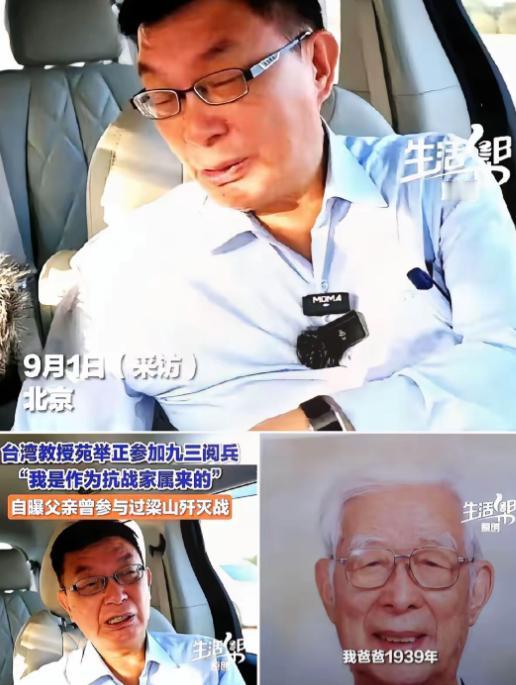他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是唯一杀敌无数的两弹元勋。 1960年11月5日的西北戈壁,寒风卷着沙砾掠过发射架。张镰斧站在人群中,中山装领口沾着油污,和周围穿工装的技术人员没什么两样。 远处,那枚被命名为“东风一号”的银色导弹静静矗立,像一柄即将出鞘的利剑。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左肩,那里埋着上甘岭的弹片,此刻却因另一种紧张而隐隐作痛。二十三年前,他还是山西一个叫张继唐的农家青年,在硝烟弥漫的太行山里,第一次握住了步枪。 那场伏击战至今刻在他骨子里。日军小队沿着山沟蜿蜒而来,他屏住呼吸,瞄准镜里那张年轻的脸突然清晰。扳机扣动,敌人应声倒地。 七个,整整七个。鲜血染红了枯草,也淬炼了他的枪法。后来在朝鲜,上甘岭的炮火几乎掀翻了整座山头,弹片撕裂了他的肩膀,战友的呼喊声被爆炸声吞没。他躺在战壕里,望着灰蒙蒙的天,第一次意识到,光靠血肉之躯挡不住钢铁洪流。 伤愈归国后,他脱下军装,换上工装,名字也改成了张镰斧。有人不解,这个在战场上以一当十的猛将,怎么突然扎进了图纸和公式堆里?只有他自己知道,朝鲜的炮火让他明白,一个国家光有勇气不够,还得有让敌人胆寒的“重器”。 他被点名参与一项绝密任务——造中国自己的导弹。从零开始,连最基础的教材都稀缺。他带着技术人员在简陋的厂房里熬通宵,用算盘计算弹道,用土办法模拟燃料配比。油污成了中山装的常客,那件领口沾污的衣服,就是那段日子的见证。 此刻,发射场的倒计时声刺破戈壁的寂静。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九点零二分,烈焰轰然喷涌,大地剧烈震颤。 导弹拖着橘红色的尾焰拔地而起,撕裂长空。人群爆发出欢呼,他却死死盯着远去的轨迹,仿佛能看见弹头里每一颗螺丝的转动。七分三十七秒,指挥所传来消息:命中目标!飞行距离五百五十公里! 他长长舒了口气,肩头的旧伤仿佛也轻了许多。这枚导弹,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结晶,更是他从一个战士向一个“铸剑师”转变的里程碑。 风沙渐歇,夕阳为戈壁镀上金边。张镰斧望着空旷的发射场,耳边似乎又响起上甘岭的炮声。从山西的伏击战到朝鲜的坑道,再到眼前的导弹基地,他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路。 那些油污、弹片、算盘珠子,都成了他生命里无法剥离的印记。他低头掸了掸中山装上的沙尘,领口的油污在夕阳下格外醒目。 这污渍,是战场硝烟的延续,也是大国重器诞生的胎记。远处,新的发射架正在搭建,更远的未来,已在图纸的线条间悄然铺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