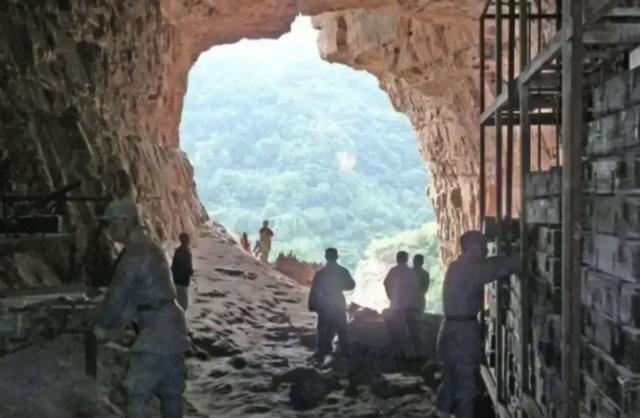1942年,为了救出情报员,新四军决定抓日军队长的老婆来交换。谁知,日军队长的老婆没抓到,却抓到了师团长的侄女! 1942年的江苏南通,那时候,南通城里潜伏着咱们新四军一个极其重要的秘密电台,负责人叫李庚。这可是咱们在敌人心脏里的一双眼睛、一对耳朵。结果,因为叛徒出卖,电台被日军破获,李庚不幸被捕。 消息传到新四军第一师师部,师长粟裕心急如焚。李庚掌握的机密太多了,一旦他扛不住酷刑,整个苏中地区的情报网都可能瘫痪。必须救人,不惜一切代价! 可南通城里戒备森严,想从宪兵队大牢里劫人,跟虎口拔牙没啥区别。怎么办?常规路子走不通,就得来点“邪”的。当时负责敌工工作的干部刘亚罕,一个留过洋、会日语的“文化人”,出了个险招:绑票。 绑谁呢?他们盯上了南通日军警备司令柴田。直接绑个大佐风险太高,但他的老婆就不一样了。一个日本家庭主妇,没什么防备,抓来做人质,逼柴田放人。这个计划,听起来可行性还挺高。 说干就干。侦察员很快摸清了柴田老婆的活动规律,她每周都会坐汽车去一个地方。行动小组埋伏在半路,瞅准汽车过来,干净利落地把车截停,车上的人一蒙头,迅速带走。 整个过程有惊无险。等回到安全区,大家松了口气,准备审审这位“司令夫人”。可头套一摘,所有人都傻眼了——车上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穿着一身洋气的学生装,身边还有个随从。 这谁啊?肯定不是柴田那个半老徐娘的老婆啊! 行动队的同志们心里咯噔一下,完了,白忙活一场,还打草惊蛇了。刘亚罕过来一问话,更懵了。这姑娘叫武内节,刚从东京的大学毕业,来南通是探亲的。她姑父,是日军驻扬州的第61师团长,陆军中将武内俊夫! 我的天!大家当时的心情,估计比坐过山车还刺激。本来想抓个上校的老婆,结果抓了个中将的侄女。这篓子捅得,好像有点大。可转念一想,这哪里是捅了篓子,这简直是摸到了一条“大鱼”啊! 用师团长的侄女去换一个情报员,这筹码,够分量! 抓到了“大鱼”,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养? 这可不是普通战俘,打一顿关起来就完事了。这姑娘是咱们手里最重要的谈判筹码,一根头发都不能少。粟裕师长和一师的领导们很快定了调子:优待,必须优待! 不仅要保证她的安全,还要在生活上给予最高规格的照顾。 于是,武内节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日子,过得有点“魔幻”。 她被安排住进一户条件最好的乡绅家里,独门独院,干净整洁。吃的呢,当时根据地军民都还在勒紧裤腰带,但供给她的,是专门从老乡那里买来的大米、白面、鸡蛋和肉。咱们自己的战士啃着粗粮饼子,得让她吃好喝好。 一开始,武内节非常害怕,以为自己落到了“土匪”手里,小脸吓得煞白,一句话都不敢说。负责跟她沟通的刘亚罕,发挥了自己的语言优势。他穿着整洁的军装,用一口流利的日语跟她聊天,不谈战争,只聊家常、聊文学、聊她在东京的大学生活。 根据地的女战士们也经常来陪她,教她唱《茉莉花》,给她讲中国的故事。武内节慢慢发现,这些“敌人”跟她在日本国内宣传中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凶神恶煞,反而彬彬有礼,尊重她的习惯,关心她的生活。 这种“攻心为上”的策略,是咱们的看家本领,也是那个年代我军区别于所有其他军队的鲜明特质。我们打仗,不光是靠枪炮,更是靠人心。 安顿好了武内节,真正的重头戏,谈判,开始了。 刘亚罕亲笔用日文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扬州,指名交给武内俊夫。信里写得非常客气,先是告知您的侄女在我们这里做客,一切安好,请勿挂念。然后才话锋一转,提出交换条件:用武内节,换回李庚等被捕的抗日人员。 这封信往扬州的日军指挥部一送,武内俊夫当场就炸了。他立刻调集部队,准备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想用武力把侄女抢回来。 但新四军早就料到他会有这一手。咱们的部队早就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给他传话:“你要是敢乱来,你侄女的安全我们可就没法保证了。” 武内俊夫投鼠忌器,仗打得不疼不痒,根本找不到新四军主力。几天下来,人没救着,自己的部队倒损失不小。他这才明白,硬来是不行了,只能坐下来谈判。 谈判的过程,也是一场斗智斗勇。日方一开始还想耍赖,说可以放人,但得新四军先把武内节送回来。这我们能干吗?刘亚罕的回应很明确:“一手交人,一手放人,在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交换。” 最终,在咱们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日方妥协了。 交换那天,场面极具戏剧性。李庚等同志被日军送到了指定地点,他们虽然在牢里受了些苦,但精神头都还在。另一边,武内节穿着来时那身体面的衣服,毫发无损,甚至看起来还胖了点。 临别时,武内节深深地向刘亚罕等人鞠了一躬,用刚学会的中文说了声“谢谢”。据说,她回去后,把自己在新四军根据地的经历告诉了很多人,让不少日本人对新四军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