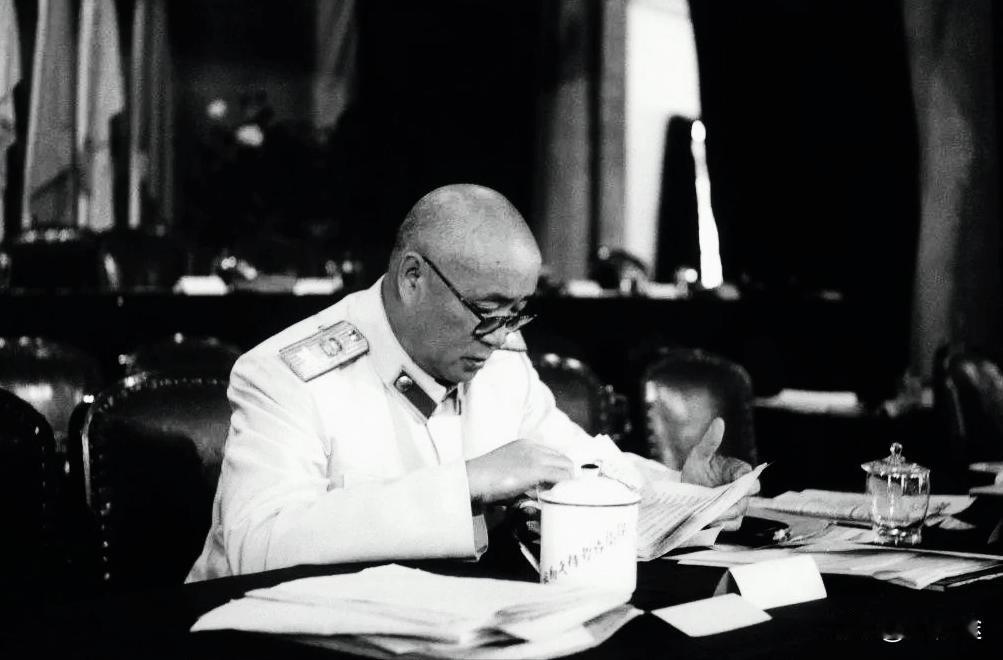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我一直持一种观点就是,抗战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而是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国共之间存在配合、默契、矛盾和斗争。初期我们的游击战配合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1940年以后,由于我抗日根据地的逐步发展,渐渐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 抗战这两个字,听起来像是巨石,沉甸甸压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可真要去触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块巨石上不是单一的纹理,而是乱刀一般的切口。 有人记得台儿庄血战,几十万大军拼到城头巷尾;有人记得夜里乡间的枪声,一群穿着草鞋的年轻人埋伏在沟渠边。 刘蒙说过一句话:“抗战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 这话乍听平常,却像在昏暗的灯下突然拍桌,提醒人们——别忘了,这场战争的形状,不是单一的。 想象一下,一边是正面会战的阵仗。 整装齐备的大军在长江岸边列阵,战马喷着白雾,军号吹得紧急。 国民党的打法就是这样,大兵团对大兵团,硬生生把人推上去,钢铁和血肉一层又一层地堆叠。 淞沪会战那年,上海滩笼罩着硝烟,空气里全是焦糊味。 指挥部里的将军们手里摁着地图,目光盯着前线传来的消息。 那种战争,很“正规”,是排山倒海的大场面。 可代价同样惊人,一个阵地失守就是一座城池,几十万人的生死被卷进去。 再看另一边,在冀中的乡村,场景就完全不一样。 白天,田埂上是赶着牛的农夫,夜里,那人可能就背着枪钻进玉米地里。 小分队埋伏在破败的土墙后,等着鬼子巡逻队走过。 等枪声响起,不过十几秒,匆匆几发子弹,敌人倒下几个,剩下的慌乱逃窜。 这样的战斗小得不能再小,常常就是一两个班的人,甚至几名民兵。 可这样的仗一天能打好几次。 冀南军区曾经半年打了八百多仗,平均每天四次,几乎村村都能听见枪声。 有人算过账,如果每个县每天能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下来就能消灭上千敌人。 听着有点夸张,但在太行山和冀中平原的土地上,正是这种“碎片化”的战争撑住了敌后的抗战。 百团大战是个转折。 那一次,八路军罕见地把力量集中起来,沿着铁路和交通线猛打。 铁轨被炸断,公路被破坏,鬼子不得不重新部署。 日军高层在日记里写下过一句话——六成以上的兵力被迫用于对付共产党。 这不是虚张声势,而是敌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也从那时候起,人们意识到,抗战的天平正在悄悄倾斜。 正面战场还在苦撑,敌后游击已经渐渐变成主要力量。 不同的作战方式背后,是不同的面孔。 国民党军队是规整的队伍,军帽压得齐整,军衔一目了然。 你走进他们的营地,能闻到皮靴擦得发亮的气味。 中共的队伍却不是这样。 很多人穿的还是家乡带来的粗布衣裳,草鞋磨破了再打个补丁。尤其到了四一年以后,大批主力脱下军装,下到县大队、区小队,成了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人。 村里有游击小组,区里有小队,县里有大队,民兵星罗棋布。 妇救会组织在夜里传送情报,老大娘在炕上照顾伤员,小孩子当交通员,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田野间。 这种军民交织的局面,让敌人气得咬牙。 大扫荡的年代,鬼子把冀中围成铁笼,意图“梳篦子”式清剿。 可八路军依然能钻进缝隙,原因就是背后有一张密不透风的民众网。 老电影《地道战》里汉奸司令那句台词——“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不是夸张,而是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这份依靠,放到个体上就更动人。 沙家浜的故事,三十多个伤病员,全靠地方百姓掩护。 没有阿庆嫂,没有沙老太,他们早就饿死在芦苇荡。 冀中“五月大扫荡”后,不少掉队的八路军伤员,被堡垒户一家一家的藏在地窖里,熬过了最黑暗的日子。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被逼到最极端:一碗粥、一张草席,就可能救下一条命。 正因为依靠不同,历史观也截然不同。 国民党总是强调将军的丰功伟绩。 青天白日勋章几乎全给了高级军官,士兵很少留名。 战争在他们笔下,是少数精英的舞台。 共产党却强调普通人的力量。 抗战时期获最高荣誉的模范,大多数是排以下干部、战士、民兵,名字叫得出、见得着。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作品一律歌颂草根。 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戎冠秀,这些人物之所以让人记得,不是因为他们权力大,而是因为他们和普通人没有距离。 陈毅当年连“陈毅不愧大将风度”这样的台词都亲自删掉,他不想把镜头留给自己。 两种叙述,造就了两种记忆。 国军的故事里是将军们的指挥,战役图纸铺满桌案;共产党那边的故事里是地道、是爆炸队、是女人们深夜挑着粮食的身影。 一个是“高处”的历史,一个是“泥土”的历史。 刘蒙之所以反复强调“全民族的抗战”,正是因为没有泥土里的那群人,抗战根本坚持不下来。